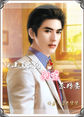黄源水的母亲郭美香原来是一个城市贫民的女儿。
郭美香十八岁那年,全中国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她母亲和小弟先后饿死。她父亲郭先进是漳州打铁巷有名的散仙,这下混不下去了,就带着郭美香搭乘捎排工的木筏从九龙江逆流而上,来到闭塞古朴的山城,准备从这里转道去永定土楼乡村投靠亲戚。那段饥饿、漂泊的日子回想起来恍然如梦,郭美香记得她跟父亲上岸之后,便饿得走不动了,全身的骨肉像纸片一样散开。你走不走啊?跟你老妈小弟一块死去做伴好啦。郭先进咒骂着,硬是把她从地上拉起来。
他们沿着一条比较象样的青石板走去,不知不觉来到了圩尾街。那时阵,天色快要黑了,圩尾街人家的烟囱一片空寂,没有炊烟,四处飘动的是饥饿的冰凉气息。郭先进鼓突的眼睛在圩尾街人家低矮的屋顶上搜寻着,他忽然发现一只歪斜的烟囱徐徐飘出几缕烟雾,眼睛立即变得炯炯发亮,快走呀,有饭吃啦,他扭头对郭美香喊道。
这户有炊烟的人家便是三十五岁的光棍黄跃鹏,他正在灶上煮一锅南瓜稀饭,忽然看见从外面闯进来两个陌生人,而且后面那个还是一个年轻姑娘,不禁惊讶万分,你们找谁?他抢步上前拦住了郭先进。哎呀,这位朋友,郭先进装作很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肩头,你不认识我啊?
郭美香知道,到处把人认作朋友是父亲的习性,她没想到,父亲拥着那人进了里屋叽哩咕噜一通,原来是在做一场交易,而自己正是被交易的对象。那人和父亲从里屋出来之后,眼光变得有些奇怪,好像一个专门贩卖牲畜的行家,上上下下把她打量了几遍,然后轻轻点了点头。饭熟了吧?父亲像是在自己家里,毫无顾忌地从壁橱里拿出一只最大的碗,便舀了满满一碗南瓜稀饭,唏哩呼噜地大口吃起来。父亲的声音刺激了她的饥饿,使她的胃壁一阵痉挛,给我一碗……我饿,她顾不上矜持,朝父亲走了过去。别急别急,有你吃的,父亲推开了她伸过来的手。
一锅南瓜稀饭很快被郭先进父女消灭干净。郭先进用舌头舔着饭碗,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的表情,他说,美香,我们遇上了好心人,就在这边歇一夜,明早再走啦。
半夜里,在偏房睡觉的郭美香忽然发现有人趴在她身上,下意识地向父亲高声呼救,可是没有任何回应,父亲已经带着黄跃鹏的十斤大米和十块钱不知去向。你老爸把你嫁给我了,黄跃鹏在她耳边呼着粗气说,嫁给我你还算是好命,我家地窖里有两筐大米,还有一堆南瓜。也许是因为疲惫,也许是因为大米和南瓜的诱惑,郭美香毫无反抗,黄跃鹏很顺利地剥下了她的衣衫。我老妈真是很有远见啊,说饥荒会来,果真就来了,黄跃鹏两眼射出一种淡绿色的光芒,在地窖里存上一些南瓜大米,还怕找不到老婆吗?
郭美香就这样落户在圩尾街。第二年年底,她生下了黄源德,后来又生了几个先后夭折的女儿。黄源水生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是她生育生涯的最后一个作品,也是她的代表作。黄源水是在郭美香唾沫里和棍棒下长大的,黄跃鹏几乎不承担父亲的管教任务。孩子会成什么材就成什么材,难道一个捡猪屎的命,你打骂他几下,他就变成状元?黄跃鹏常常在一种理论高度上对郭美香望子成龙的做法表示轻蔑。每当这时候,郭美香就恨不得把赶不上儿子的棍棒敲在丈夫南瓜般的脑袋上。
黄源水穿开裆裤起便和梁伟东、叶建清、许光平、刘志华玩在一起,旷课、爬树、下河、抽烟、打架、喝酒,结果只念完初中就到社会上闲混,成为一个十足的散仙。去年八月,黄跃鹏肝病而死,黄源水好像幡然醒悟,决心正经做人好好打拼。他托人贷款,就在五卞桥头开起一间摩托车修理店。郭美香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了这手技术,修理店的生意越来越好,春节一下就抛给自己五千元。正当郭美香准备好好享受儿子的成就和孝心,他却把脑浆涂了一地,两腿一蹬,变成水尖山上的一座新墓。
一夜之间,郭美香头发蓬乱,犹如肮脏的鸡窝,两眼暴突,脸上憔悴失血,至少老掉了十岁。她每天坐在当着圩尾街的门槛上,神情痴呆,嘴里喃喃自语:“歹水,歹水,都是你们,害了我家歹水……”
开头几天,过往的邻居和路人还饶有兴趣地看她几眼,渐渐就熟视无睹,从她面前踢起尘土或者纸屑,踢踢哒哒地走过去。
天气越来越冷了。生长在路边和石缝里的杂草全被冻蔫了。圩尾街捡垃圾的老童坐在娘妈宫的门槛上歇气,他从装垃圾的蛇皮袋里摸出一张《闽南日报》,像县长一样认真地念道:“明天冷空气下降,希各有关部门做好准备。”
有个挟着公文包的中年人从他面前经过,不禁郑重地看了他一眼,说:“你那是去年的报纸,冷空气前天就下降啦。”
郭美香仍然坐在自家的门槛上。几天未经梳洗,她的样子肮脏而又邋塌,好像刚刚从垃圾堆里爬出来。她开裂的嘴唇像两条蛆虫在蠕动,发出充满恶臭的声音:“都是你们,害了我家歹水,歹水啊,歹水……”
捡垃圾的老童提着蛇皮袋子走过来,他低头在街上寻找垃圾,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样子极其专注。一般说来,冬天是老童的淡季,这是令老童非常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他正想抬头出一口气,前边一只矿泉水瓶子跳入了他的眼帘。
那是一只被人踩扁的天第牌矿泉水瓶子,躺在郭美香的面前,一块青石板的凹缝里。老童快步走去,弯腰把它捡进蛇皮袋子。这时,老童听到郭美香混浊的声音,好像巫婆的咒语一样:“都是你们,都是你们……”
“你是说谁?”老童多事地问。
“赌伟、三耳、光头、狗清……”郭美香扳着手指头对老童说,然后又重新说了一遍,“狗清、光头、三耳、赌伟……”
叶建清的母亲曾玉华在自家院子里洗衣服,郭美香的声音传到她的耳边,好像一根刺把她刺痛了,她叭地摔掉手上的衣服,高挽着衣袖的双手水淋淋的,也顾不上擦,几步窜到街上来。
“长嘴巴是让你吃饭,不是让你乱说话的,”曾玉华挥起手,就在圩尾街局部地区下起一阵小雨,“自已命中注定要撞死,又不是什么人害他,整天唠唠叨叨有屁用!”
“不是你家狗清,我歹水会撞死?”郭美香的声音尖了起来。
叶建清在家里闲呆着,听到街上吵吵嚷嚷,跑出来把母亲拉进家里。“你这不是白费劲吗?”他说。
“我听了不舒服。”母亲说。
“不舒服怎样?”叶建清白了母亲一眼,“不舒服又不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