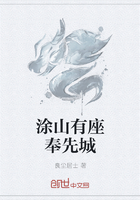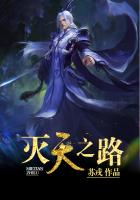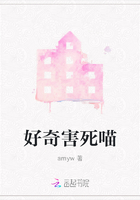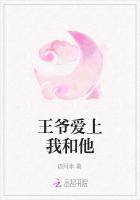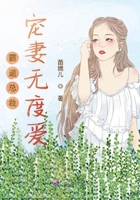不辞而别已经渐渐成了我的习惯。
我不知道我的出现对于他和汤汤意味究竟是好是坏,也不敢知道。
一直走了很远很远,远到我感觉身后那座小城的风也无法触及,我都没敢回头看一眼。我怕一回头看见自己的影子脱离地面变成一个微笑浅浅的汤汤,近百朵粉白莲花如烟花一般在天空中旋转飞舞,他神色如常要我还他汤汤。
如果没有我的出现,也许他还在忙着绣一个如月光般温顺的汤汤。而那些汤汤还可以在夜晚无忧无虑放着烟花。
我到底是该出现?还是不该出现?这真是个无聊的问题。
苏幕遮说这个世界有三个问题最难回答,也是最无聊的。我是谁?我来自何处?我又要去往何方?我当时说,我是吴心,来自桃山,没有要去的地方。苏幕遮只是淡淡笑了笑说,过个十年,你再来回答。
好像十年已经过了。
现在回答的话,我还是吴心,还来自桃山,还是不知道要去往哪里。报复将军?拯救倾城?寻找四象?争霸天下?复活桃花?写完《春秋》?……各种念头在我心间闪闪烁烁。似乎每一个都是我要做的,又每一个都不是我想做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玉门关的,也没有想过会这么快走到玉门关。
大汉很大,但也不是那么大。老王头说这句话的时候喝得烂醉。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现在看来他说的一点不假。
玉门关再往西,就不是大汉了。
这是我第一次来玉门关。可我却一点都不担心认错。因为天下间除了此处,再没有第二个地方值着数量如此众多的杨柳。
长城城墙两侧种着的两排柳树一直延续到了视线尽头。沿着柳树行走的人也排到了视线尽头。他们大多数手里拿着一束绿意盎然的杨柳枝。
玉门关的杨柳从来没有四季之分。一年到头永远是枯瘦着,不长半片柳叶。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也正因如此,流传下来一个习俗。就是每个春天到玉门关的人都会用红绳在干枯的柳枝上系上一根抽了新芽长着绿叶的柔韧柳枝。
城墙下每隔一里的地方会放有一个巨大的箩筐。筐里面有扎成束的杨柳枝免费供人拿取。拿空后,会有专人放入新的杨柳枝。我没有预计到自己这么快就走到玉门关,来之前也忘了折一根杨柳枝,只好从筐中拿了一束杨柳枝,从筐旁抽了一根红线。走了很长一段路,我回了头,找到了柳色最少的那颗柳树将柳枝系了上去。
系完柳枝,我有些饿了,便准备吃点东西。每年来玉门关的人很多。城墙下搭了很多棚子,摆了许多小吃摊。一家馄钝摊前架了一口很大的锅,锅里面乳白色的汤汁被炭火煮的咕咕冒泡。我有些喜欢这个浓郁的咕咕声,便坐了下来,要了两碗。卖馄钝的是一对父子。老父亲负责包馄钝,儿子负责招待客人。老汉侧着锅坐着,眼睛看也不看锅里,包好一个馄钝随手一丢。没有一个馄钝落到锅外。我默默给他喝了个采。
板凳还没坐热,馄钝就好了。我吹开葱花,喝了口汤,没下得去筷子,抬起头对着站在我桌前的一个婆婆笑笑。婆婆头发全白,脸上皱纹密布,眼睛微眯,背有些驼,拄着一根拐杖。
我客气地问她:“婆婆有什么事吗?”婆婆声音柔若柳絮:“你要请我吃碗面。”笑容灿烂仿佛柳条,柔顺却又坚韧。看着她的笑,我总觉得眼前的不是一个已值古稀之年的婆婆,而是一个正逢二八年华的活泼少女。
我请她坐下,把另一碗馄钝推到她面前说:“婆婆请慢用。”婆婆也不客气,从筷笼里拿出一双筷子,喝一口汤吃一个馄钝。等她吃完一碗馄钝,我才礼貌地问她:“要不要再添一碗?”她笑着摇了摇头。我就自己又要了一碗。年轻老板递来馄钝的时候,她说:“这个没我包的好吃,等以后你有机会去我家,我给你做,叫你尝尝什么叫正宗的馄钝。”年轻老板挑了挑眉毛:“婆婆,你再说我家馄钝不好吃,以后我可就不让你在这吃馄钝了。”婆婆呵呵笑道:“这里又不是你一家卖馄钝。你要是不让我在这吃,我就去别家吃。”年轻老板被噎得说不出话来,端着空碗拿去洗刷了。婆婆吃完馄钝,也不走,就坐在对面乐呵呵看我吃馄钝。等我吃完馄钝,她才问我:“吃完了?”我点点头。她又问:“你是军人吗?”我点点头。她说:“那你借我点钱吧。”她说话很流畅,没有一点不自然。我倒是有些尴尬:“婆婆要借多少?”婆婆说:“你有多少?”我说:“二十两?”婆婆说:“那我借一两。”我说:“我是说借二十两给你。”婆婆说:“我就借一两。”我点点头道:“没问题。”婆婆笑着说:“我可没办法还。”我说:“没关系。”婆婆说:“年轻人,不介意陪我这半截入了土的老东西走走?”我笑着说:“婆婆可不老。我刚好想消消食。”
说是随便走走,可她并不是真的只是走走。看见有杨柳枝没系好的,婆婆便将之解下重新系好。如果她自己没系好,就解下来继续重系。一定要她自己看着舒适才作罢。她的个子不是很高,背有有些微驼。所以高处的杨柳枝我便帮着调整。走了一会儿,她有些累了。我便全部接管了过来。又走了一会儿,她有些微喘。我便邀她去城墙上看看。她磕了磕拐杖,看了看依旧望不到尽头的杨柳树,笑着同意了。她走在前头,想自己一个人爬楼梯。可楼梯对于她来说有点高。她爬得有些费力。我快走两步,抢到了她的前头,将一只手递给她。她也没有犹豫,笑着接过了我的手。
现在没有风。长城西边无边无际的黄沙平静得像一个无波的湖。她望着黄沙,笑着对我说:“你愿意听我唱歌吗?”我笑着说:“好。”
歌的名字叫《曾杨柳》。她唱得如风拂柳。
羯鼓声里沥新酒酒暖恰入喉
满街正唱折杨柳夕照飞絮惹得回忆皱
曾经君也折杨柳我也折杨柳
千万杨枝折尽后走的人只留思念悠久
唱至高潮处,她稍稍加大了声音。句与句间隔很长。她浅唱一句,我低吼一句。
那些年我们腰间藏着剑仗剑觅封侯势作狮子吼
那些年我们眉上写着愁一雨便成秋踏风上重楼
时白发未生轻狂尚有且听风听雨听日奔月走
我们向着天下伸出手说一生一战?说不死不休
低垂的柳条随歌而动。柳色翻涌,从南至北,吹成一场春风。歌越唱越悲。她眉眼越笑越开。笑至最灿烂处。她说:“送他入伍的时候,别的情侣都是姑娘唱着《折杨柳》相送的,可我生来不会唱歌。我有些难过。他笑着折了一枝杨柳说,等你能够完整唱完一首《折杨柳》的时候,就是我归来的时候。他拿走了我的发钗,把杨柳枝簪了上去,转身走了。我等他的时候,就很努力地学唱歌,还学了琵琶。可我学会了三百《折杨柳》,唱哭了自己,弹断了琵琶,却还是没有等到他。”
婆婆伸手拔下了头上的两根木簪。我才注意到,原来这发簪是已经断成两截的杨柳枝。表皮早就脱落了。但可以看出被精心保养过。婆婆张开双臂,任春风从身旁吹过。可春风太柔,既吹不动她被岁月染白的枯燥头发,也吹不起她身上年老畏寒之人常穿的粗布棉裙。婆婆笑着问我:“我是不是太胖了?以前他就老说我胖。”我笑着说:“哪有。”我上前两步,像帮桃花梳头一样帮她整理头发。婆婆很开心,又唱起了歌。
多年后你说在山中相候花红正合嗅酒浓适醉游
多年后我说一别音容朽心老白马瘦不如恩怨休
时白发尽生轻狂依旧又听风听雨听日奔月走
我微笑向着你伸出手说时光尽头说不死不休
我小心地帮她盘起长发,从她手里拿过两截断裂的杨柳枝,轻柔地簪到她发上。她唱至最后一句。
恍惚又回初见时却抚了斑驳甲胄。
春风缱绻,招来一场春雨。我左手扯起大麾,替婆婆遮雨。
婆婆说:“有人等你吗?”我说:“有。”婆婆说:“趁能回去早点回去吧。”我没说话。婆婆笑了笑说:“那时我还不懂事,就想着要嫁个盖世英雄。跟他讲,他要娶我就得打下洛阳。其实我都不知道洛阳城门朝向哪儿。后来他们真的打下了洛阳。”我说:“婆婆,我送你回家吧。”婆婆笑了笑:“我家在锦官。”我说:“你是自己走来的?”婆婆点头。
雨点轻柔地落在我脖颈里,有些痒。锦官离玉门关,是一千里还是两千里?
我说:“那我就送你回锦官。”婆婆笑着摇了摇头。我说:“我认真的。”婆婆说:“我也很认真。”我无奈说道:“婆婆今年有十八吗?”婆婆很认真地回答我:“我离十八还差两年。”我摸出了钱袋递给了婆婆。婆婆从中拿了一两银子又把钱袋递给我。我说:“我是个说书人。这就当我买你故事的钱。”婆婆瞥了我一眼说:“我这故事又不是只卖给你一个人。”我只好接过钱袋。
雨停了。婆婆让我放下给她遮雨的手,又替我理顺了衣服。她挑了挑眉说道:“他曾经对我说过,若他死了,那天下何处不是我的家,何人不是我家人。你说对吗?”我不知道对不对,但还是点了点头。婆婆莞尔一笑。弯弯的眉像一对雀跃的黄鹂。只可惜少了一行白鹭,直上青天。
婆婆说:“之前我把故事卖给一个诗人的时候,他送了我一首诗。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你说写得好不好?”我说:“写得真好。我也曾听过一首。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婆婆喃喃念道:“何须怨?何须怨!何须怨……”她望着直至天尽头的黄沙,一时间竟痴了。等回过了神,婆婆问我:“你会去外城吗?”我说:“会。”“那你能替我捎一封信吗?”“能。”婆婆从怀里取出一封褶皱泛黄的信,温柔地印了个并不明显的唇印后递给了我。我双手接过。婆婆别过头,转过身,说句谢谢,拄着拐杖蹒跚下了城楼。
走去城门的时候,我路过刚刚吃饭的混沌摊,听见了那对父子的说话。
“爹。你都在这卖了三十年馄钝了。还要卖到什么时候?该回去了。”
“你个浑娃儿,你懂什么。要回去你自己回去。我一个人又不是不行。”
“是是是。您没老,您一个人很行。别一说这您就生气啊。”
“你一天问一次,烦不烦?我能不跟你急?”
“好好好。我不问了。”
“早就说了让你走。你个大小伙子待在这干什么?跟个废人似的。”
“爹,我不让你回去,你也别赶我走。”
我忽然想起老王头少有的正经时候问我的两个问题。
国门究竟是怎样一扇门?
国人究竟是怎样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