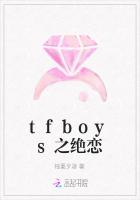有人或许会猜测,渐进地走向三方合作,或者更普遍地说,“社会伙伴”在公司监事会中的重要作用预示着社团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迎来了第二春,甚至还包括大多数其他欧洲大陆国家。那么前文介绍过的反映社团主义程度的统计数据能否证明这种趋势?在“二战”后的数十年中,有数据表明公共部门的地位在几个国家有所提高。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德国也有这方面的普查数据,1933年,德国的公共部门雇员占全国雇员总数的9%,到1938年提升至12%,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队的扩张。到1960年,这一数据依旧为8%,但是到1980~1981年,却已增长到15%。公共部门的规模已经高于20世纪30年代和平时期的社团主义经济的水平,这非常引人关注。另一个反映社团主义的惊人数据是政府总支出的增加,包括购买消费类产品和服务以及购买资本品(如厂房和设备)的支出,在同一时间跨度内,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60年的32.5%提高到1981年的49%。意大利的公共部门雇员比重从9%增长到与德国相当的15%,政府总支出从30%增长到51%。德国当时的数据几乎达到了峰值,到2006年,在经济严重下滑前,德国的公共部门雇员比重下降到12%,政府总支出的比重降至45.5%。而在意大利,这两个指标反映的政府规模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达到新的峰值,到2006年,公共部门雇员比重依然在15%左右,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则减少到49%。至少在西方国家,这些统计指标显示政府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似乎证明欧洲大陆的社团主义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更具影响力了。此外我们应该很想了解,与某些参照国家相比,这些欧洲国家的社团主义性质是否更显著。
法国的社团主义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的时代,从现在来看,以各种反映社团主义的统计指标测算,法国与意大利或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没有多大区别。法国的公共部门雇员比重也在上升,从较高的起点13%提高到1981年的16%乃至2006年惊人的22%。法国政府总支出的起点也更高,在1980年达到和意大利相近的49%,到2006年更是进一步提高到52.5%。
这三个国家在反映社团主义的另一个指标(政府审批)上的表现如何?根据1999年的调查,法国在这方面与意大利相当,超过其他国家。德国的审批较少,但明显多于英国和美国。
法国和意大利的劳动关系在外国观察家们看来依然充满冲突,而工会则抱怨说它们并没有公众想象中那么大的权力。法国在2008~2009年危机中爆发了大量“绑架老板”运动。法国的大罢工(令人恐惧的示威活动)有时会造成经济瘫痪,意大利与之类似,只是程度略轻。至少在公开的议论中还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比法国更反感“市场社会”、对商业活动更为疏远。
回溯这三个国家“二战”之后的历史,影响最大的社团主义发展现象似乎是工会的崛起,其政治权力的影响已经和产业利益集团相当。劳方的势力并没有超过企业或公司的势力。在产品市场上,总体的垄断程度甚至显著增强。工人和投资者可以通过工会、公司和商会等非市场渠道发挥作用,对经济行为和发展方向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通常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由此导致公共部门的活动大幅增加,监管规定越来越多。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新制度及其伴随的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通过何种途径限制了变革和创新?为保持稳定和维护现状,给产业活动的回报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在英国也出现了与法国类似的社团主义趋势,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才转向。公共部门雇员的比重在1960年已达到15%左右,高居欧洲之首,到1981年更是迅速蹿升到惊人的23%。英国的政府总支出规模在1960年与意大利和德国相当,到1981年提高到47%,略低于意德两国。然而到2005年,英国已降至45%,明显低于意大利的48%和德国的47%。20世纪80年代英国发生的变革在近年来的研究越来越多,那场使英国分裂了整整10年的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论并不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因为英国的国有企业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是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最小的,从“二战”结束到今天,一直维持在1.3%左右。那场争论其实是针对社团主义的,在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任首相之后爆发。
如今很难想象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当选给雇主们和工会带来的冲击,她给出的令人振奋的自由市场和放松管制的药方使英国在“二战”后的历史上出现了最活跃兴奋的时期。
英国工业联合会在当时被撒切尔政府边缘化,由于高利率和强势英镑加剧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衰退,很多制造企业陷入困境,很多会员感到恐惧。但随着经济改革措施和严厉的工会法开始生效,社会上的态度出现软化。与撒切尔关系良好的詹姆斯·克莱明森爵士(Sir James Cleminson)做了很多工作,以消除工业联合会总是寻求政府扶持的嗷嗷待哺的原有形象。他在1985年说:“产业界人士开始承认,要求政府做的事情中有4/5其实是可以自己做的,他们希望政府做的就是铺好道路而已。”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态度延续至今。
在这段时期之后,英国逐渐改变了社团主义立场,脱离了以法国为首、意大利紧随其后的传统阵营。根据1999年的统计,在西方七国中,英国阻碍企业发展的官方审批数量远远少于其他国家。
最后,我们来看看社团主义在美国的影响。1960年,尽管经历了战后的大规模裁军,但美国的公共部门雇员占全体劳动力的比重仍高于英国水平,是西方七国中最高的。到1980年,美国的这一指标虽然被英国超过,但依然高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相对而言,在政府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一指标上,美国在1960年仍居中游,仅为27.5%;到1980年更是西方七国中最低的,为35.5%。在官方审批数量方面,美国在1999年显著低于意大利、德国和法国。
在刚过去的10年中,社团主义在美国的影响肯定有所上升。联邦要求的监管规范的数量持续快速增加。有证据表明,某些新的监管规定降低了企业从事具有不确定前景的新项目的意愿,如《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要求首席执行官为公司提供的会计方法承担法律责任。
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在个人所得税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1981年的里根减税法案消除了各种税收征管漏洞,给政府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以弥补税率结构下调的损失(涉及从最低到最高的各档边际税率)。然而,税收漏洞以及使特定个人和企业受益的法规却越来越多,美国的税法长达16 000页,而法国税法只有1 900页。
美国的另一个惊人发展趋势是诉讼的大量出现和随之而来的对诉讼的恐惧。虽然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美国人可能没有那么多工会保护自己,但他们今天能够借助庞大的法律体系和法院系统保护自己在社会对变革和进步的不懈追求中不会被他人置于不利位置。对于诉讼的担心给个人的行动和判断造成了显著影响,并涉及创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