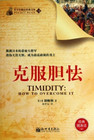那天晚上,我基本上没有睡着,脑子里老是回旋着公路、大雾、汽车、过阴、那边的世界等等乱起八糟的东西。
奶奶那个故事我将信将疑,这和我历来接触到的“阴间”概念毫不相同,在我们惯常的阴间概念中,有阎王判官牛头马面无常小鬼,十方地狱阴气森森,鬼哭狼嚎,恶人要受难,好人要投胎富贵,要过奈何桥,要喝孟婆汤。
可是,在奶奶的过阴故事里,这一切全没有了。阴间的世界和阳间的世界毫无区别,有城有镇有住户居民,还有做小生意的,搞运输的(抬轿子),同样是贫富悬殊,同样过普通老百姓生活。唯一不同的是,那边没有太阳。
那样的阴间就如同不存在于地球上的另一个时空,或者说另一个星球,拷贝了地球的一切,仿若世外桃源。
我的思想越来越混乱,身边的胡知道同学却没心没肺地熟睡过去,发出了抑扬顿挫的鼾声。
在我的想象中,鬼魂应该只是一缕意念,一束脑电波。而我们活着的人就如同一台调频收音机,如果你的波段正好和那个鬼魂的波段相同,你就可以“接受”到这个鬼魂,从而出现“见鬼”这样的事情。
鬼是不应该以实体形式存在的!
可是,奶奶的故事……
我想起了魔法橙子讲述的九姨太的故事,那个故事里,有个来自唐朝的丫鬟也曾经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空间,那个“镜子空间”有各种颜色的浓雾。会不会那个地方也是一种“地狱”,一种存在于我们想象之外的空间。
我的想法越来越混乱,脑袋不由又开始疼了起来。在高速公路上,我们丢失了那枚从木渎女船主那里弄来的玉蝉,这枚玉蝉莫非也掉到我们想不出来的空间里了吗?
这个宇宙,或者说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莫非还存在着无数看不见摸不着的异度空间。
汗,我拧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再这么下去,我快成科幻大师了。
旁边胡知道“嗷”地一声大叫,坐了起来。
我说:“你干什么?”
胡知道惨叫:“银子,你掐我腿,我疼!”
我哑然,怪不得自己没有痛感,原来掐的是胡知道同学的腿。
我说:“哦,没什么事那你继续睡吧。”
胡知道同学反而起身披起衣服,坐在那里发愣。我说:“你怎么不睡啊,你要不睡我可睡了。”
胡知道说:“银子,我刚刚做了个奇怪的梦。”
我心中咯噔了一下,这两天我最怕听到“奇怪”“离奇”之类的字眼了,我说:“有多奇怪,你说来听听看。”
胡知道愣了片刻,忽然问道:“银子,你说,兔子会不会抽烟?”
我哑然失笑,这家伙脑子坏特了?问这么稀奇的问题,我说:“兔子要是会抽烟,我家胡知道就会飞檐走壁了。”
胡知道说:“知道你不信,我跟你说,我梦到咱们在高速路上开车来着。”
我拍拍他的脑袋:“乖,看来你白天被吓坏了,来,姐姐疼你。”
胡知道挣脱我的怀抱:“和你说真的呢,银子,我梦到开车撞人。”
我诧异:“撞人?我还以为你又梦到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雾呢~”
胡知道说:“不是,当时我梦到咱们在高速公路上,阳光明媚,可是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就像美国西部一样荒凉,我使劲踩油门,速度表上已经越过了红线区,车身却还没有起飘的感觉,我就想这宝马果然非同一般,好车啊。高速路两旁的护栏飞快地后退,看上去就像一条模糊的飘带,你坐在我的身边,打开车上的音响,我清楚记得,那是一首潘玮柏的老歌,什么你是高手我是庸手的,节奏挺劲爆。正听得来劲,车前方不到二十米处忽然出现一队人。那队人穿着麻衣,头缠白布,打着经幡,散着纸钱,人群里幽冥诡异的哭声传过密封的车身,似清楚似隐约地传进了我的耳朵。”
我说:“扯什么呀,高速公路上怎么会突然出现送葬的队伍?”
胡知道白我一眼:“我这不是做梦嘛!当时我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根本来不及多想,就看到一个长头发的女人在我的车头飞起,接着是一个孩子血肉模糊的脸摔向前挡风玻璃。咱们车子上的雨刮器自动打开,将血水和孩子的碎脸刮开去,血丝满布的脸上有一双始终圆睁着看着我的大眼睛在玻璃上缓缓移动……”
我听得冷汗直冒,胡知道这猪头形容得也太仔细太血腥了:“然后,你就被吓醒了。”
胡知道说:“我是被吓醒了,但不是你理解的‘醒’。”
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当时我发出一声惊叫,就一身冷汗地坐了起来。心想妈的,原来是个梦!身周的光线有些刺眼,我转头去看睡在旁边的你,一看却看了个空。强烈的阳光伴着蝉鸣从四面八方朝我扑过来,我这才发现,自己坐在一张浓荫下的竹榻上,时间分明是正午。”
“这怎么可能呢!我明明记得昨天晚上和你一起睡觉的,你还嘀嘀咕咕和我说了半天话,怎么回醒来却独自一人睡在一张竹塌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头上翠盖浓荫,几棵老大的榕树将阳光阻融在外,前面是一间稍微破旧的老式平房。感觉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然后屋子里走出来一个女人,穿着干净朴素,衣服的款式都很老旧,提着个圆圆的仿佛我们家多年前用来装酱油的塑料壶,壶里灌满了水。她一直走到我面前,我这才看清楚了,是我妈,但精神旺健好象年轻了十几岁。我刚欲开口,她将壶递给我,朝我咧嘴一笑,说‘道道,该上学了,开水里加了蜂蜜’。银子,你不知道我听到这句话有多震惊,我只觉得后心发凉,记忆的阀门一下洞开,这完全是我小时侯的场景啊,老屋,大树,睡午觉的竹榻。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伸手去接那个水壶。但是,我的手,那双还显着稚嫩小手!是我的手?
我心中仿佛被巨大的铁锤一下又一下地撞击,低下头,看到我弱小的身子!我的小脚!我穿的小号衣裤!我开始头晕目眩,狠狠在自己胳膊上掐一下,那疼痛感却十分真实!那一刻,我真的是怀疑自己回到了少年时代?”
“虽然我曾经无数次地梦想回到童年,回到无忧无虑的快乐年代,不用担心学习,可以捉弄那些捉弄过我的人,弥补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然而这一刻真的如梦幻般降临后,我的心里乱成一团麻,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应付,心里溢满了无助。已知的一切也变得深不可测。我回到小时候,那现在的家会不会失去我,银子会不会失去我?容不得我多想,母亲上来给我一个爆栗,说‘你发什么呆,上学去!’我慢吞吞滑下竹榻,左手忽然一紧,别过头,是被另外一个小孩子牵着,他兴奋地说,‘原来你和我一样,还没走啊!’我搜肠刮肚,不记得小时候有这么一个朋友,冷冷问,‘你谁啊?’无奈童音稚嫩,语气上拉不出那种冷冷的距离。”
“头上又吃了母亲一爆栗,‘道道,死小子,睡糊涂了,快和宝龙上学去!’那个叫宝龙的流着鼻涕的恶心小家伙理直气壮拖起我就跑,转过村子是一条两旁长着高大水杉树的小路,沿着路边是一条小河。我觉得被宝龙拽着的手粘粘的,也不知道他拿这手擤过鼻涕没有,我用力挣脱。宝龙忽然指着我的脸哈哈大笑,我懒得理会他的举动,自顾自看着清澈的河水。宝龙在我身后拍手,‘鼻涕王,长又长,流进嘴,吐一缸。’我头脑里依然纷繁错乱,懒得听这小家伙罗嗦,解下别在胸口的手帕反手递给他。宝龙笑声加剧,捂住肚子打迭,两条恶心的鼻涕随着颤动不已,我刚准备开口说话,猛觉嘴唇一甜,鼻子很自然地用力刺溜一吸。妈的!宝龙说的是我,我鼻涕拖得比他还长。”
“我将擦鼻涕的手帕随手扔进小河,顺水浸润下沉,这条小河在我的记忆里也很淡薄,若有若无。河的两边有很多嫩绿的浮萍,一块一块随波荡漾。河边稀疏的树丛漏下的阳光在河面上间隔铺就金色鳞片。是我的童年吗?我转过身来,宝龙这孩子已经脱得一丝不挂。我说:‘你干什么?’他说,‘不是游泳吗?’‘你不上学了!’我想敲他一个爆栗,却够不着他的后脑勺,我比宝龙还矮小!”
“我坚信宝龙不是我童年的玩伴,我也曾在上学的路上脱掉衣服去河里游泳,我隐约记得那河面上老散落着几只麻鸭,四五个活动的脑袋,那才是我的伙伴,可是他们的面孔,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道道,你发什么呆,快点下来。’宝龙嘿嘿笑了起来,眼睛里闪动着一丝妖异的光芒。天,我忽然想起了了,我认得这双眼睛!在梦里它曾贴着我的车窗玻璃滑落……‘你到底下不下来?’宝龙开始着急起来。我不下去他着什么急?我顿时觉得这个叫宝龙的小孩子居心叵测,想在水中谋害我。不敢再盯着他的眼睛看,那里面似乎含着一股魔力,仿佛能随时生出一双又长又细的手来将我拖下水去。我转身就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