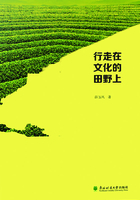施晗
天也有一双眼睛,到底是人在看天呢,还是天在看人。
夜里的天,早晨又活了。
巷道里平时跻身的一群乞丐,这时本该斟杯碰盏,共进午餐,此刻,是因为凄厉的风带着寒意,也带来了冬天,促使他们重又蜷身一团,遥望蓝天。
“天是圆的么。”一个人说。
“不,天是无边无际的。”一个人说。
“天用光速可以测出它的距离。”一个人说。
“天就是我。”一个人说。
“天还是天。”一个人说。
他们说的极为认真,仿佛在为真理定义。
我不去理会,暂也不去给他们的结论作一番自嘲,安静地上了楼,找那么一间地方谪居读书,让灵魂自发去打发生活的繁文缛节。
窗台透出点点余光,走过座位,爬到书页,停在我的脸上,最后,点亮整间晕暗的房屋。窗帘拉过,只有惟一的一线隙缝给了阳光可乘之机;我心中一动,觉出阳光好像有了生命,它启迪着什么,又暗示着什么。印度大文豪泰戈尔,每天早上对着初升的太阳,静坐沉思,幻想与天地同体,宇宙合一。我从未修炼到这样的境界,可我能感受到天的眼睛的威力是能洞察三界,透视万物。这个伟大的发现,使我陡然兴奋起来。我干脆把所有帷幕都拉开,外面竟是一片纷飞的白雪,天被遮住了,只有纷纷的云落下的眼泪。这是何时的事,就在刚才,仿佛我的一举一动都被天监视着,来不及思索。这雪是为我下的么。
“一年倏就除,风物何凄紧。百岁良悠悠,向日催人尽。即不为大椿,便应如朝菌。一死息群生,何处问灵蠢。”
农人兴许已在家中烹羊烤肉,以祈求来年的丰收,天对他们来说,有时是多好的征兆,一年的望穿秋水,也许就等这么一天,可谓“渭城朝雨挹轻尘”。且说我自己关于天的鉴别,总觉都是与地相关的。古人虽说以天鉴地,行事讲天时、地利、人和,而人的行为或者是天“发号施令”的根本原故罢。
天的怒狂,风雨大作,冰雹交加,导致黄河决口,写下过多少痛苦的回忆,睁开眼闭上,你明明记得是一场梦,天却把你作弄得狼狈不堪。事实追溯起来,到底是人自己在作祟。人多了,得罪天,气温就升高,人又砍树,造厂,灭绝人性的杀生敬自己,绿色少了,污染多了,动物少了,人又多了,疆域并没有辽阔,地球并没有变大,天可就膨胀了,天哭起来,眼泪变成了风雨冰雹,人却拍手高叫,人是多么的无知啊!
“行事预见天命,随机顺势而作,增善减恶,得被苍生,万物皆兴。”我竟有了诧异,终于慨叹,慨叹存在神秘,已身的微弱;漠漠的天空有了这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才使得它这般充实、丰满,才所以叫天,人们才看不见它,是该为它鼓掌,还是为它低徊。
我侧过头,一转瞬间,阳光又不见了,一片阴影在楼群砖瓦中停留。风光如旧,四季不同。对面的窗台探出一个女孩,她行动缓慢地提起水壶,给海棠浇水,水溢出来,从四楼往下漏,女孩抬头看看天,似在向天陈诉什么——在白杨和梧桐的缝隙里,一块块黄色天空。几只野鸟正俯冲,飞翔在这样的天空里,一条弧影落在湖里,清晰可见,宛如镜中花,水中月。阳光又露出了脸,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我怀疑她是不是和小说中的情节一样,是个盲童。
我有心,却不敢到对面探望,我几次穿过楼道,也从没遇见她,她还是每天都会看天,我却不一定经常去对面楼上写作。她的眼神一直告诉我,天是神秘的、充实的,她深深爱着这天,懂得这天,也只有这天爱着她,懂得她。
几天下来,天突然变的阴沉,就像扳着的死人面孔,既没有阳光,也没有风,更不会来一场雨,冲刷你无穷无尽的悒郁,天并不懂人心。
“天要死了”一个猎人委屈地说。他一定在诅咒天,天阴下来,鸟也不出来了。我知道,这鸟儿一定在感谢天,使它看见了猎人的狰狞。我对着天苦笑了一声,天应该是人性的一面镜子呢。就在这时,不远处一辆轮椅,划过我眼前,车上坐着楼台对面的女孩,推着车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车经过我身旁,我冲女孩友善地一笑,她目光呆滞,面无表情,永不曾知道我关注过她。女孩不时伸出手指向天空,男人应声附和,直到走远。只道他们是对好的夫妻或是朋友,天应该知道答案。无穷无尽的悲凉徒然袭上心头。我又把头抬了抬,仔细地看了一眼天空,天是多么明净,多么浩淼,多么有吸引力,似要把地球上每一个生灵都装进它的怀抱。
我记起一位作家的话了,天地是互相的镜子,人与人是互相的镜子。天又何尝不是人的镜子呢?在这面镜子里,人偶尔近乎于温驯,又偶尔近乎于残忍,但人的本性才表现了出来。我们常常看天,却不知道天到底能给我们什么,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举动。而人本身又在这种可笑里成长;爱情、亲情、友情,无一不在天的包容里滋生。对于天与人,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我真觉得,人生毕竟是非常可爱的,这点感情在我文学的作品里,我也从不隐讳什么,甚至到老去的那一天,我还要在天的眼睛里怀古追今,对月作文。
拐过巷陌,我看见那群乞丐还在一起说天,怡然自得,只可惜天看懂了他们,他们却一直没看懂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