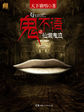这顿晚餐,在本城最高档的饭店,五星级,大凡小城,这样的饭店都是屈指可数的。妈妈很满意邵杰的安排,“邵杰一直很看重你的。”芹芹听了也只有笑笑,难道五星级的饭店一定搭配五星级的人?母女俩到得早了些,在饭店大堂角落的咖啡吧里坐着,妈妈为自己把时间提前半个小时的事辩护:“我知道你做事喜欢拖拉,说五点半,铁定你六点到的。”她们以为自己坐得很隐蔽,但邵杰一进门,就抬起手和她们打招呼了。芹芹真想假装没看见,妈妈却已经飞快摇手回应了,芹芹也只好点头微笑。
“我记错时间啦。你看,我老糊涂了!”妈妈急着解释。
“没有啊,我是说过请老师和师妹早点过来帮我点菜的啊。”邵杰说得认真。
“你说过了?”
“说过了。真的说过了。”邵杰落后一步,对着芹芹挤眼睛。芹芹对他摇摇头,耸了一下肩。这是他们“那时候”的动作,用来嘲笑父母们迂腐或者蠢笨的。
半年多了,妈妈已经动员不少芹芹的同学朋友来给她安排相亲,芹芹一概不领情,连同学假装聚会把她约出来相亲,芹芹也明察秋毫,都婉拒了。这一次,算是邵杰请她们母女,芹芹只能跟着来。邵杰是芹芹初恋男友,她恋爱得早,高一就开始了,而且就在她妈妈的眼皮底下,芹芹猜想邵杰也一定深感刺激,居然跟自己班主任的女儿谈恋爱,还可以仗着“得意门生”的身份时不时上门“做客”。他们是谨慎的,相信没有一丝痕迹落在父母眼里。芹芹从上大学之后所有的恋爱都是对那两年谨慎的补偿,大大方方,恨不得天下人都知道了。和邵杰分手的理由很简单,高二下半学期,隔壁班一个傻乎乎的女生老是来找邵杰,邵杰居然也应承,当着芹芹的面两个人谈得很投机的样子,没多久,芹芹就要求分手了。邵杰很委屈,也赌气,说:“禁不住你这么闹!”芹芹说:“我闹了?我哪里闹了?”因为谨慎,连吵架也吵不开来,一段恋情就这样郁郁而终,也正因为没有吵开来,多年以后,当时的情形倒成了落进贝壳的沙砾,渐渐圆成一颗珍珠了。要不,芹芹也不会跟着妈妈来吃这顿饭,妈妈的心思,她自然是知道的,所以,她故意穿得比平时还黯淡些,灰色套头衫,暗蓝牛仔裤,素着一张脸。
一桌人坐满了,临时还加了个位子,一个听到消息的同学主动要求赶来吃饭,是当年班上最顽皮的,现在成了本城一个半大不小的老板。除了两个邵杰带来的朋友,其余都是同学。“我不会喝酒,你们又不会饶我的,只好带两个保镖来。”邵杰是这样介绍那两个男人的,一个和他们年纪相仿,叫颀伟,一个比他们年轻五六岁,叫美良。到他们这个年纪,才会感觉出五六岁的差距确实是个差距。四十岁是个不大不小的坎啊。女同学也来了三个,都是平时和芹芹还算相得的,芹芹这个人,向来是与男同学相处得更自如些,她们都穿得鲜艳,一见芹芹的素装,就齐声夸她:“我们这个年纪,也只有芹芹这样的还镇得住灰灰蓝蓝,像小姑娘一样!”芹芹有点撑不住,索性连谦逊也省了,只是笑笑,举起手中的红葡萄酒,为她们的赞美干杯,连声说:“谢谢谢谢!”妈妈在旁边拉她衣角,她僵僵地坐着,只当没感觉。
妈妈的视线时不时落到颀伟身上,还问他名字的写法,问了他之后,又问美良怎么写,说两个都是好名字啊。邵杰说:“吴老师这是语文老师职业病哈,不过,也幸亏吴老师这一问,我一直以为颀伟是奇伟呢,你看,我手机上存的号码就把它存成‘奇’了!”一边就拿起手机让吴老师看。芹芹看着她妈妈。吴老师把手机举得远远的,看了,说:“邵杰,你看,你犯错误了吧?”邵杰说:“那个颀长的颀字,很少有人把它拿来当名字吧?”妈妈说:“你忘啦,芹芹的女儿不就叫颀颀吗?我们取名字取得不用心,芹芹颀颀的混叫。颀伟这两个字啊,是正宗书面语,你查查字典就知道了,形容身材高大魁梧的。你看,人家父母多用心啊。颀伟,你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吧?”颀伟说:“爸爸在大学里教历史,妈妈是高中语文老师,跟您是一样职业呢。”芹芹忍不住了,她说:“我们取名字哪里不用心了?你把我叫做芹芹,我们取了一半,又加上新的一‘页’,可不就成了颀颀了?”她妈妈看看她,不说话了。
只要来一场新的恋爱,旧的伤痛就会被覆盖,这是妈妈总结芹芹年轻时谈的那么多次恋爱的结论。芹芹的恋爱谈得叫人心悬悬,总是热火朝天地开始,冰冷凄惨地收场,然后再热火朝天地开始,这开始的季节,往往都是在深秋,结束的季节倒是不一定的。芹芹对妈妈是坦白的,总会说一声:“我恋爱了。”后来次数多了,就变成“我又恋爱了。”或者“我有男朋友了。”二十八岁秋天开始的那一次,从谈恋爱到结婚,顺当得让妈妈吃惊万分。怕芹芹那些不到一年的短恋爱的惯性会对婚姻不利,妈妈倒也费了些心思跟芹芹说过一通婚姻如何与恋爱不同,离婚如何会伤筋动骨,芹芹说:“我不想过动荡的日子了,安稳结婚真的很好。”妈妈到底还是不放心,盯女儿盯得比她丈夫还紧,直到有一回听到芹芹劝导她表妹:“谈恋爱就是那样,伤身耗神,我想都不敢想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他那么认真求婚了,你也就答应了吧。”妈妈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谁曾想十六年之后,这颗心又得悬起来啊。
迟到的那位老板同学一落座就说:“我知道邵杰只会给老师吃普通鱼的,什么鲳鱼带鱼梅童鱼,顶多再有虎头鱼,哦,还有醋溜鲨鱼羹。”众人都笑了,他报的菜名,居然跟上过桌的一个不差。他说:“我给大家吃款稀罕鱼。刚才我先去了厨房,问过厨师长了,今天有没有不上菜单的好鱼啊,他说有,我就让他添了!”很快,稀罕鱼上来了,邵杰说:“这不是箬鳎吗?”老板同学说:“不懂了吧?是比目鱼哪!箬鳎有这么大个儿吗?这家伙是深海来的呢。” 颀伟说:“叫它比目鱼,也对也不对。比目鱼是鲽啊鳎啊鲆啊鲣啊几类鱼的总称,它们那两只眼睛越长越到一块儿,都移到头部一侧了,有的在左有的在右,另一侧平平的什么也没有,平卧海底正好。这条啊,是箬鳎的兄弟卵鳎呢。”邵杰笑了:“怎么样,没话说了吧?人家海洋研究所出来的。”那个叫美良的插话说:“叫比目鱼多有诗意啊,不是有古诗吗,‘愿成比目不羡仙’,你们这些做研究的,真没意思。” 颀伟认真道:“那是诗人臆造的,比目鱼绝对不像鸳鸯,非要雌雄相随的。”美良说:“拜托啊老兄,给我们保留点美感好不好?”颀伟这才醒觉过来,说:“不好意思啊,职业病职业病,自罚一杯!”仰头一杯红酒下去。老板同学不接话茬,开始敬酒,轮着敬了一圈,还嫌不过瘾,又来了一圈,都把红酒喝成果汁了。都是那条鱼闹的。芹芹家的沙发靠垫就是比目鱼的造型,芹芹结婚时买的,两条鱼姿态优雅地贴在一起,看着就让人安心,以后靠上去的时候就得想,这不过是箬鳎啊,还真有些吃不消。
饭吃完了,邵杰就是不让老板同学买单,说自己早就签好单子了。同学们都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邵杰是单位一把手,签单是他分内事。老板同学直着脖子叫:“下个节目唱歌,一个也不许走,走就是看不起我这个差等生!当然,吴老师要早休息的,我叫我司机送她走!”
邵杰说:“光包厢费就涨到6000元一夜了,你就不心疼?”
芹芹说:“我也得走。我得去接女儿。”
妈妈说:“今天周末呢,我去她奶奶家接到我家住一晚吧,我也很久没跟颀颀热乎了,你就安心玩吧!同学聚会也难得的。”
老板同学扯住芹芹:“怎么?邵杰的饭你吃,我的歌你就不唱了?”芹芹就跟随他走了,她不是屈从于他的霸道,而是那霸道底下的什么柔软的东西,让芹芹起了怜悯。她已经很久没有怜悯别人了。
走到饭店门口,桂花香潮涌过来,隔了桂花林,娱乐城的霓虹灯闪个不停,灯如星,密布墙身,像个水晶棺椁。红酒有点上头了,芹芹耳朵里血液在流,刷,刷,刷刷,刷刷刷。她目送妈妈上车而去,妈妈摇下车窗,一脸要给女儿许多提示的欲说还休,芹芹胃里一阵翻涌。难道死去了的女婿就不再是家人了吗?他曾经那么用心地做了好些事来讨丈母娘的欢心,难道人走了,那些事,也都毫无意义了吗?恍惚间,芹芹觉得他就站在身后,冷冷地把这些问号打进她的思绪,这一转念,又使她愤慨起来,她转过身去,想质问他:谁叫你自己这样离开的?!身后空无一人。面对这虚空,她突然可怜起妈妈来,妈妈是奔七的人了,总害怕“不知还有几年好活啊”“说不定明天就眼歪嘴斜了呢”“万一老年痴呆了那可怎么办”,所以才急着想把女儿丢失的“幸福”再找回来吧?现在的妈妈怕都是不稀罕从一而终的贞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