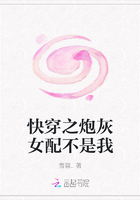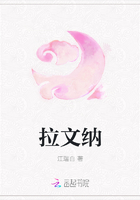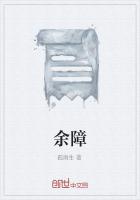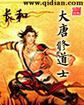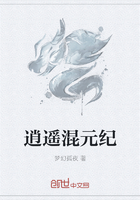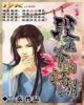一
五四文学影响深远,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从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再不可能恢复到传统样式,五四文学又是独特的,五四文学的新型文化角色并没有得到延续,五四之后的中国小说和中国文学进入一种现代中国特殊的文化样式,而且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上没有返回五四样式。
这样,我们就必须分辨三种文化样式:传统样式,五四样式,五四后样式。
从我们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样式的主要特征,是文类意义权力的金字塔式划分,为保持这个结构,关键的问题是维持文类等级,尤其是维持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分野。
这个分野在古代中国社会中起先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亚文化没有书面文本,而中国文化自从“书同文”之后,语音与口语的变异和发展很难影响文字,这个文化成了全世界最“书面化”的文化,书面文字历千年变异很小。
口头“文本”虽然能用师徒传授记忆方式代代相传,但传授不可靠(变异散逸可能性太大),渊源也不可考(作者权威性难以确认)。在先秦时期可能口头书面并存为文本流传途径,因此在西汉造成了古今文之争。从那以后,中国文化中就只有版本之争而不会再有口述文本与书面文本抗衡之可能。口述文本已成为不具有历史性的文本。优戏,说讲,历史上一直有记载而无记录。歌谣因为短,一直有少量记录,却是风俗志、谶纬、野史等其他文类的附笔。《诗经》中某些篇什保留不少口语痕迹,但到汉乐府诗后,口语成分就相当弱(虽然名义上还是歌谣的记录)。
11世纪之前,中国的书面文化,基本上是匀质的。“口头文学”留在口头,与书面文化很少关联。这样一种文化结构中的口述文本,它的存在是即刻的,此时的,非积累的。如果说它也是社会文化表意的一种,那么它也是永远停留在亚文化状态之中,无责任,无权力,无历史,根本不算一个文化的文类。
可是,在这种状态中,它也得其所哉,与主流文化互不干涉,两得相安。主流文化一般说并不把自己的规范强加于口头艺术,而让它作为“化外之文”存在。“礼不下庶人”,也就是文不下庶人,君子小人之分,也就是书面口头之分。
宋元时期中国文化出现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书面化的俗文学。俗文学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系列两难之境中:俗文学不是口头文学(实际上既是“文学”就不可能是口头),也不是口头文本的书面记录,它只是假定在模拟口头文学。俗文学以书面方式出现,却不是书面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它是书面化的亚文化文本。这就是它的特殊文化角色规定性之由来。
口头“文本”因为几乎无存留性,可以免受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过强的压力。俗文学在文类等级上处于极低地位,却没有口述文本的自由度。俗文学的书面化,其代价就是不得不对主流文化规范表示尊崇。实际上,俗文学为了在中国文化的书面文类阶梯中取得一个地位,哪怕是极低的地位,都不得不对主流文化规范格外崇敬。
俗文学的出现,使主流文化规范得以往社会下层延伸,限制并控制亚文化,因此造成这样一种安排:主流文化允许亚文化有书面表达流动的权利,而俗文学也因其道德教化作用而被容忍。
这种文本间关系,元末明初文人领袖杨维桢在给文言小说集《说郛》写的序言中作了一个说明:
是五经郛众说也。说不要诸圣经,徒劳搜旁采,朝记千事,暮博万物,其于仲尼之道何如也。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约则要诸道而已。
杨维桢在此把“文以载道”论扩展到中国文化中新出现的书面文本分层格局上:五经为城,众说为郛(外城),众说必须让出中心地位,并且礼崇中心,无法“要诸道”的文本,则拦在郛墙之外。这城—郛—郊格局是皇城的典型设计,也是中国文化的文类安排。康熙这位道德家皇帝几乎把杨维桢的比喻变成了实际文化政策:
凡唱秧歌妇女……尽行驱逐回籍,毋令潜居京城……京师内城,不许开设戏馆,永行禁止。城外戏馆,如有恶棍借端生事,该司坊查拿转。
看来口述文本是被拦在郊外了,在那里它们享受着亚文化文本的某些宽容特权。只有在出问题时,官方才出面查问或惩治。
但俗文学的地位呢?如果杨维桢说的“郛”还是包括文言小说的百家杂言,那么白话小说更等而下之,它挂在郛城墙上,不上不下。慕史与教化是俗文学悬挂在这体系上的绳索,也是爬进城的希望。
这希望在晚清似乎得到实现,道德教化变成政治说教后,白话小说忽然登堂入室了。梁启超康有为等都认为,“小说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
这样做,表面上把俗文学招进了主流文化的文类等级,拉上了城郛,实际上政治宣传目的使传统小说地位更复杂化了。万一这个目的消失,白话小说的地位就突然下跌,落到城墙根,成为消闲文学。
二
五四运动改变了小说的文化角色,并非由于抬高小说的地位,而是由于把小说从中国文化的文类结构中移了出去。这样做,不仅改变了小说生产的文化机制,而且其势态是重组中国文化的文类结构——把金字塔式的文类结构变成多少是并列式文类结构。五四运动虽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但至少因为破坏了原文类等级,从而破坏了这结构的基础。
上一章说到五四小说叙述文本的个性化。个性化并没有使小说成为非社会的表意方式,相反,它获得了更强的社会性——它用一种离心的方式颠覆传统文类等级。
此时,小说成为主要的文学文类,代替了传统文类等级中诗词散文,是因为小说文本具有了足够的个人性和个别性,一部作品本身的优劣决定其意义价值,它属于什么文类,诗歌、散文、杂文、还是戏剧,已是很次要的事,甚至题材归属也并不是其真理价值的决定因素。文类价值让位给文本的个别价值,这就是五四文学迫使中国文化结构转型的机制。
但是,五四文学在另一个方面不但保持而且加强了文类等级,那就是雅俗之分。小说这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文类,现在截然分成雅俗两个阵营。出现同样分裂状态的可能还有戏剧,俗剧(地方戏)与新剧(话剧)几乎很难算作同一文类,旧派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五四小说的区别是叙述学上的区别,其分野更为内在。
此时的俗雅之分,壁垒分明。新旧二派作家,几乎完全没有来往。固然我们可以找到个别例子,某些五四小说家,原先受鸳鸯蝴蝶派影响颇深:例如施蛰存的第一本小说集《江干集》,例如张天翼在1923年前以“张无诤”或“无诤”笔名发表的小说,他们不久后就成为新文学中坚作者。叶圣陶和刘半农早期曾是鸳鸯蝴蝶派中人,但五四文学一开始他们就成为前驱者。除了这些偶然的个人联系之外,两派几乎从不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作品,甚至不在同一社交场合出现。旧派对新派偶有讥嘲,而新派对旧派攻击尤为犀利。不过,即使一位作者在人事上不加入社团派別,就作品本身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位作者属于什么派别。本书引言注中所说某些作品归属不得不存疑,大部分原因是笔者尚未找到该作品读一读。
这时的新旧之分,就是雅俗之分。俗文学不仅以商业利益为目的,以消闲为内容,不仅叙述特征基本上局限于传统方式,而且,最主要的是,它的文化模式是公共的、大众的、教化的(哪怕“黑幕小说”都以教化为题旨);与之正成对比,五四小说是文人化的,个人化的,其叙述特征由此而求新,而多变,而不易为喜爱程式的教育程度较浅的大众所接受。
五四时期小说的雅俗之分,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结构中的雅俗之分。属于雅的五四小说并不在文类等级之中,相反,由于处于反文化地位,破坏了这个文类金字塔,因此,这种雅俗之分,实际上是变革与传统之分。
五四时期作家,常自认为他们用白话写作,是在接近大众,因为他们用的是“引车卖浆之徒”用的语言。实际上五四小说的特殊叙述方式,相当脱离大众,完全不是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与晚清小说相比,五四小说明显地雅化,文人化了。不必否认五四小说是有“现实意义”的,许多五四作品是关心现实社会问题的,但与晚清小说之强烈社会性、功利性相比,五四小说是从社会现实后退了一大步。五四作家很少有像晚清作家那样用小说,或以小说家身份卷入政争,或在小说中提出社会改造方案。(鲁迅等作家卷入女师大事件,并与当朝的部长章士钊正面冲突,已是1925年的事。鲁迅的小说之笔就停止在那一年底,恐非偶然。)
因此,五四小说之文人化,与晚清小说之“文人化”很不相同。晚清热衷于小说的文人,除了个別的例外,都是有意用小说作革命或改良或道德教化的宣传,因此他们愿意,而且希望使小说保持传统叙述形式,以利于接近大众。这样做的结果,反而是保持了小说的亚文化地位,从而维持了传统的文类等级文化结构,不管晚清作家自认如何革新,他们的文学实践却是保守的。
五四小说与传统小说,与晚清小说之根本性的不同,不在于把小说从俗文学地位抬高,而在于用个人化的方式,使小说脱离了传统文化的城-郛-郊格局。这样做的代价,是雅俗的彻底分裂。
三
然而五四小说在雅俗问题上的态度,在1925年左右发生了变化,即“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化,以及30年代“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
1925年英国警察在上海租界枪击中国示威工人的事件,使中国知识界迅速走向革命化。革命文学的口号开始在一部分文学家中流传。在这之前,恽代英、邓中夏、沈泽民等革命工作者已经在1923-1924年间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他们要求“抛去你锦绣之笔,离开你诗人之宫,诚心去寻实际运动的路径”。并不是要求文学为革命服务,而是要求青年弃文学而从事革命,因此这些发表在政治刊物上的号召并没有在文学界得到普遍响应。1925年后的情况就不同了。蒋光慈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沈雁冰在该年发表了《论无产阶级文学》的长文。后来他在回忆中承认此文是他收集到的关于苏俄文艺论争的英译文之拼合改写,对象与其说是中国文学不如说是苏联文学,但其中提到了一个几乎是转折性的基本方向路线问题:
所以无产阶级如果要利用前人的成绩,极不该到近代的所谓“新派”中间去寻找,这些变态的已经腐烂的“艺术之花”不配做新兴阶级精神上的滋补品的……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文艺的遗产,反是近代新派所认为过时的旧派文学,例如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和各时代的C1assics(经典著作)。
他举的堪为无产阶级文学楷模的两种“旧派”文学,在中国不曾有过。公平地说,沈雁冰没有提出回到中国传统小说,但他预示了30年代关于大众文学和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诸种论辩的方向。
1926年郭沫若作的《革命与文学》一文,标志了从创造社开始的大规模向“革命文学”转向。郭沫若反对“文学无用论”,强调文学在革命中在历史中的地位。他对革命文学的定义用的是不容置疑的绝对口吻:
我们知道文学的这个公民中包含着两个范畴:一个是革命的文学,一个是反革命的文学。我们得出了文学的两个范畴,所有一切概念上的纠纷,都可以无形消灭,而我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就可以决定了……
这个简单的“画线”法也预示了此后大半个世纪中文学问题的处理方针。虽然如此,五四小说的最主要作家鲁迅和郁达夫,以及相当大一批作家,对“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依然持保留意见。鲁迅这段时期对革命文学,尤其是创造社郭沫若等人主张的文学激进主义,看法相当犀利:
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
郁达夫当时与鲁迅一起讽刺“革命文学”提倡的“血与泪的文学”。鲁迅本人,则到1927年6月,在革命根据地的广州,依然主张把革命与文学二者分开。他说:
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个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到那时,鲁迅可能是主要五四作家中唯一坚持“分离论”的人。他坚持认为,“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
1926至1927年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复晚清关于小说作用的讨论。革命形势的需要,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利用文学作革命宣传的目的很自然地产生。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文学的形式(而不只是文学的内容),也不得不随之变化。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是五四文化批判运动的根本性蜕变——我称之为“学院溢出”,即原先以学院为依托的批判力量过于强大,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出现真空,意义权力的对比过于悬殊,文化批判就理直气壮地溢出学院之外,进入社会,进入实际政治操作,甚至成为独立的政治抗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