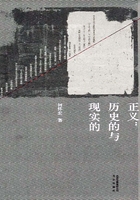在大多数时代和国家,离婚制度已普遍被人们接受。离婚的目的并不是要取代一夫一妻的家庭,而只是想减少痛苦,因为有些人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已经无法忍受婚姻的继续。当今时代,离婚法在不同国家也是有别的,在许多非基督教的文明国家中,丈夫极易获准离婚,另一些国家,妻子也不难获准离婚。摩西的法律允许丈夫提交离婚申请;中国的法律也允许离婚,条件是将妻子的嫁妆如数奉还。天主教视婚姻为圣礼,无论何种原因也不准离婚,但实际上,如果确有许多证据表明婚姻无效,也还是可以通融的,尤其是涉及到大人物的时候。我们也许还记得马尔巴勒公爵和公爵夫人一案,他们要求宣判离婚,因为公爵夫人是被迫成婚的,这理由被认定成立,虽然他们已同居多年而且有了孩子。
在各基督教国家,对离婚的宽大程度与人们信教的程度成正比。米尔顿曾撰文赞成离婚,因为他是新教的忠实信徒。过去,当英国教会认为自己属于新教时,它曾承认因通奸而离婚,虽然其他原因不在考虑之列。现在,英国教会的绝大多数教士都是反对离婚的。斯堪的纳维亚拥有非常宽松的离婚法;美国大多数新教地区也是如此;苏格兰比英国更赞成离婚;在法国,反教权主义拥护离婚自由;在苏联,只要一方提出离婚,即可获得批准,但是由于通奸或私生在苏联不受社会或法律惩罚,所以那里的婚姻也就失去了它在其他地方所具有的那种重要性,至少这适用于统治阶层。
关于离婚,那最奇怪的现象之一,就是法律和习俗往往是两回事。最宽松的离婚法决不是总能产生最多的离婚事件。在革命前的中国,人们几乎不知道离婚为何物,因为虽有儒家之先例,离婚仍被视为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在瑞士,经双方同意即可离婚,而在美国则不能作为离婚的依据。但是,我所了解的数字表明,一九二三年,每一万人中离婚的数量,在瑞士为二十四起,在美国则为一百三十六起。我认为,法律和习俗之间的这种差别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虽然主张对离婚一事应有宽松的法律,但只要父母双全的家庭仍被视为是标准模式,习俗就会成为反对离婚的强大因素,只有极个别的情形例外。之所以持此观点,是因为我不光把婚姻看成是性的结合,而且首先把它看成是生育和抚养孩子的一种合作。通常,由于各种因素,首先是经济因素,会造成婚姻的破裂,但是如果婚姻会破裂,离婚也会遭到破坏,因为离婚是因为婚姻存在而有的一种制度,离婚是婚姻的安全阀。
总的说来,新教和天主教对于离婚的看法,都是根据神学的观点,而不是根据家庭的生物目的。天主教徒认为,按照上帝的意图,婚姻是不可解除的,他们自然会主张,一旦两人结了婚,只要对方还活着,就不可能与第三者有圣洁的性关系,不管他们的婚姻会怎样。新教徒赞成离婚,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反对天主教关于圣礼的说教,另一方面则是,他们断定,不可解除的婚姻将会导致通奸,他们还确信,自由的离婚可以减少消灭通奸的困难。因此,在婚姻容易解除的新教国家,通奸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在那些不允许离婚的国家里,通奸虽说也被视为犯罪,但总有点默许的意思,至少对男人如此。在离婚极其困难的沙皇俄国,高尔基从未因他的私人生活遭到非议,不管人们怎样看待他的政治见解。美国则相反,虽然没有一个人指责他的政治主张,但他却因道德问题遭到驱逐,而且没有一家旅馆愿意供他食宿。
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新教和天主教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都不被赞同。首先让我们以天主教的观点为例。假如结婚之后,丈夫或妻子成了精神病,这样的家庭就不能生孩子了,而且那些已经出生的孩子也不能与精神病患者接触。因此,从孩子的利益出发,即使精神病患者还有神志清醒的时候,离婚仍是必要的。假如我们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精神正常的一方也不能有法律所承认的性关系,便是一种荒唐的残酷行为,是与社会的意愿背道而驰的。精神正常的一方需要做出困难的抉择。他或她是应当继续那种法律和社会道德所希望的婚姻,还是应当有不生育的秘密的性关系,或是应当进行所谓不管有否生育的公开的犯罪生活?以上几种方式,我们都有充分的反对理由。完全拒绝性,尤其对于一个已婚之人,是非常痛苦的,这往往导致男女过早地衰老,还有可能会引起神经错乱,这种情形下的挣扎将严生不快,使人充满嫉妒,性格暴躁。对男人来说,他的自制力会突然丧失,从而变得残暴起来,他很可能会产生寻求婚外性交的欲望,并且一不做,二不休,视一切道德约束于不顾。
第二种方式,即不生孩子的秘密性关系,这是在实践中最为广泛采用的一种方式。对此,我们也有充分的反对理由。一切见不得人的事都是不好的,而且既无孩子又无共同生活的性关系自然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如果男女双方都年富力强且生机勃勃,按照社会利益,我们不应说:“你们不能再生孩子了。”事实上,如果法律规定说:“你不能再生孩子,除非你选择一个有精神病的人做孩子的父亲或母亲。”那么,这与社会利益更加相悖。
第三种方式,即“公开的犯罪生活”,是对个人和社会危害最小的一种方式,但由于一些经济上的原因,这种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行不通的。一个企图过公开犯罪生活的医生或律师,会失去他的病人或顾客。教育部门工作者会立刻失业。即使经济状况使这种公开犯罪生活成为可能,大多数人仍会受到影响的制约。男人希望与俱乐部有联系,女人则希望受人尊敬,而且常有女友拜访。失去这些乐趣显然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此,公开的犯罪生活是很难实现的,除非他是富翁、艺术家、作家,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
在那些不允许因精神失常而离婚的国家里,例如英国,那些患精神病的妻子或丈夫就落入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境地。其实,除了神学的迷信之外,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去拥护这种情况的产生。这不但适用于精神病,而且也适用于花柳病、习惯性犯罪和习惯性酗酒。所有这些都会给婚姻带来危害。它们使伴侣生活成为一个梦想,使生育成为一种罪恶,使孩子和犯罪的父母得不到应有的接触。因此,反对离婚的理由只能是:婚姻是一个圈套,我们要用这个圈套把那些上当者骗人地狱,让他们经受痛苦的煎熬。
真正的遗弃理所当然要成为离婚的理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只是把已有的即婚姻已经破裂的事实,追认一下罢了。从法律的观点出发,这种做法会带来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果遗弃可以作为离婚的理由,那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遗弃现象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至于其他各种能够生效的原因,也都有同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已婚男女迫切渴望离婚,以致主动创造法律所承认的一切离婚条件。过去在英国,如果一个人想离婚,他必须有虐待和通奸的行为,所以,丈夫和妻子预先约定在佣人面前殴打妻子,以此作为虐待的依据。必须承认,无论离婚的理由如何规定,许多人还是会故意去做,以得到这些理由。
我认为,通奸本身不应做为离婚的依据。除了那些受教权的命令和强烈的道德自责的人外,其他人都不可能不对通奸产生强烈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绝不意味着婚姻的失效。即使有了这种冲动,夫妇之间仍会具有热烈的爱情,而且希望婚姻能够继续。例如,一个出差数月的男人,如果他的身体健全,必定很难压制住性欲,尽管他很爱他的妻子。这同样适用于他的妻子,如果她对传统道德的正确性有所怀疑的话。这种不忠行为不应成为夫妻日后幸福生活的障碍,每对夫妇都应当有这种暂时的兴致,因为只要那种潜在的爱仍然存在,这种兴致总会产生。传统道德歪曲了通奸的心理,它认为,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国家中,若对一个人有了爱情,就不可能同时再对另一个人产生真正的爱情了。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事实,但是由于妒忌心作怪,所有的人又都根据这一伪理论,把蚂蚁说成大象。因此,通奸并不能构成离婚的充分根据,除非人们在通奸的时候,真的认为第三者比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好。
这当然不是指那种导致生孩子的通奸式的性交。一牵涉到私生子,问题就变得复杂多了。如果孩子是妻子生的,事情就更复杂了。假如婚姻仍在继续,丈夫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孩子,也要抚养别人的孩子,而且还要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这是违反婚姻法则的,而且会带来无法忍受的本能上的痛苦。因此,在避孕法产生以前,通奸也许确实是一件大事情,但随着避孕法的产生,已使得人们很容易把性交和伴侣生活区别开来。因此,通奸成了一件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事。
合理的离婚理由有两类。第一类是由于某一方有问题,如精神病、酗酒和犯罪行为。第二类是根据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理由可能是:双方经常争吵,无法和睦生活;双方均从事重要工作,而且这工作要求双方必须分居两地;其中一方虽然不讨厌另一方,但对第三者一往情深,以致无法忍受婚姻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不能给予帮助,危险就会接踵而来,甚至可能会导致谋杀。如果婚姻破裂是由于双方合不来或某一方对第三者怀有极为深切的爱慕之情,法律不应做出否定的判决。因此,双方自愿是最好的离婚理由。如果某一方具有确凿无疑的重大问题,离婚就不需要征得双方的同意。
制定离婚法极为困难,无论法律如何规定,法官和审判员总要受情感支配,丈夫和妻子也会极力歪曲立法人的本意。按照英国的法律,夫妇之间的协议不能作为离婚的依据,但事实上,夫妇之间常有这种协议。在纽约,人们往往走得更远,他们会雇用伪证人,以作为可依法处罚的通奸的凭据。从理论上说,虐待完全可以作为离婚的充分根据,但是对虐待的解释却莫衷一是。一位最有名的男影星因虐待而被判处离婚,他妻子提出了许多虐待的证据,其中一条是,他经常把那些谈论康德的朋友带到家里来。很难相信,加利福尼亚的立法者们会因为其丈夫时常当着她的面谈论知己而同意这一离婚案。避免出现这类现象的惟一途径是,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没有那种显而易见的理由,如精神病,来证实一方的离婚要求,离婚必须征求双方的同意。这样,双方就会在法庭之外解决一切经济问题,而且也都没有必要雇用精明之人,去证实对方的不法行为。应当补充的是,因不能性交而无法生育的婚姻应当同意解约。这就是说,如果夫妇希望离婚,而且妻子持有不能怀孕的医生证明,他们便可以离婚。孩子是婚姻的结晶,把人们束缚在一种没有生育的婚姻中,只能是一种残酷的欺骗行为。
法律虽然能使离婚变得容易,风俗却可以使离婚率大为降低。离婚在美国之所以极为普遍,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人在婚姻中所寻求的并不是他们应当寻求的东西,另一部分则是由于通奸得不到宽容的缘故。双方都应当把婚姻看成是一种伴侣生活,而不应当把它视为暂时的私通。这种视婚姻为私通的做法很容易彻底毁灭父母双全的家庭,因为如果一个女人每隔两年换一个丈夫,并从每个丈夫那里得到一个孩子,那些孩子就会失去他们的父亲,婚姻也就因此而失掉了它的意义。在美国,正如《哥林多前书》中所说的那样,婚姻被视为私通的替换形式,所以当一个人得不到离婚就会去私通时,那他就必须离婚。
如果完全根据孩子的利益来看待婚姻,就会得出一种完全相反的道德观。凡是疼爱孩子的父母都应当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以使他们的孩子获得幸福和健康成长的最好机会。有时这需要父母具有极大的自我克制力,无疑这要求父母认识到,孩子的权利远胜过他们自己的浪漫感情。其实,如果父母的感情是真实的,这一切都会是自然而然的。有些人说,如果夫妻不再彼此热烈相爱,不在意对方婚姻以外的性经历,他们就不能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通力合作。因此,沃尔特·李普曼先生说:“没有爱情的伴侣,在生儿育女一事上,是不会像伯特兰·罗素先生所要求的那样真诚合作的,国为他们总是心不在焉,而最为糟糕的是,他们认为夫妻关系只是一种责任而已。”没有爱情的伴侣在生儿育女一事上当然不会通力合作,但是在孩子出生以后,他们是不会像沃尔特·李普曼先生所说的那样失去父母的养育的。对于那些具有自然情感的理智之士来说,即使他们失去了热烈的爱情,生儿育女一事上的合作也决不是一项超人的事情。至于说这些父母“认为夫妻关系只是一种责任而已”,那是因为他并不了解父母的爱情——只要这种爱情是真挚而热烈的,那么在肉体的欲望衰落很久之后,它还是会保持夫妻间那种牢不可破的联系的。
李普曼先生大概从未听说过法国的情形,因为法国家庭非常稳固,父母也十分尽职尽责,尽管他们在通奸一事上享有特殊的自由。美国人的家庭感是极为淡薄的,因而离婚率非常高。如果家庭感很浓厚,离婚率就会降低,即使在法律方面离婚也是很容易的。美国动辄轻易离婚的现象,应当看成是从父母双全家庭向纯粹母性家庭过渡的一个阶段。然而,这是一个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痛苦的阶段,因为现在,孩子们都希望既拥有母亲又拥有父亲,而且在父母离婚之前,有了相当深的父子感情。只要父母双全的家庭仍被公认为社会的标准模式,离婚的父母,因重大原因离婚的除外,就实属没有尽到责任。从法律上对已婚男女进行强制,根本就于事无补。真正需要的是:第一,给双方一定程度的自由,使婚姻变得更为人们所接受;第二,认识到孩子的重要性,因为圣保罗和浪漫主义运动已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性上。
虽然离婚在许多国家是一件困难的事,但轻易的离婚也不是解决婚姻问题的真正途径。为了孩子的利益,稳固的婚姻是很有必要的。稳固婚姻的最好途径是,把婚姻和单纯的性关系区别开来,注重夫妻之爱的生理方面,而不是浪漫方面。我不敢断言婚姻可以摆脱法律上的义务。按照我所建议的制度,人们无疑可以摆脱夫妻间性忠实的义务,但他们还是应当有控制妒忌的能力。美满的生活离不开自我的约束,与其约束那丰富多彩的爱情,不如约束那狭隘的妒忌。传统道德的错误并不在于它要求自我约束,而在于它没有要求到点上。
在内华达,以下情况均可作为离婚的依据:执意分居、犯有重罪或丧失廉耻罪、长期酗酒、自结婚之日至离婚之日始终阳萎、极端虐待、一年不提供生活费、精神病两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