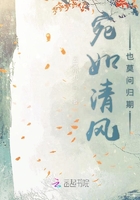朋友把我带出派出所,介绍我进了一个“新闻部门”,可去了才晓得内情。里面的老“记者”康询告诉我,这个地方从来不挂牌办公,但对外却名正言顺称某新闻机构“专题部”。屋里有一本大大的深圳企业电话薄,用来联系“采访对像”,其目的却醉翁之意不在酒 昨晚上还生怕朋友知道了这事,现在却顾不了这么多了。
朋友叫我把电话拿给派出所的警察,我把电话递给尖嘴猴腮。这家伙看了我一眼很不耐烦地接过了电话。我不知道朋友在电话上与尖嘴喉腮说了些什么,反正这家伙放下电话后脸色有了些变化,“怎么不早说你朋友在报社呢,一会你朋友来接你。”
狗日的撂下这么一句就走掉了。
不到一个小时,朋友到了派出所,这时尖嘴猴腮已不见了。只有那个年纪稍大的警察和另一个小警察在办公室。年纪大点的警察说,你这朋友很倔强,昨晚上他要早说你是他朋友,就不会把问题搞得这样复杂。“唉,受了点委屈……”好心的警察面对朋友觉得有些歉意。
朋友把我带出派出所,我们在深圳街头走着。朋友责怪我,怎么不告诉他什么时候到深圳。他说,派出所很多警察都是当地人,文化不高,政府要征人家的地,得解决人家的工作,不少警察都是从保安过度过来的,遇到这些人肯定要吃亏。
我说,也不至于这样不听人讲道理。朋友说,这些年来,警察的特权思想膨胀,要和他们抬杠,管你有理没理都是你不对。再说深圳这地方,外来人口多,确实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在深圳乱搞,所以有的警察执起法来就顾不了那么多。我说,我不能这样就算了,妈的,被他们当作罪犯铐了一夜就白铐了。
“先把工作安顿好后再考虑这问题。”朋友说北京某新闻单位在深圳设立了一个工作站,站里专门成立了一个专题部。他和那里专题部的头熟悉,可以去那里试试,虽然没有底薪,但提供住处。朋友还说:“深圳这地方,发财的人都不是拿固定工资的人,大多都是跑单的人。跑单,用内地的话说就叫拉广告。这个专题部主要就靠跑单拿提成,跑得好,很快就会发的。”朋友还列举了好几个例子以证明跑单是很有前途的,比别的什么工作赚钱都快。
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我不能在深圳街头流落。我对朋友说,去试试。
我们在街上走了很久,弯来拐去,分不清东西南北,都把我转蒙了。最后才在一个住宅区停住脚步。朋友说,这个地方叫深大新村。朋友把我带进高楼林立的深处,然后在一栋楼房前的门外停住脚,按开电子锁上到四楼。
天气很热,汗水湿透了衣衫,我右手腕被手铐勒伤的地方开始焦辣的刺痛。
开门的是一个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女子,她问我们是不是来找某某主任的,朋友说已经和他们主任预约好了。女子把我们带进主任的单间办公室,我这才发现,这是一套标准的住房,三室一厅的住房。进了办公室,朋友和那个坐在桌子后面、身子已经陷进沙发里的主任简单寒暄了两句,然后把我向主任作了简单介绍。朋友急切地说他下午还有重要采访,不能多停留,就把我撂在主任面前匆匆走了。
面前的主任四十岁左右,不苟言笑,脸一直阴着,显得很深沉。他看了我的学业证书后,又要求看看我曾经发表过的作品。我打开背包,翻出我准备好的几篇作品复印件递给主任。主任快速地翻了翻,对我的东西装腔作势做了一番评价,说:“按我们的规定,你本来是不符合我们招聘要求的,但考虑你是某某的朋友,我们就破例接收你。”
主任很诡诈地把我打击一通后,没有再说什么,然后从抽屉里取了张“协议书”给我。我走到外面的大办公室认真填好协议,然后走进去毕恭毕敬放到主任的桌上,他拿在手里看了一眼就丢在了桌子的一边。
他假装思索了一会,然后慢条斯理地从抽屉里摸了两张盖有公章的公文纸给我,我摊在手中一看,一张是“追寻闯浪者的足迹,共绘不夜城的辉煌——关于编写出版系列文史丛书(相会在明天)——驻深群英谱”特邀函;另一张是“系列文史丛书《相会在明天——驻深群英谱》订书单”。
我更是蒙了。我不明白这是要我做什么,我没有直接询问。我想,万一问出什么问题,把我赶出门去,晚上又要流落街头。管它三七二十一,先住下来再说,常言道:走三家不如稳一户。
主任还是那样没有好脸色,他说:“没事了,你出去,到外面去安顿自己的床铺。大厅里都是男生的床铺,你找个空的住下来。”
我走到大厅,这时从外面回来了一个男生,气吁吁地一屁股坐在靠墙的一张铁床上。铁床是上下铺,上面是空位。我问他:“兄弟,这上面没有人住吧?他说:“这床不好,你住那张床的上面吧。”听得出他的话意是不想让我住在他的上铺。这个位置靠窗,光线明朗,可他虽然没有明说不让我住,但就那意思。
初来乍到,我怎么能和人家较劲。算了吧,息事才能宁人。正在这时,一个稍显瘦弱但很精神的男生提着个黑皮包走了进来,他一看就知道我是新来的,而且发现了我的难处,就马上对我说:“住我的上铺吧,没关系,我叫康询。”
我谢过他,就从包里取出简便的床单丢在了康询上铺的木板上。
康询见此,马上把我带到楼下的一个铺子买来一张篾席垫在木板上。算是在深圳有了个安身的地方。
康询在带我下楼买篾席的路上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比如,是从哪个地方来的,过去做什么,为什么想到来深圳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他见我很坦率,也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我。他说他是湖南常德的,真名根本不叫康询,但他从没有告诉过这里的人,他觉得我们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所以才跟我说实话。他还告诉我,他来深圳已经快一年了,过去在一家公司做拉线长,固定工资,赚钱太慢,看到很多一起过来的朋友做业务都赚了大钱,所以就跑到这里来了。
“来了就千万不要回去,那要被别人看不起的,即使要饭都在深圳要,回去太丢人了,说明自己太失败了。我刚来的时候很久没有找到事做,一天吃两个面包,晚上睡在水泥管子里面。我也想过回家,但我坚持下来了,现在对深圳有了很多了解,适应了。其实来深圳的人都不容易,来前以为这里遍地黄金,来了才知道这个城市既是天堂,也是地狱。我们里面有两个女生来了两个多月,没有跑到一个单,晚上出去很晚才回来,我都怀疑她们出去做鸡了,没办法啊,要吃饭……”
晚上,主任走了,同事们回来了,有的唉声叹气,有的骂骂咧咧,我仔细观察,屋子里男男女女有七八个,单间房里两张铁床住了三个女生,有的没有吃饭就到厨房里自己下面条,有的就干脆到外面吃便餐。等女生们都做停当后,康询才到厨房去下了两碗面条,我一碗,他一碗,还搞来一盅广东产的白酒,尽管很难喝,却因心情郁闷,那杯酒我三口就干净了。
从此我和康询臭味相投,成了最好的搭档。
康询告诉我,这个地方从来不挂牌办公,但对外却名正言顺称某新闻机构“专题部”。工作要求是,我们这些“记者”自己设法捕捉采访对象,办公室里有一本大大的深圳企业电话薄,上面有许多公司的通讯电话,大家都可以用桌子上的电话与那些公司联系。至于用什么方式和技巧把单搞到手,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我不仅惶惑,而且感到很孤独。我想童月,但不知道童月的心情怎么样,我觉得她根本没有想我,我有种预感,我们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情感在慢慢稀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