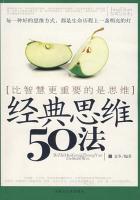如果我们从“存在主义对心理学有何用处”的观点来研究存在主义,大概会发现这实在太模糊、太困难,因此无法从科学的观点来予以了解。不过我们也会发现许多好处。在这观点下,我们了解到存在主义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发现,而是对早已存在于“第三势力心理学”中的趋势的一种强调、确认、尖锐化和再发现而已。
我认为存在心理学有两个主要的重点。第一,它极端强调自我身份的观念经验,而所谓自我身份,是就其为人性以及和人性有关的任何哲学、或科学的充要条件而言的。我之所以选择“自我身份”作为基本概念,是因为我对这个概念比对像本质、存在、存有学等诸如此类的概念较为了解,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可以用经验的方式来处理;即使现在不行,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可以。
但是,这却产生了一个奇异的结果,因为美国的心理学者也已深深受到“追寻自我身份”的风潮的影响了(例如奥波特、罗杰士、高斯坦洛姆、惠利士、艾力克森、莫瑞、穆尔菲、何妮、梅义等均是这类的心理学者)。而且这些作者更了解、更接近原始事态。也就是说,他们比海德格、雅士培这些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还更注重经验。
第二,存在心理学非常强调以经验知识为起点,而不以概念系统、抽象范畴系统、或先验系统为起点。而存在主义则以现象学为基础,换言之,它以个人主观的经验作为建立抽象知识的基础。
不过,也有许多心理学者以同样的强调为其出发点,更别说在各门各派的心理学分析学者中,也含有同样的强调了。
1.因此第一个结论是:欧洲哲学家与美国心理学家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如最初所显示的那么远。(美国人常有终日谈论不休,却不知所云之弊。)当然,一部分是由于这些在不同国度内同时进行的研究发展,其本身就显示出人们虽各自独立研究、却获得同样的结果,只因为大家不约而同地对本人以外的某种实情作出了同样的反应。
2.我认为所谓“某种实情”就是指:个人外在价值的一切来源都已完全崩溃瓦解了。许多欧洲存在主义学者要是反应尼采所谓“上帝已经死亡”的论点,也或许是反应出“马克思也死了”的事实。不过美国学者已经知悉: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基本的价值问题,除了返回内在、走向自我,此外别无他处可作为价值的依归。奇怪的是,甚至某些具有宗教信仰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竟然也赞同此一论点的某部分看法。
3.对于心理学者而言,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能为心理学提供一个目前所缺乏的哲学基础。在这一点上,逻辑实证论已宣告失败,尤其对临床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而言,逻辑实证论更是无济于事。无论如何,基本的哲学问题一定会再度被展开来加以讨论。届时,心理学家也许不必再依赖虚假的答案,也不必再依赖一度会幼稚地采取的无意识的、未经检证的哲学思想了。
4.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欧洲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存在主义所极力处理的是人类由于抱负和限度之间的隔阂(即由于人类所是、所类是、与所能是之间的隔阂)而呈现出的困境。乍听之下,这似乎远离了“自我身份”的问题,事实上,相去无几,因为人不但是现实的存有者,也是具有潜能的存有者。
严肃关切这种差异性,则必能导致心理学的改革。我对这点毫不怀疑,各种各样的文艺也都支持这一论点。例如:投射测验、自我实现、各种高峰经验(在此经验中,人可以跨越上述隔阂)、荣格派心理学、各派神学思想家等均支持这一论点。
不仅如此,他们甚至针对人性的两个层次:较高层次与较低层次、身为受造物的层次与稍似于神的层次,提出整合的问题与方法。无论东方或西方,大部分的哲学与宗教都将此二者截然分裂对立,并教导我们:步向“较高层次”的方法在于弃绝、并控制“较低的层次”。然而存在主义却告诉我们,二者同时都是用以定义人性的基本特征,放弃其中任一项,皆不可,只能加以整合。
不过,我们也已略知某些整合的方式,例如洞察、广义的理解、爱、创造、幽默与悲剧、游戏、艺术等。我怀疑我们集中在这些整合方式上的研究,能超越于前人。
这种强调人类本性具有两种层次的思想,也让我了解到,有些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的。
5.根据此种论点自然会去关怀一种合乎理想、真正、完美、相似于神的人格;并会去研究人的潜在力,而把人的潜在力视为具有某种意义的存在物,是当下即可被认知的实体。这段话听来好像只是字面上的文字游戏,其实不然。我要提醒读者诸君的是,这其实是一种新奇的追问方式,追问的是那没有答案的古老问题:“治疗、教育和养育子女的目的究竟何在?”
其中还隐含了另外一项真理,和另外一项迫切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存所有有关“真正人格”的描述,实际上都具有以下的含义:这种人,凭借其所成就的人格,而与其社会——事实上是与整个社会——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他不仅在各方面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他的文化。他抵制任何管束。他与他的文化、他的社会愈来愈疏离,他逐渐变成全体人类的一份子,而不再是地方团体的一份子。我想大多数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于这点必然会大不以为然。因此,我衷心期待这方面的争辩;而且为了达到“普遍性”,争论显然也是必要之举。
6.我们能够而且也应该向欧洲作家们学习重视所谓的“哲学人类学”,也就是说,应该尝试去定义人类、尝试去界定人与其他物种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的差异。人类独一无二、且可用以定义人性的特征,是什么呢?这对人类极为重要,如果缺少了它,人类的人性本质便无从定义。
大体说来,这是美国心理学界一直废弃搁置的工作,各种行为主义并未致力于制订这类的定义。至少没有一个定义是可以严肃以待的。(一个“刺激——反应”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谁又会是这样的人呢?)弗洛伊德对人类所描绘出的图像,显然并不十分恰当;因学家所见,事实上,弗洛伊德所提供给我们的,所谓具有最丰富的内容系统的病态心理学和心理治疗,都已偏离正道了。
7.有些存在主义哲学家太过武断地强调个人的自我创造。例如沙特等人所说的“自我就是一种投射”,便完全是由个人自己持续不断(独断地)选择所创造而成的,好像人仍然可以任意决定自己所欲成就的模样。当然,在这种极端的形式下,这的确是一种夸大其辞的说法,而且直接违反优生学和体质心理学所提出的事实。就事实而论,也仅只显示出它的可笑罢了。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派存在心理学派的治疗学者、罗杰士派和人格成长的心理学者,也都论及了有关“发现”自我和“揭发式的”治疗方式,但是他们或许太低估了意志和决定的因素,也忽略了个人抉择对个人塑造自己时的重大影响力。
(当然,这两个学派可以说都太过心理学化,而太缺少社会学化了。换言之,他们在各自的思想系统中,都太不重视社会和环境的决定因素,太不重视诸如贫穷、剥削、国家主义、战争和社会结构等这些外在于个人的因素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当然,没有一个神智清醒的心理学者会妄加否定个人在这些力量之前所感到的某种程度的无能为力。但是,毕竟他主要的职责是研究个人,而不是研究外在于心理的社会因素。同样,对于心理学者而言,社会学者则似乎太过武断地强调社会力量,而忘却了人格、意志、责任等的自律性。所以,我们还是把两个学派都视为有,而不是盲目或愚蠢,比较好些。)
8.我们不只是一直在逃避责任与意志的问题,也在逃避与责任、意志息息相关的力量和勇气。最近,心理分析派的自我心理学者已经觉察到这项重要的人性变数,并且也已经密切注意到“自我的强忍性”。至于对行为主义的学者而言,这依然是个遥不可及的问题。
9.美国心理学界学者虽已响应了奥波特的呼吁,注意到个案研究的心理学,却还没有多少成效,甚至连临床的心理学者也没有什么成绩。现在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又在这方面加给我们一道推动力、一道难以抗拒的推动力——我认为理论上是“不可能”抗拒它的。如果已知的科学不能配合对个人独特的研究,则它充其量仍是一种糟糕的科学概念,终究须得忍受一番改造。
10.现象学在美国心理学的思潮中已具有一段历史,但是就整体而言,我认为它已经没落了。不过,欧洲现象学家以严谨审慎及苦心孤诣的举证,教我们明白,了解别人的最佳途径——或者至少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必要途径——就是去了解他的世界观以他的眼光来看他的世界。当然,这样的论点,就任何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来看,都是粗糙不堪的。
11.存在主义哲学家强调个人终极的孤寂感,不仅有利于提醒我们要更深入地去研究人心、责任、选择、自我创造、自律、自我身份等等;同时也使得孤寂者彼此之间的沟通秘密——例如:直观与同情、爱与利他、与他人认同、和普遍的和谐共融——愈发显得有问题、愈发令人迷惑不解。而我们却将这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如果我们能将之视为尚待解释的奥秘,则应该是比较恰当的做法。
12.存在主义作家另外还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简单陈述如下:他们认为与生命之严肃面、深刻面(或者所谓“生命的悲剧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生命的肤浅与平淡,这是一种萎缩了的生命,是对生命终极问题的抗拒。这不仅是一个文字上的概念,更有实际运作的意义(比如在心理治疗上)。我(还有其他人)都日益感受到,悲剧有时也有治疗的功效。而且,如果病人是为痛苦所迫而寻求治疗,则治疗的功效往往最佳。当肤浅的生命行不通时,它便受到质疑,继而引发返本溯源的呼唤。正如存在主义学者清楚明白的指证,肤浅的心理学已经行不通了。
13.存在主义以及许多其他学派的学者都帮助我们了解到,语言性的、分析性的、概念化的理性有其限度。而这些学派都是当代呼声中的一部分,呼唤着我们返回先于任何概念或任何抽象作用的原始经验。我相信这是一种检证批判,针对的是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整个思想方式,包括正统的实证科学与实证哲学在内,都迫切地需要重新予以检证。
14.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所引发的一切变革里,最重要的可能要数科学理论中迟来的革新。也许我不应该说他们“所引发的”,而应该说“在他们的帮助下”,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力量也有助于摧毁正统的科学哲学或“科学主义”。不仅要克服主体与客体之间所谓笛卡尔式的分裂对立,还有,由于心灵和原始经验都被纳入实体界,也必然会造成许多其他更剧烈的变革,这些变革不仅影响心理学科,也影响其他各学科,因为像吝啬、简朴、精确、秩序、逻辑、优雅、定义等,也都属于抽象概念的领域,而不只是经验的领域。
15.最后我要谈谈存在主义作品对我影响最大的激励,心理学中有关未来时间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全然陌生,我想,对任何一位研究人格理论的严肃学者来说,这也不是一个陌生的问题。布勒、奥波特、高斯坦等人的作品,都使我们深深感受到有必要对于“未来”在现有人格中所扮演的动态角色,作一系统化的处理。例如成长、蜕变,可能性均必然指向未来;而潜能与希望、欲求与想像等概念亦然。一旦将之化为具体之物,则会丧失未来;威胁与焦虑同样指向未来(没有未来就不会有精神官能症);自我实现若不指向一个流畅活跃的未来,则毫无意义可言;生命可以成为一种时间的形态……
存在主义学者对此问题基本而核心的重视,对我们良有以教,像史特劳斯所写而收在梅义所编纂的《存在》一书中的那篇文章,即是一例。任何一套心理学理论,其重点若不包含以下的概念:“人类的未来潜藏于自我的内在,且动态地活跃于当下的时刻里”,便不会是完整的理论。我想这是十分合理的说法,在此意义下,我们可以把“未来”视为雷印所谓“非历史性的”。我们也必须了解,只有未来是原则上未知的,且是未可知的;换言之,一切习惯、防卫和应付技巧都是模糊不定的,因为它们的建立基础是过去的经验。只有具有弹性活泼的创造力的人,只有能够常怀信心、面对新环境无所惧的人,才能真正地处理未来。我确信目前我们所谓的心理学,有许多部分都只是在研究我们“为了逃避绝对创新之焦虑,而迫使自己相信未来仍将一如往昔”,所使用的惯技而已。
以上这些想法支持着我的希望。我希望我们看到的是心理学上的一种扩充,而不是反心理学或反科学的一种新“主义”。
存在主义很可能不仅能够丰富心理学的内容,而且可能也是一种附加的推动力,足以建立一套心理学。这套心理学处理的是有关已完全发展的真正“自我”及其存在的方式。苏提须建议将这种心理学称为“存有心理学”。
的确,我们似乎日益明白,心理学中所谓的正常,其实是一般人的一种心理疾病,只不过它太不起眼,范围太广,因此平常注意不到它。而存在主义对于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生命所作的研究,帮助我们把这种普遍的假象,这种在幻觉与恐惧下的生活,投入一个清晰耀眼的光明之中,并暴露出它是病态的——即使它也是普遍的人都有的情形。
我不认为有必要太过严肃地去看待欧洲存在主义学者絮絮不休地谈论恐惧、苦恼、失望等诸如此类的现象,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惟一药方就是“坚忍到底”。由于价值的外在来源都已失效,才会引起这种“高IQ”为宇宙现象哭泣的情形。在这方面他们实应向心理分析学者学习去了解:幻觉的消失与自我身份的发现,起初虽然痛苦,但最后总是令人兴奋、且令人坚强的。还有,他们当然也不肯提及高峰经验、体验、欢悦与忘我、甚至不曾提及一般正常的幸福感,这使得我们强烈地怀疑,这些作家是否不曾有过高峰经验,不曾体会过欢悦。他们俨然只能用一只眼睛,而且还是一只有色的眼睛去看世界。大多数的人都不仅体验过各种不同程度的悲剧,也体验过不同程度的欢笑。而任何一种哲学如果遗漏了其中二项,都不能算是广大悉备的哲学。威尔逊曾明确地区分“正面言论”的存在主,义学者与“负面言论”之存在主义学者。我完全同意他所作的这种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