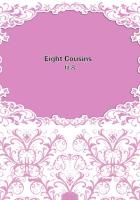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有句名言:“像半神人那样思考, 像普通人那样生活”。而这个意思在中国传统中似也有个对应,那就是儒家经典《中庸》所言:“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的生活境界,它既超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却又不完全否弃一般人的生活。“极高明”与“道中庸”从世俗角度看去本来是对立的:“极高明”便不大可能“道中庸”,而“道中庸”则难以做到“极高明”。但儒家所要求的理想生活, 却恰恰要求在现实生活中统一这种对立:“极高明而道中庸”,中间的“而”字,正是这种统一的表示。
然则,从历史上看,儒家思想由于自身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使人们在践履“极高明而道中庸”理想时,终究难以跨越“道德境界”而进入冯友兰所标示出的人生四种境界(依次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之首的“天地境界”以达到“极高明”,自然也更因此而限制了在此基础上“道中庸”意义的真正实现。换句话说,正是儒家对道德的“苛刻”要求使古代的君子们面对“极高明而道中庸”理想时进退两难,从而最终使成就最高道德而“达标者”鲜见于世。同时由于拘于“道德”的境界,又使得许多人的人生虽达到了“高尚”,但是却缺乏更自由超越的“高妙”人生境界,比如做一个自由的人、完全的人,能在现实生活中“诗意地栖居”。因此就可以说,如果一个人想真正实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高尚而又高妙”境界,就必须具备超越儒家泛道德化思想的智慧和勇气。
在多年研读、讲授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作品的过程中,渐渐地我们发现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所表现的诗意与襟怀现实而完美地昭示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或者说,借用冯友兰人生“四境界说”,我们可以认为《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代表了陶渊明站在“天地境界”对自然、功利乃至道德境界的同时超越。当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们才似乎领悟了陶渊明胸中别有大业,非浅儒所知的真正内涵。
冯友兰哲学思想中十分有价值的“人生四境界说”为我们理解陶渊明提供了一个极有意义的平台。他认为人生因个人对生活的“觉解”的不同而有四种境界:自然、功利、道德、天地。陶渊明是达到了“天地境界”的诗人,这种定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升华超越性。因为这个平台,终于可以使我们对陶诗极高妙的境界与其极平实的生活实践以及平淡无华的诗风是如何现实而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与把握。
在古今(尤其古代)诸多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评价中,最一致的恐怕就是“不可企及”,而他的“不可企及”处我们又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是“极高明”的思想境界,另一“不可企及”处则是他的“道中庸”的行为状态。试析如下:
陶诗胸次浩然,其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沈德潜:
《说诗晬语》)
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陈师道:《后山诗话》)
靖节胸中阔达,有与天地同流气象。(钟秀:《陶靖节记事诗品二十二则》)
陶彭泽如绛云在霄, 舒卷自如。(敖陶孙:《敖陶孙诗评》)
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元好问:《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
赤堇氏云:昔人以太白比仙,摩诘比佛,少陵比圣;吾谓仙佛圣犹许人学步,惟渊明诗如混沌元气,不可收拾。(厉志:《白华山人诗说》)
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文句,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 其本色高也。(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
宋末理学家包恢认为“彭泽一派,来自天稷”,有一种“汪洋淡泊”之美。“汪洋”是指诗歌的境界阔大无涯,这主要因为它同乎造化,是“自大化混浩中沙汰陶熔出来”的,与“大道本体之宏”融通化一。故陶渊明为诗多自胸中流出,多与真合。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才可以达到一种天春气霭,花落水流的境界。
另一“不可企及”处则是他的“道中庸”。如“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耳”。
这个评价可谓不仅将陶渊明“高于老庄”之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这是他的“道中庸”,更明示出陶渊明“高于”一般人之所在乃“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而这是他的“极高明”。由于“极高明”,才使得“道中庸”绝非是“道平庸”;而更因为“道中庸”,才使得“极高明”不会“倜然无所归宿”,他是脚踏实地的。陶渊明“即从作息勤厉中,写景观物,讨出一段快乐。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一副旷达之语,所以为真旷达也”。
极高明而道中庸,所谓“极高明”是就人的境界说,“道中庸”是就人的行为说。就境界说,由于人对人生觉悟理解的程度不同,可有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不同的境界。就行为说,不同岗位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行为,但不同境界的人不必有什么特别不同的行为,所以冯友兰说:“圣人并非能于一般人所行底道之外,另有所谓道。若舍此另求,正可以说是‘骑驴觅驴’……圣人有最高底觉解,而其所行之事,则即是日常底事。此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那么,陶渊明在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诗中是怎样站在“天地境界”对道德、功利、自然境界同时进行超越的呢? 或者说,陶渊明是怎样以“极高明”的修养而在生活中“道中庸”的呢? 试析如下: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途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寒草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其一)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其二)
癸卯是晋安帝元兴二年,即公元403 年。陶渊明正是在这一年开始躬耕的。一般注本的解题总说这首诗写怀念古代的躬耕的隐士长沮、桀溺。事实上,其意义没有这样的简单或表面。“初视若散缓”的陶诗在很多情况下令一般读者难以充分感觉到其诗的“奇趣”,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两点: 一是惑于二三流作品那眩人眼目的文采而对超文采的“平淡”这种最高艺术境界不易体认,二是囿于功利乃至道德的境界而对超世俗的“天地境界”这种最高的人生境界不能理解。
一、“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对道德境界的超越
对于田园耕读生活, 陶渊明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以极高的智慧与勇气所自觉选择的,因而这两首诗的结构一如他的人生境界,是极其完整精妙的:
《怀古田舍》二首,气脉相连。起句“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曰“在昔”、曰“当年”,便是怀古矣。“闻南亩”,便伏荷蓧、沮、溺一流人;“竟未践”,便伏孔颜之徒,言有此两种人也。二句系二首冒子。“屡空”句紧承“未践”,“春兴”以下,承首句意自序,而引植杖古田舍翁以自况,作一顿。结语“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乃一开一阖,若曰颜、孔之徒乃通识者,若以荷蓧、沮、溺对之,即使此理有愧,然而耕凿中所保岂浅哉? 故次首紧接先师忧道。所谓通识者,我愧不能逮。
“瞻望”以下,皆言耕凿所保也。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四句的写法是“愈平愈高,转近转远”,其中的诗意与胸襟与众趣殊然,故常人难以赏悟那种平夷冲淡之味。按一般小儒浅士的理解,圣训所言应该是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可陶渊明却公然说:“先师‘忧道不忧贫’的遗训太高远了,我抬头望了望发现够不着,于是便不再勉强自己,还是转身种地算了。”这里就存在一个大问题,先师所言“忧道不忧贫”是对古代君子们的不容置疑的人生道德要求,在陶渊明之前,还没有人敢怀疑过,哪怕很多“君子”实际上都做不到,也不会有谁敢对它说“不”。可是陶渊明究竟哪来的勇气和智慧以看来是如此“轻松”的姿态把“它”搁置在一边,几乎是自甘“堕落”地种地去了。并且从本诗所反映的情绪来看, 陶渊明还把回归园田种地的日子几乎过出了“高峰体验”的极乐境界,这是为什么呢?
当年孔门弟子樊迟问稼,遭到孔子斥责,从此不仅樊迟就背上了千古小人儒的骂名,而且其长远的影响是中国的君子们如不能有“兼济天下”的机会的话,只有坐以待毙,其“独善其身”的精神生存空间与物质生存空间是相当有限的。谁有足够的智慧与勇气为生存而耕稼陇亩,从而让别人说自己是“小人儒”呢? 本来儒家是倡导重农的,以农为本从来都是古代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儒家却反对君子躬耕自资,因为它给君子所赋予的大任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同时君子自然更不能考虑从事工商这等“末事”来糊口。魏晋以来的士人们一直是“耻涉农商”。而陶渊明在《劝农》一诗中委婉地批评了孔子不问稼穑,董仲舒不窥园的态度,“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弗履”。认为:“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民以食为天,舜尚且不弃躬耕,如我之辈,怎能“曳裾拱手”? 在陶渊明看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由此可见陶渊明求得人生“自安”的道路是永恒正确而光明的路,是真正现实而又理想的路。如果仔细思索一下陶渊明完整的一生, 我们肯定会发现他最超绝也即最富于勇气与智慧的地方恰恰是从选择“躬耕自资”开始的。
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诗中陶渊明说:“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而“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就是“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而“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也正是“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看似自谦非攀“高操”,“固穷节”是“谬得”,然此“栖迟”“讵为拙”? 这就是陶渊明的超拔的智慧与非凡的勇气。
试想,古代的君子们如果“兼济”不成,想独善其身于世,那么“生生所资”几乎无法解决。如不想饿死,便很可能无奈地再回到污浊的现实环境。因此我们就看到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理想与其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之间从而构成了事实上的矛盾。那么陶渊明又是怎样做到无视儒家“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而“转欲志长勤”的呢? 这其中必定有某种超凡的智慧和勇气。
“养真衡茅下”,“任真无所先”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而“真”又是“天地境界”的本色,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即理愧通识,所保岂乃浅”的“正言若反”之妙。所保岂止是“深浅”问题,更涉及的是“完整”与“残缺”。因为达到“真”境界的人生必定是深度安足的,也是完整无缺的,无论其对人生的情感态度还是具体行为都是如此。而这正是陶渊明的“不可企及”处: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陶渊明“谋道”“忧道”并不是不着边际的玄谈空想上,他始终把“谋道”“忧道”放在“谋食”“忧贫”的基础上,始终坚定不移地把归隐之后的生活理想、人生道路落实在“躬耕自资”的行动上,从“躬耕未曾替”的实践中去体验挖掘“道”的精髓。因此,陶渊明兼有“高人”与“细民”、“隐”与“农”二重身份,在人格上是完整的。他不仅执着于形而上的“道”,而且致力于形而下的“食”,这在文化意义上也是完整的。这种完整性,正是陶渊明的难于企及之处。
事实上,我们早应看到的是,当拥有的物质超过一定的度时,生活反而会是残缺的。尤其在精神方面因过多操心、驰骛于外在世界,不仅会如老子所说的“甚爱必大费”,更严重的是精神生存的空间亦必将日益干枯萎缩,从而导致人生整体的“残缺”;有求于外物,终究会被外物所控制。所以陶渊明的“完整”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结果:
正因为陶渊明以自己的生活实践将“高人性情”和“细民职务”集于一身,融为一体,因此他的人格、他的风貌、他的创作才显示出旁人难以仿佛一二的魅力:既真旷又淳厚,即潇洒又执着,既高雅又平实,既出世又入世。就拿他的田园诗来说,并不单纯是描写隐居田园的闲情野趣,其中有劳动的甘苦,有劳动者的希望和忧虑,贯穿着陶渊明质朴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理想,既有“谋道”者的孜孜求索,也有“谋食”者的辛勤耕耘。
因为圣贤之所以境界高,并非有奇才异能。无非对一般人的生活有充分的了解。圣人的生活,原本也就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不过他比一般人对于日常生活的了解更为充分。了解有不同,意义也有了分别, 因而他的生活超越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所谓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就是他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里所应做的他都做了。所以古人说:“陶彭泽诗,颜、谢、潘、陆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赋之于诗,无一点愧词,所以能尔。”这或许就叫“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陶渊明反复强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陶渊明这是在告诉人们要想走人间正道,走真正自由、超越与解脱的“正道”,则必须先从正道上解决吃饭穿衣开始。他说:“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显然陶渊明绝非苦行僧, 他说得非常明白:“难道我不喜欢穿又轻又软的裘皮衣服吗,可是它如果不是从正道得来的我就不希罕! ”田园耕读生活是陶渊明理智与情感双重选择的生活方式, 由此可见陶渊明选择的是一条更需要智慧和勇气的艰苦的道路,绝非是逃避现实,绕开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