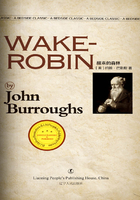魏晋玄学最高阶段的代表——郭象基于其“独化于玄冥之境”的“足性逍遥”观,主张物无大小,只要自足其性,就是逍遥的存在,这使得传统的“儒式之隐”与“道式之隐”随着士人们新的存在方式的选择而发生了融合、变化,一种“小隐隐林薮,大隐隐朝市”的“朝隐”风气大行于世,这是一种“亦隐而非隐”的“隐逸”新概念。
自陶渊明被南朝的钟嵘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后,陶渊明千百年来就以隐士的身份“飘逸”在人们的心目中;当然,认为陶氏颇有“康济之念”, 因而断定其绝非隐士之论也是代不乏人的。但通过考查,我们发现简单地为陶渊明贴上“隐”或“非隐”的标签都是不妥的,因为这无法准确地把握和说明陶渊明其人其诗的价值和意义。陶渊明处在“隐逸”概念大发展、大丰富、大深化的东晋时代,并终于使他采取了“亦隐而非隐”的存在方式,在田园耕读生活中求得了自身存在的统一。
一、东晋前两种传统而经典的“隐逸”方式
《隋书·隐逸》指出:“自肇有书契,绵历百王,虽时有盛衰,未尝无隐逸之士。”“隐士”的存在,可谓源远流长。他们给人的经典印象其一是《论语·泰伯》所言:“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守死善道”也就是像中国隐士的祖宗伯夷、叔齐那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此为典型的“儒式之隐”。这类隐士如《孟子》所言是“治则进,乱则退。”所谓“隐”则不过是他们一时的权变,无关乎“治”与“乱”。这类隐士往往采取极端的生存态度与方式。《晋书·隐逸》说他们“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过着“却粒餐霞”的日子,以此“养粹岩阿,销声林曲”。他们超然绝俗到不是如《南史·隐逸》说的“终身不窥都邑”,便是《晋书·逸隐》所言“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言。”我们甚至在《南史·隐逸》中看到最极端的是“父为之昏,妇入前门”,而有隐逸“痼疾”的新郎却从“后门出”,溜之大吉了。这些显然是具有道家风格的隐士做派。
不论“儒式之隐”还是“道式之隐”,古来人们一般都是赞美有加的。因为隐士虽皆欣欣于独善,鲜汲汲于兼济,但纵无舟楫之功,却终有贤贞之操。他们“无为”的存在方式因此而产生了“有为”的影响,可使人们如萧统《陶渊明集序》一文所言:“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怯,贪夫可心廉,懦夫可以立。”二、“亦隐而非隐”之隐逸新概念的产生及其理论根据
魏晋之前,儒式之隐与道式之隐是绝不混杂的,各有其源与流。
但是魏晋之际社会的空前动荡与黑暗状况使此前人们一直独尊的儒术及所服膺的老庄思想都暴露出了局限性, 已无法为人们在现实中寻找理想的存在方式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儒学向来倡导的只是“有为、兼济而出仕”,而老庄则力劝人们“无为、独善而遁隐”。为了说明其理论的根据,儒家强调“天”,道家推崇“道”,但无论儒家的“天”,还是道家的“道”都在表明现实世界是由一种超现实的力量所支配。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讲,儒家与道家都是以“天”或“道”为终极价值、终极目标的。但任何价值与目标一旦具有“终极性”,那么它就不免是“一元化”的。这种理论往往只适合于几百年大一统的汉代,那时“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时至魏晋“你方唱罢,我登场”所导致的政权走马灯式的血腥更替使一切都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社会与个体存在的有限性空前凸显。特别是“人必死”的现实更让理性的人们痛感唯有自己的富于个性的、有建树的存在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因此,许多人为能驻足于历史之流而选择了各种形式的“建功立业”,乃至不惜发出“若不能流芳百世,遗臭万年亦可”的慨叹。同时更有许多人为表现自身的存在而“任性自为”,也就是说此时人们在选择、决定隐逸或出仕时早已不是简单地基于传统的出、处理由,即如《晋书·袁宏传》所说“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而更多的人在“默”(指“隐”)而不“语”(指“仕”)时,只不过表现了“性分所至”的天性使然也:
(谯)秀少而静默,不交于世。(《晋书·隐逸》)
(辛谧)性恬静,不妄交游。(《晋书·隐逸》)
(宗少文)好山水,爱远游。(《南史·隐逸》)
(杜)京产少恬静,闭意荣宦。(《南齐书·隐逸》)
这就是《宋书·隐逸》所说的“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具体说来,“少而静默”、“不妄交游”、“闭意荣宦”、“好游山泽” 乃至“不修仪操”是他们共同的“性分所至”,他们就是这样“任性自为”、“任性而适”地生活着。
问题是,这些“性分偏介”的隐士们,任其“性分所至”的活法算不算是一种存在方式? 或者说,这种“活法”是否是“自足”的,其存在价值是否独立无依? 其意义该怎样评价?
应该看到,这种“禀偏介之性”而自得逍遥的隐士是大量出现在东晋以后的。而且他们已不再像前辈隐士那样注重自己“激贪厉俗”的榜样形象,甚至其存在简直就是独善之美有余,兼济之功未也。而如果要追寻这种存在方式大行其道的理论根据的话, 那自然就是东晋玄学家郭象基于其玄学体系“独化于玄冥之境”之上的“足性逍遥”论。
郭象只承认现象世界之实在,现象之外再没有东西,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偶然的,是突然而生的,每个事物都是独立的,这就是他的“独化”论。据此,郭象在注《庄子》时认为:
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 并且举大鸟与小鸟的例子来说明大鸟虽“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而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枋而止”,若比起能耐来,大鸟与小鸟似无法比拟,但郭象认为“其于适性一也”,理由是:
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
以上是郭象基于自己的玄学体系的基本思想对《庄子·逍遥游》的注解。郭象要肯定的是物无大小,只要自足其性,就是逍遥的存在,在《庄子·齐物论》注中他对此更作了发挥:
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
任之而自尔,则非伪也。
凡物云云, 皆自尔耳, 非相为使也, 故任之而理自至矣。
冯友兰先生认为庄子的“齐物”观念并不是快刀斩乱麻式地“削齐”万物的差别,“而是从一个较高的观点得到一种较高的理解”,“这个高一级的观点,就是‘道’的观点。照郭象注的解释,《庄子·齐物论》
的主题就是从‘道’的观点看不齐的事物和言论,能够这样看,不齐的事物就齐了。”郭象对庄子“齐物论”的“齐论”是与他的万物皆“独化”自尔而生的理论体系相一致的,只要使“各有宜”的物“各得其宜”,进而“任其自明”,则“其光不弊也”。如此郭象就把庄子的“逍遥”论与“齐物”论统一了起来,因而就形成了玄学的“足性逍遥”观。
这种“任自然”的玄学“足性逍遥”论为“隐逸”本身赋予了新的内涵,带来了新的变化,相当多的隐逸行为便成了一种超功利的(而所谓“功利的隐逸”则指那种“存身以待时命的权变”、“激贪厉俗的榜样”甚或“终南捷径的铺垫”等等为目的的隐逸)生存选择。因为“隐士”们的“任性自为”本身已历史性地获得了“自足性”,已无须假以他人及社会的承认与否而得“存在”之“真”。因此,《南史·隐逸》记载,当有人被指责在“世路已清”时“犹遁”,得到的回答是:“为仁由己,何关人世! ”不独“时方颠沛”才隐,“世路已清”也要隐,这即是超功利的为“真”为“仁”而隐! 如此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多自由潇洒之美及多情仁爱之善的故事:
(宗少文)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之“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南史·隐逸》)
(王弘文)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弘之常垂纶于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不? ”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门,各以一两头置门而去。(《宋书·隐逸》)
“好游山水”是此期隐士们最一般的共同“性分所至”,而且他们还常施爱于自然,如《南史·隐逸》记载,“曾有鹿中箭来投(孔)祐;祐为之养创,愈然后去。”魏晋以后这种“超功利”新隐士的存在,是我们民族“人”的个性及丰富性大大展开的结果。这些体现了“隐逸”新境界的隐士们虽不能为社会的进步做出“直接”的贡献,但他们那种“自足其性”的存在以及当时社会对他们这种“非日常”存在方式的一定程度的容忍乃至赞美,其本身就已表明了一种社会进步,一种自由的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如郭象所言:“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任其自成,故无不成。” 若非如此,社会则将产生恶与伪,而“任之而自尔,则非伪也。”“任其自得,故无伪。” 只要各任其性,不论翱翔天池,还是毕志榆枋,皆得逍遥自由。
郭象的“足性逍遥”理论如此看来支持的就是人生、人的生活方式多元化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肯定的也因而是过一般性生活的人是能够使自己恰恰在此一般的而非特殊的存在方式中活出意义来。主张“贵无”的王弼着重强调的只是“名教”(即封建的纲常礼教)
存在的合理性,而郭象则是不限于“名教”的存在去论证一切可称为“有”的存在之合理性。这种意识在今天看来都是很现代的。
郭象认为“独化”而“自生”的万物各有其“性分”,彼此绝对不同。
“性分”就是一物的“极”,或者说“限”,超出了这个“极”、“限”,一物就不是自己了。对此,当代哲学家汤用彤先生有一段精彩的分析:
王弼说物得之于“无”或“道”,物之所得(或性分)离不开“全”,“德”为“道”所命(order),夫道而后德,失其母则发裂。郭象说万有各得其得, 各物之性非“为某物所命”(ordered by something),而是为自己所“命”(order),故在此种意义上说,“性分”是绝对的。……欲全一物,即须全其性。
王弼说“全性”须“反本”,郭象则说只须实现其自己,用其自用,不可为(人为),不可造作,不可强制,“恣其性内而无纤芥于分外”,即是“无为”。“无为”者,非谓“放而不乘”、“行不如卧”,而是令马行其所能行。“任性”即“无为”也。就“物各有性,性各有极”说,物各绝对独立。而物各绝对独立,各为中心,此即是无中心,无绝对。我自为独立,但我不能忘记甲乙等(皆自为独立),故不可使人从己,亦不可舍己从人。帝王治天下,在顺民之性。
由此,汤先生认为王弼的“贵无”学说为抽象一元论,而郭象之“崇有”为现象多元论。哲学上的多元主义,意味着否认绝对真理,否认终极目标,否认造物主的存在,否认现象之外有本体。郭象的万物皆自生,皆“独化于玄冥之境”正是如此。由于认为物各有性分,性分绝对, 郭象的意思就是一切平等, 或曰一切相夷相齐,“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 。这就对世间万物的存在的合理性给予了极大的尊重, 故他所肯定的就是人们在自己的“性分”内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的合理性。由于性分不同,当“任性而适”时,自然也不会产生完全相同的存在方式,并且不管是哪种存在,它们的价值总是相齐、相夷而不能取而代之的。重要的是“直各任其自为” 。“各任其事,而自当其责矣。” 为自己的存在各负其责,而不要去干涉他人他物的存在,因此,万物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性分,获得自身存在的统一,便可各自逍遥。
由于重要的是“足性”,那么传统的“隐逸”概念自会发生变化:
“所谓无为之业,非拱默而已;所谓尘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 既如此,以“无为”为本质特征的“隐逸”就产生了历史性、戏剧性的逆转。
那种“肥遁于山林”的经典“隐逸”就在此时因其偏执性、极端性而被人们视之为“小隐”,算不得什么能耐。而隐于朝市,即在世俗“尘垢”中求得逍遥才算“隐逸”的最高境界,才是“大隐”。乐广那句著名的“名教中自有乐地”便成为带有时代特征的新体会,其广告效应自然深入人心。晋代的邓粲更是直言不讳,《晋书·邓粲传》中记载了他的“新隐逸观”:“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关键就在于“隐初在我,不在于物”,因为诚如《莲社高贤传·周续之传》所言“心驰魏阙者,以江湖为枯槁;情致两忘者,市朝亦岩穴耳”。这表明,“隐士”们开始更注重“隐逸”质量而唾弃了那种仅仅“肥遁于山林野薮”便算完成了以“隐逸”求超越、逍遥的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