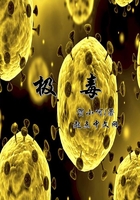此诗写人与春燕感情之交流,亦见陶渊明物我之情融。其中“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一句极准确地将春天万物复苏的情态呈现出来。“骇”字、“舒”字似不经意,却读来有“惊”心“动”魄之感! 这是春天给我们的感动! 且每次读到这一句总让我们想起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诗:《春天以及一切》:
通向传染病院的路旁
在蓝色的斑驳的
汹涌云涛之下——一阵冷风
逐云自东北。远方
大块大块荒弃的泥泞田野
歪歪倒倒的干枯野草,褐色一片
一滩滩死水
零零落落的高树
沿路都是绛红的
深紫的、叉状的、竖立的、槎桠的
灌木丛、小矮树之类
树下堆积褐色的枯叶
无叶的蔓藤——
表面无生命之痕迹,而懒懒的
迷糊的春正姗姗而来——
他们赤裸裸地在新世界登场
挨冷。除了登场是肯定的
一切都不能确知。他们周围
是熟悉的冷风——
现在是小草,明天轮到
野胡萝卜硬挺的曲卷叶芽
万物一一明确化——
迅速加快:清晰,树叶的线条
而此刻的登场,充满
轮廓分明的尊严——然而,他们
突然发生深刻的变化:根植的他们
向下抓紧,开始觉醒(钟玲译)
陶渊明的“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是“诗”,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春天以及一切》是“赋”。后者也几乎是前者的“注释”或者说是“译文”。对春天的感觉,中国东晋时期的陶渊明与美国现代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真可谓一唱一和,共同完成了一曲春之交响。
陶渊明其人天机自运,有浩然盛德,其言平易而昭明,诚君子之诗也。先将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与专事雕章琢句者的境界大别于此。晚唐后许多诗人专尚镂镌字句,语言虽工,只不过在彰示其小智小慧之雕虫小技,终非浩然盛德之君子之所为也。所谓“浩然盛德之君子”就是冲和雅澹,得性情之正的人,杨士奇认为:“诗以道性情,诗之所以传也。古今以诗名者多矣,然《三百篇》后得风人之旨者,独推陶靖节,由其冲和雅澹,得性情之正,若无意于诗,而千古能诗者,卒莫过焉。故能轻万钟、芥千驷,翛然物表,俯仰无渐,岂非足乎己而无待于外者乎。”清代谢榛《四溟诗话》也认为:“渊明最有性情,使加藻饰,无异鲍谢,何以发真趣于偶尔,寄至味于澹然? ”(谢榛:《四溟诗话》)谢榛的见地是极高的,但这里容易产生误会的是陶渊明写诗绝无藻饰, 而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一点也是古来研究陶诗的“大家”们一直在纠正的世人对陶诗的一种绝大误会。一般人认为陶渊明只是一味高古平淡,而看不到中庸的陶渊明却一边高古平淡,一边将语言琢炼到不可思议的神妙境界。如“微雨洗高林, 清飙矫云翮”,“神渊写时雨,晨色奏景风”,“青松夹路生,白云宿簷端”。这种诗后人极意做作效仿,却终难望其项背。
这种琢炼并非单纯琢炼语言,而是“琢炼”人格精神的结果。《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起笔云:“虚舟纵逸棹,回复遂无穷。”写舟行之妙,不可思议。“逸”字用得奇,实是“逸”怀之象。“回复无穷”,是从上“纵”字来。“神渊写时雨,晨色奏景风”,用“写”字“奏”字极尽妙丽地状出“神”字“晨”字之韵来。可见即使雕章琢句,陶渊明诗亦有风流孤迈、旷世独立之逸致。赵文哲《媕雅堂诗话》认为:“陶公之诗,元气淋漓,天机潇洒,纯任自然。然细玩其体物抒情,傅色结响,并非率易出之者, 世人以白话为陶诗, 真堪一哂。学者须从此著神, 然亦不宜多学。” 将陶诗比平常白话,确是皮毛之见。陶诗平淡,不是无绳削斧凿,但绳削斧凿到自然之处,令人只见其平淡之妙,不见其斧凿之痕、绳削之迹罢了。所以后世学渊明诗,往往有意为平淡之语,却不知渊明无斧凿痕、绳削迹那种极尽天然的人工制作之妙,已在其中矣。如《读山海经》一诗中“华丽”的句子:“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瑶流。”岂无雕琢之功? 此处“明玕”谓竹,“清瑶”谓水,真是将朴素与绮丽妙合一体。许多时候,陶诗直是口头语,乃为绝妙词。极平淡、极色泽。平淡中见丰腴绮丽,就是极富色泽。铁凝小说《大浴女》中引罗丹的话说:“独创性,就这个字眼儿的肯定意义而言,不在于生造出一些有悖常理的新词,而在于巧妙使用旧词。旧词足以表达一切,旧词对天才来说已经足够。”所以对于天才的诗人来说,只用“极平淡”的“口头语”却能达到“极色泽”的“绝妙词”就是可能的。
至此,我们将会更准确地说陶渊明的诗还不是全然“清蒸”烹制出来的,而是有一道隐然不见的“红烧”程序。就像中国的广东菜对肉类的烹制何以表面看来清爽不腻,却往往是先经油炸再清蒸的,所以味厚。我们也就容易理解陶诗何以能“平淡朴素”与“警策绮丽”妙合一体,道理是类似的。
陶诗在高古浑厚之中又别有一种精致清丽的语言风貌, 这是汉末古诗传统与陶渊明所处的中国艺术自觉时期那种工于造语、讲究艺术形式的融合,故臻于将“高古浑厚”与“精致清丽”妙合一体的艺术化境。此化境乃是语言形式的精致性与思想情感的高古浑厚之超逸性的统一。其精致的外在表现是诗中的文字只自然地承载作者高古浑厚的思想情感,却不喧宾夺主地“跳”出来“独自”暴露于读者的视野中。换言之,陶渊明诗中的“文字”颇具“道家风范”:保持低调,不事声张,但是却“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其超逸性则是因其思想情感深具哲学的超然而同时又能高度提炼语言而形成的语言总括力,所以其诗外在特色就是“简炼高妙”。超逸之“逸”的本质是“神”的精华和提炼。还需要强调的是陶渊明的诗在极“自然”中,却用了不少典故,《庄子》、《论语》等等经典被他运用到了十分纯化的境界,这又是陶渊明的大本领;关于这一点,在近人古直《靖节诗笺定本》中有详细的注明。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认为陶诗的特色是“恰到好处,适得其中”,在其著名的《陶渊明》一文中,朱先生有一段分析文字正支持着我们“中庸的陶渊明”的观点:
陶诗的特色正在不平不奇、不枯不腴、不质不绮,因为它恰到好处,适得其中;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它一眼看去,却是亦平亦奇、亦枯亦腴、亦质亦绮。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化境”,渊明所以达到这个境界,因为像他做人一样,有最深厚的修养,又有最率真的表现。“真”字是渊明的唯一恰当的评语。“真”自然也还有等差,一个有智慧的人的“真”和一个头脑单纯的人的“真”并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Spontaneous 与naive 的区别。渊明的思想和情感都是蒸馏过、洗炼过的。所以在做人方面和在做诗方面,都做到简练高妙四个字。
这是一种无斧凿痕的精致性同简妙之中饶具深刻隽永的思想感情的超逸性的结合。在表面平淡无奇的语言文字之下,全然充盈流溢着卓越非凡:“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 陶渊明只要白描情景物象, 便可以达到空明澄澈、气韵清高而难以摹习的境界。
陶渊明体味到的全是人生的真趣,他捉到了“鲜鱼”;他用了“清蒸”手法,虽然并未绝对排斥“红烧”手法,但他未露痕迹,一片神行,他因此而保留了“鲜鱼”的原味;更可贵的是,他也没有“熬成一大锅汤”,做到了简妙。虽然“气势”不“夺人”,“力量”不“雄辩”,“气象”不“轩昂”,却自有一种非凡的气势、强劲的力量及超逸的气象。尽管陶渊明的诗也“不追求强烈的刺激, 没有浓重的色彩, 没有曲折的结构”,但我们知道一流的艺术境界从来都不以曲折复杂的情节、强烈刺激的人物冲突来显示自己的价值的, 这往往是三流作品的趣味所在。一流的作品总是超越了那些枝蔓的情节、激烈的冲突而将笔墨意趣集中在对人物精神历程、情感状态的“清蒸”式的呈示上。所以一流的作品一般不纠缠、滞笔于“感情的事件”,而是着重在“感情的境界”上运笔行文。艺术是超越于肉体性、物质性的有关灵魂的、精神的事!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才说“艺术可以帮助人类认识到心灵的最高旨趣”!
更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同样表现自然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也绝不能简单地类比中国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他们之间依然是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的。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华兹华斯的专著《华兹华斯诗学》中认为,在华兹华斯进入中国文化氛围时,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对华兹华斯诗学产生了转换与“遏制”(Containing):
传统文化总像一把无情的剪刀, 把外来文化中不合自己需求的方面剪去。当华兹华斯的诗学思想进入中国文化观念的视野时,就已经失去了它的神性,失去了它对黑暗中的人的拯救力量。于是华兹华斯在中国成了一个对现实不满、明哲保身、徜徉于山水的隐居诗人、逍遥诗人。中国传统文化顽强地把西方文化中“堕落与拯救” 的主题改换成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定居湖畔自然成了对现实斗争的逃避, 定居成了隐居; 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被转换为寄情山水;对自然的深情体悟和哲理思考被等同于山水诗。中国文化拒不接受华兹华斯诗学思想中的救赎主题, 这就使得哲理的、沉思的华兹华斯变得简单而平面。因为从关心贫苦人民的生活处境来说,他关心的是那么地不彻底;从中国人熟悉的山水诗来讲,他的“山水诗”又完全达不到“忘我”的境界。于是许多论者不能理解,这么一个华兹华斯何以在西方文化史上占有那样重要的位置。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作用之下将华兹华斯与陶渊明进行对比几乎成了中国华兹华斯研究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