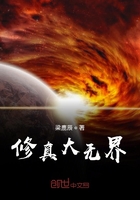覃夕见鹃姨许久不回转便让我留下照顾四哥,他自己则外出购些吃食回来。
我忐忑上楼推了房门。
灯影摇曳,四哥垂首抚额保持着方才的姿势倚在床榻上,神色郁郁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低着头走过去,无声落于他塌边。
他抬头勉力而笑,温和问:“她走了?”
我缩了手,诺诺点头,想说些什么却终究开不了口。
他反是过来握了握我的手,语带歉然,“是四哥不好,叫你为难。”
我喉头梗咽,唯唯愀然却接不上话,只好问他身子好些了没。
他故意支起身来笑道:“没有不好的道理。整天吃四爷送来山茸海珍,补得未免过了头了。你呢?你身上的伤……”
一听他说话的气儿都是虚悬的便知是安慰我,心下一紧,顺着他道:“我好多了。覃夕一会带些小菜回来,我给你煮些白粥如何?鹃姨怎么晚了也不回来。”
“这些天她皆是戴露而出披星而归,恐怕还要一会。”他许是撑得久了,嘘了口气道:“也不用麻烦了,覃夕回来我们随意将就点就是了。”
我不禁稀奇起来,鹃姨对四哥甚是重视怎会丢下伤重的他独自外出,且日日如此?于是急急问道:“怎会这样?那这几日都是谁在照顾你?”
“四爷底下的人。你放心,他们照顾得很周到。”他宽慰我道。
“胡说!不然这会怎么没人来服侍你?”我眼圈微微一红,驳他。
他眉间似有难言,片刻才道:“因为今日梅要过来。”
我内里清冷自嘲,不然呢?便压抑了鼻中酸涩,叹道:“你……你打算怎么办呢?”
“提亲。”他朗然答我,病容中目光亦烁如星辰。
我胸中丘壑起伏,头垂下去下颔擦到衣襟上的棉锦有些摩挲,哀凉道:“师父准不准先不说,师伯一定不会准。”
“月儿,难道你认为梅该留在师伯身边?”他抓住我肩膀低下头欲看穿我的表情。
我连连摇头否认,“我从来就没有这样想过,真的。”
“你不明白,看着她活得像只笼中之物,那种心同刀绞。”他放开我,脸上急切而心疼。
我凄然一笑,不明白?怎会不明白,却只能出谋道:“待回到宛居,先自师父旁敲侧击吧。要从长计议,你毕竟是宛居大弟子,梅师姐又是陆公馆的大师姐。若是联姻,关系重大……”
“这许是我入行最为无奈之事。”他眼中划过一缕淡淡清愁,“宛居大弟子……月儿,我此刻倒真有些羡慕若风……”
我忙捂住他的嘴,恨道:“你再这样胡说,我说什么也不帮你了。”继而陈迹,“我们这一行,固势联姻再正常不过了。师父视你如子未必不可,况且梅师姐本就是自宛居出去的人。至于师伯那里……欠他一个,还他一个就是了。”
“什么意思?”他听我话里余音,蹙眉问道。
“江湖上谁都知师伯底下弟子各个冶器制药的功夫上乘,身法却稀松平常。而宛居的弟子却是相反,所以我们许多行动上所需之物却被陆公馆掣肘。”我慢慢道出自己的想法,“梅嫁到宛居正是解吾之困,而作为交换我们家亦要嫁过去一个女弟子平师伯的气,这就两全了……”我越说越小声,到最后是几不可闻。女弟子,宛居从来只有一个女弟子。无言是个陪人,年纪太小不说,除却轻功了得其余皆是平平。
如若四哥下定决心要上陆公馆提亲,照陆逸明锱铢必较的性格这可说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法子,就是以人易人。
自师父抛出宛居正统的事于我后,不知不觉心已凉了半截。我多年侍她并无差池,她却多番质疑试探我,可见我这个唯一的女弟子在她心内不过尔尔。若是此番真的答应她嫁给四哥,一来四哥与梅燕好,那情形只有日渐靡深,万万是消减不下半分了。届时我反成了一个夹心人;二来即便师父不吩咐,我亦不希望伤了四哥覃夕兄弟情谊。覃夕对我……我从不是毫无知觉的人。
如此一来,远嫁还能成全四哥和梅二人,倒成了出路了。只是一想到陆一竹那张阴鸷凶狠的脸,腹部就翻腾绞痛得厉害。
四哥越听越诧异。他向来缜密,唯有碰上梅的事难免乱了方寸。此刻他恍然大悟,大声叱责我道:“你不许动这种念头!想都别想!”
“可到时候你就会明白,这由不得你。师伯的个性,多年来你我未必不知。不给些好处,他怎肯放人?”我抬眼楚楚一笑,心尖几乎沁出血来。
他怔一怔,或许我言辞细密他无可辩驳。须臾,他嘴角缓缓扬起一个坚毅的角度,定声对我道:“不管发生任何事,我都不会拿你的终身去换我和梅的幸福。我不会,梅也不会。再者覃夕也不许,你去嫁陆一竹他怎么办?这事,依你所言,要从长计议,梅目前的处境算不得太糟。再过些时日,或许会有各方都能妥协的契机出现的。”
我心平气和。虽是应他,却知他心里亦是无奈。终于,思绪仿佛被一只手轻扯了一下,细细回味他的话,大彻大悟。
“你以为我和覃夕?!”我险些窒气,怪叫道。
“你以为我是傻子?”他捏拳坦然笑道,“是前一次出门前的晚上他特意跑来告诉我的,不然真想看你们俩一齐瞒我到什么时候去。覃夕虽是偶尔浪荡了些,待你倒是真心的。再说你们年纪相仿……”
我有种待覃夕回来直截将他丢入楚江涛涛之中的冲动。诨说这种话,纵使我跃入黄河也洗不净了。
我心内一长啸,听到四哥说:“月儿,四哥已是这般。前车之鉴,更不能叫你跟覃夕走我和梅的老路了。”
这会子,辩驳还有何用?只好木讷答道:“劳四哥费心了。”
许是梅方才在屋子里焚了一线香给四哥镇痛,这会香虽是焚尽了药性却未曾散去。再缓和了情绪,问道:“鹃姨这些日子究竟是做什么去了?她极少离开师父超过两日的。”
“我辗转问过她,她也是闪烁其词。”四哥抬了抬下巴。
四哥甚少过问长辈行踪,我不由奇道:“四哥可是发现什么玄机?”
他示意我去取放在伏案上的一张报纸。我过去拿起一看,是日期为傅志诚死后第二天的城中新闻,头条自然是傅的死讯,亦是如我们谋划佯装成功,说他自戕如何。
我觉得无甚疑点,便一目数行扫去,越往下读越是冷汗连连。
新闻稿中赫然写着:“……于某处发现傅某遗书一份,内容为其生前所有财产尽归其独子傅栋阳所有……”
“遗书……我们什么时候给他准备了这样的遗书?!”我惊呼道。
推荐一本同频道好友太极低手的好书:[bookid=1454739,bookname=《国术之拳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