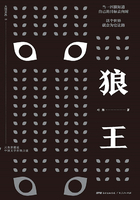1874年的夏天,我正在利物浦,准备到纽约去为布龙松,雅内特商号处理商务。我叫威廉·雅内特,这家商号的另一个合伙人是泽那斯。布龙松,不久前,商号破产,布龙松不堪受此打击,穷困落魄而死。
在结束这次生意后,我深感疲倦与心力衰竭,想到延长海上的航程会是惬意与舒心的,便没有登上条件良好、床位众多的蒸汽船,而托运着一大堆购买的值钱货物订了“摩罗号”的票。这是一艘英国的船只,当然只有很少的床位供旅客使用,整船上唯有我,一位年轻的小姐,还有她的仆人——一个中年的黑女人。开始,我奇怪于一个英国女孩竟如此孤身一人,仅带一个侍者出行,但后来她向我解释说,自己被南加州的父母遗弃,女孩的父母亲双双死于同一天。女孩的父亲祖籍在德文郡——这个地方显然在我的记忆中不同寻常,甚至在后来与女孩的交谈中发现,她父亲叫威廉·雅内特与我同名。我知道,自己家族的分支有一部分在南加州定居,但他们的事我不太了解。
六月十五日,摩罗号从利物浦出发。许多星期的航程中,都是清风拂面,万里碧空无云。船长,那个令人敬佩的水手,除了在餐桌上,其它时间很少与我们交流。于是我与那位年轻的小姐雅内特·哈罗德加深了进一步的交往。事实上,我们几乎一直在一起。说句真心话,我始终努力在分析与试图满足。她不时激起我的对她的奇异感觉与情绪的好奇心——那既神秘又新奇,难以解释,但这一切强烈的吸引着我,并不断促使我去反复探寻她,她心底的秘密,但一切试图与努力都无实现的希望。但我可肯定,那至少不是爱情。在肯定自己的意图与她对我的诚恳之后一天晚上,我决定冒险(我记得那天7月3日)。我坐在甲板上笑着问她,是否她能帮我解决一些心理上的疑问。
她沉默片刻,一直背转着脸,我开始害怕自己的行为是否有些无礼与太不慎重。然后,她沉重地望着我的双眼。一时间,我的思绪被一种强烈的奇异幻觉所占据,是超意识的。似乎她在望着我——穿透人心的目光,在那眼睛后面隐藏着无限的——有许多人,男人,女人和孩子,那些脸孔居然我都有一种奇怪的曾存在却已消逝的熟悉之感,那一切聚集于她一身,通过同一双眼睛尽力地温柔热切地望着我。船只、海洋、天空——全都不见了,除了眼前的这奇异、幻觉似的人物的场景,别的我什么都看不到。突然间黑暗笼罩我身,我逃不出来,似乎有人逐渐弄暗灯光,眼前的甲板,桅杆绳索渐渐被其灰暗包裹。哈罗德小姐逐渐合上双眼靠在椅上,沉沉睡去了,膝上的书本打开放着。被一种不知名的动机所促使着,我看了书页的上部分,那是一本有些奇怪与罕见的书:《丹尼克冥思》,小姐的食指停在这一段话上:
对所有人而言,它变成了悲伤的离别,变成了在一个恰当的时机从肉体上分离而去;因为,小溪们愿意带走每一个被强者驱赶的弱者,因此在这里,亲族的道路纵横交错,他们的灵魂被迫相随,虽然他们的肉体正去向早已指定的、不能知晓的旅途。
哈罗德小姐渐渐醒过来,微微颤抖着,太阳已落下沉入地平线,但并不冷。没有一丝风,天空无云,也没有星星。船长和站在船边测量察看的技术工人在下面说着什么。“老天!”我听见他的叫声。
一小时之后,沉船上汹涌的浪花将我牵着的哈罗德小姐冲开得无影无踪。她消失在一片黑暗与茫茫海水里。胡乱中我抓住一件浮物,我似乎得救了。
我被灯光惊醒。我正躺在蒸汽船上十分熟悉的卧室的床上。沙发对面坐着一个男人,半裸着正要睡觉,且在看着一本书。我认出了他——我的朋友古当·多勒,那是在利物浦上船那天刚认识的,当时他极力要求我陪他乘布拉格号。
不一会我叫他的名字,他简单地回答:“嗯,”翻了一页手中的书,并没抬眼看我。
“多勒,”我说:“他们救了她吗?”
他走过来望着我,微笑着似乎表示很好笑。很明显他以为我还没睡醒。
“她?你指谁?”
“雅内特·哈罗德。”
他的笑容突然变成惊异;他疑惑地望着我,什么也不说。
“你等会再告诉我好了,”我说。
一会后我问他:“这是什么号船?”
多勒又盯着我,“蒸汽船布拉格号,从利物浦到纽约,由于故障停了三周了。主要的乘客有古当·多勒先生,还有同样愚蠢的威廉·雅内特的先生。这两个糊里糊涂的乘客同时上船,但它们停住了。”
我坐起身来,“你是说,我在这条蒸汽船上已呆了三周?”
“是的,现在正是7月3日了。”
“难道是我病了?”
“都像三角铁架似成天躺着,只会按时吃饭!”
“我的天啊!多勒,这有些奇怪啊!是谁那么好心,我是在摩罗号沉船上获救的吧?”
多勒变了脸色,他惊诧极了,之后他走进我用手指放在我的手腕上。不久后,“你是怎么知道雅内特·哈罗德的?”他平静地问。
“那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样认识她的?”
多勒先生盯着我看了好一阵子,似乎在考虑些什么,之后重坐回沙发上,说:
“我怎么知道?我与她订了婚,在一年前,我们在伦敦相识,她那在德文郡最富有的家族残暴地要拆散我们,于是我们私奔了——私奔,就是遇见你的那天,我正到岸边也准备上船,当时她与她的女仆,那个黑女人正与我们擦肩而过登上摩罗号船。她不愿与我同行,那样会好一些,用以避开别人侦查的危险。现在我正着急呢,这该死的机器出了倒霉的故障,拖延我们的时间,摩罗号船将先到纽约了,那可怜的人儿该怎么办啊!”
我仍躺在床上,呆住了几乎无法呼吸。但很明显,刚才那奇怪的经历定会令多勒不悦,于是过了很久,他说:
“顺便提一下,她只是哈罗德家的养女,她的母亲打猎骑马时摔死了,不久父亲也因悲伤自杀去世,都在同一天。没有人想至那个孩子,过了很久才有人收养了她。她在悲伤与忧郁中成长。”
“多勒,你在看什么书?”
“噢,是《丹尼克冥思》,那书非常离奇,是雅内特给我的,她碰巧有两本,你要看吗?”
他拿给我,书本不小心落下,开着的书页可看到一段话:
“对所有人而言,它变成了悲伤的离别,变成了一个恰当的时机从肉体上分离而去;因为,小溪们愿意带走每一个被强者驱赶的弱者,因此在这里,亲族的道路纵横交错,他们的灵魂被迫相随,虽然他们的肉体正去向早已指定的、不能知晓的旅途。”
“她,她也,也在看这一段。”我想说,但恐惧掐住了我脖子!
“是的,或许你愿意告诉我你如何知道她的名字以及她坐的船怎样了。”
“你是在梦里与她对话。”我说。
一周后,我们到了纽约码头。但那里,从未听说过摩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