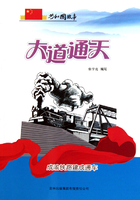1989年初,四川师范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诗社——东方诗社成立。李文化、何春、张述鸿、南江、陶诗文、山杉、印冬冰、饶勇、殷明、许志君等,包括我在内成为诗社的发起人。著名美学家高尔泰,《星星》诗刊的孙静轩,四川师范大学的曹万生及石光华、万夏等是诗社的顾问。记得当时,第三代诗人中的贵州大学的郑单衣,四川大学的赵野,重庆大学的钟山,四川大学的查常平,四川师范大学的老师陈小平也曾有过指点。东方诗社只出了一期刊物《东方》后解散。“社友们各自东西,一些兄弟被迫提早沦落江湖”(山鸿:《我所认识的诗人们》,求贤网2011年1月31日)。事隔20年后,东方诗社有了一次集体纪念。2009年,《星星》诗刊在第8期上用了30个页码来专门刊发东方诗社当年13名诗人的诗歌。当时青春年少,如今人到中年,诗歌已经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抛弃了一大批曾经的狂热追求者,像我这样信徒一般虔诚的写作者也为数不多了。
关于诗歌的困境和出路。其实作为一个业余诗歌写作者,这样专业的问题我是没有底气来回答的。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网络文化、电脑文化正在侵蚀着我们既有的文化形态,物质主义征服了整个世界,诗歌能做什么,出路在哪里,这会是一个恒久的话题。但当代诗歌同现实之间关系的张力,使得如何回应现实的设问变得更加急迫。“……在像人口一样高度密集的、复杂、活跃、混乱、多变的现状面前,诗人的选择主要有两种:其一、成为新的隐逸派,‘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语出《周易》),以便在语言中自处;其二、向屈原和杜甫学习,关心天下事,且能够‘随时敏捷’(语出杜甫),从而不使亲历者的历史记忆与见证散逸于语言之外。二者的交互影响或许还产生出第三种,即着眼于启示未来的,更博大的综合,它取决于诗人个人的抱负与时代的机遇。”(宋琳:《诗与现实的对称》,载《当代国际诗坛》(4),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欧阳江河认为,诗歌写作和现实,和贫富,和经济高速发展之间,不是一种成正比的关系,诗歌还是和内心更相关。写诗,也是我们对智慧迷恋的一种形式,所以和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诗歌最大的力量就在于它背离现实,而不是顺应现实的力量。(参见欧阳江河:《公开活动现场纪实》,载《当代国际诗坛》特辑,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而于坚却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正进行在激烈的转型阶段,今天我对现代化已经变成了困惑和怀疑。如果现代化旨在消灭古代社会的黑暗,消灭一切朦胧和混沌,把一切都变得清楚,用数字和货币来衡量的话,我对现代化的前景是不能表示欢迎的。当我们拥有许多物质的东西时,我忽然发现,我们的内心非常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