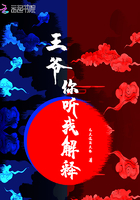每一个周末时分的来临,城市的天空弥漫着脏乱差的气流。我习惯于在每一个这样的周末穿不同颜色不同款式不同质地的睡裙以同一种姿势站在中关村知春里N座11层的阳台上看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男男女女搂搂抱抱、亲密暧昧。心理医生把有我这种行为习惯的人称作是有“窥视欲”。
我的阳台小得可怜,只能放下我和我的猫:咪咪。它就被我抱在怀里,像我的孩子。
我一直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最好是一个男孩。二十八年来,生为女儿身的生理上的苦我是吃够了,每月一次的痛经把我折磨得恨不能立即投胎做个男人。我在十八岁那年就为教我英语的大学老师堕过胎。这段师生恋以最快的速度传遍校内外,我成了别人眼中的“坏”女孩,年纪轻轻就勾引别人的老公。
咪咪是我在一个散步的傍晚捡回来的猫。
我是一个像热衷于洗澡一样热衷于散步的女人。喜欢洗澡是因为我喜欢站在水雾里看镜子里的自己,即便是不洗澡,我也喜欢穿一件半透明的睡衣坐在镜子面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什么也不去做,什么也不去想,就是盯着镜子里面的那个人发呆。有一个走进过我生活里的男人曾经尖锐地指出我的这种行为叫自——恋——狂。确实,我是一个恨不能立即把自己抱个满怀的自恋女人。
可自恋又有什么不好呢?最起码我不用像一般庸俗女人那样成天纠缠着一个男人问自己漂不漂亮,问你到底爱不爱我,自恋是一种自给自需的行为,是不需要外求的满足。做个自恋的女人总比做一个自卑的女人要强百倍。
我用散步来延长我的思维。通常,我所有的思考都在散步中进行。散步使我的思想变得愈来愈敏锐深刻。散步可以提醒我其实我还很有魅力。
我在散步的途中会引来身边的行人向我行注目礼。我一副冷漠不染尘埃的样子,没有人知道我在心里正在策划着能有一段艳遇发生。我是一个喜欢奇迹的女人。比如在北京的街头拾到一只宝贝猫,最好还能捡回一个梦寐以求的男人。
我不知道咪咪原先的主人是谁。我不愿相信咪咪是一只被抛弃的猫,我更愿相信咪咪只是和它的主人走失了。所以一度,我每晚都抱着咪咪去那条街道上散步。
咪咪陪伴了我三个月,它既充当我的玩伴,我有时很贪玩;又要充当我的情人,我会对它说一些很动听的情话;还要充当我的孩子,特别是我把它抱在怀里的时候,那仿佛是我和一个男人生养的孩子,是纯粹的爱情结晶。
我点燃一根细长的“绿叶”女士香烟,顿时,一股清凉的薄荷味从我的口腔流进我的脾胃。
“绿叶”在北京的烟摊上并不多见,我是在一次无意之中到国际展览中心开会发现的。后来“绿叶”就取代了“圣罗兰”。
平日里,我在寂寞无聊、郁郁寡欢的时候就吸一两根“绿叶”。我不以吸烟为瘾,我深知吸烟影响美容。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看重美丽,只对爱情上瘾。
陈松买“绿叶”送给我,他是惟一一个给我买烟吸也不发表反对意见的男人。他这么做并非表明他赞同我吸烟。他是出于爱我。陈松说只要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只要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我想做什么他都支持,甚至他都可以为我去做。多好的男人,可我就是爱不起来。假如他可以为我杀人,那可能会是另一种情形。
陈松是我一个关系看上去有些暧昧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执着的追求者。他这个人很有些“各色”(北京方言,特别的意思)。
我们相识已整整三年。三年,对于现在这个流行快节奏的社会而言,有些男女恐怕早就从相识相恋同居到婚嫁生子一条龙办完事了。而我和陈松之间一直处于这种既冷不到哪里去也热不起来的阶段。
其实陈松生活里有一个女朋友,他们同居在一起。那个傻女孩全心全意地爱着他,就像曾经的我傻乎乎地爱着另一个男人。是不是每个女人都会有一段时间是百分之百的“爱情傻瓜”?那个女孩甚至还知道陈松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追求我。她亲眼看见过陈松的老板桌上摆放着我的美人照。
陈松除了定时给我买“绿叶”女士香烟,还会在每天请花店为我送来一束玫瑰花。掐指算来,一千多个日子从未间断过。我也只收他送给我的这两样礼物。
陈松是一家证券公司的老总,毕业于北大经济管理系,其实年龄才三十岁。但人看上去长得特老成,可在我面前,我的“狐狸”眼睛能看得他在我面前老练不起来。他的不自然或者说不自信被我一览无遗。他曾经就由衷地感叹女人不能太聪明,一眼就能把男人洞穿的女人,特别是美丽女人,更是让男人惧怕。
我笑,很优越的一种笑。陈松拿眼前的我没辙。
有时,我会直愣愣地盯着坐在我面前故意装出一副什么都无所谓样子的男人发愣,不明白面前这个在人前人后浑身上下充满了北京人优越感的男人为何要在我面前受这种“洋”罪。
反正他落寞我不难过。爱与被爱原本都不是错。
我的目光又停滞在某一点上。这时,陈松伸出一只手张开手掌在我的眼前晃动,他看着我直愣愣的眼神小心翼翼地问:你到底是怎么着?你又发什么呆?为什么总是千金难买你一笑?
我骨碌碌地转动了一下眼珠,推开已伸到我眼前的那只手,依然故我地对他说: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的眼睛是陷阱,掉进去容易,爬出来难。说完,我的眼珠又故意往东南西北方向转了几圈。
如果真是陷阱,那也肯定是温柔陷阱。陈松嘿嘿地冲我坏笑。
我对陈松一直很坦然。因为我不爱他。因为我知道他是真心地爱我。
我悠闲地坐在我房间的靠椅上,实话实说,我没法让自己爱上他。陈松熄灭了手头燃了一半“555”,他用双手轻巧地将我从坐椅上提起来按倒在床上,这是他第一次以这样野蛮的方式对待我。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着叫喊:你不可以碰我,讨厌,你会后悔的,我不会原谅你的。
但是所有的挣扎和叫喊都无济于事。陈松北方人特有的高大身躯重重地压在我小巧的身上,他的吻爆发得粗野而又狂乱。我紧紧地咬住嘴唇,头不停地做着无力的摇摆。
那一刻,我心如死灰。陈松,你知道吗?你的粗暴摧毁了我对你掩埋于心的歉疚和感动。
我放弃了反抗,确切地说是被迫放弃了反抗。我全身虚弱地任凭他的双手在我的身上揉捏。我的眼泪无声地流淌,一滴一滴地落到床上,打湿了他的手背。陈松这才猛地意识到他双手用力过猛弄疼了我。
他松开粗暴的手,看着蜷缩在床边一角泪流满面的我,满脸的懊恼,一种龌龊感占据了他的大脑。他阴森森看着我说:你是个磨人的女人,你犯贱,你还在想着那个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你生命中的男人?你依然对他心存幻想,你是个贱女人。
陈松沮丧的背影消失在我的门外。我躺在床上,睁着一双空洞的眼睛,大脑里一片空白。心里有一种比被人强暴了还要让人心灰意冷的感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用玫瑰花瓣洗澡。我的卫生间只有三四平方米,内设一面大镜子和抽水马桶。我喜欢洗淋浴。我惧怕泡浴缸,因为浴缸总是容易让我联想到恐怖片里的鲜血和死尸。洗澡对于我而言是一件痛快的事情。我的手指轻柔地滑过我每一寸肌肤,清香的浴液泡沫在我的胴体上摩擦,水龙头喷射出来的水体贴地流遍我的全身,我感到浑身上下一阵阵酥软。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喜欢站在镜子面前,隔着一层层水雾在哗啦啦的伴奏声中挥动着我的四肢,在水龙头下面独自跳一种灵动的舞。
我用浴巾裹住身体,赤裸着柔软的身子滑进软绵绵的被子里。我主张裸睡,因为我从一本杂志上看到有健康学家认为裸睡有助于身体健康。
裸睡的女人是最本色的女人,最本色的时候是面对我自己。我和男人同睡一张床是穿着睡衣的,我乐于体验被男人解开衣扣的那种感觉,跟着感觉走能够有助于性爱达到高潮。我是一个讲究情调的女人,特别是在和一个男人谈情说爱或者做爱的时候。
周末午夜十二点钟,北京城里有人在喝酒,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卖艺,有人在蹦迪,有人在哭泣,有人在犯罪,有人在生病,有人在看电视,有人在吵架,有人在出生,在人在死亡,有人在睡觉,有人在做爱,有人在孤枕难眠……
我认识过这样一种类型的未婚女人,当她得知我是一个独居的单身女人时,她会发出一声惊叫,继而会问我一个人睡觉害不害怕、孤不孤单?这种提问带有很大的矫情成分,看似小女孩似的天真实则泄露了她私生活放荡的一面。一个不结婚的女人每天都有男人陪着睡觉,还在我面前装小女孩的天真,甚至还夹杂着一丝炫耀的成分。这种离不了男人的女人肯定和我做不了朋友。
我枕在靠垫上,点一盏台灯看法国作家左拉写的性爱小说《爱情的一页》,房间里始终流淌的是席琳·狄翁充满质感的音乐《My Heart Will Go On》。它是赚了我三天眼泪的《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我最要好的女朋友艾艾特地为我买的。
下面我该用怎样的口吻介绍我的这个要好的密友呢?艾艾在北京一家医院妇产科做护士,有洁癖。她是东北人,会烧一手好饭菜,人长得高高大大的。她漂亮但不惊艳,这一点有别于我的美。艾艾说我是一个放在黑暗里也能发出亮光的危险女人。我不依不饶地抢白:我就喜欢迷惑男人的眼睛。
艾艾有着做医生的美德。她善良、体贴,有北方女孩特有的胆识。我害怕走夜路,艾艾总是像英雄一样陪我走夜路。我们曾相约着走在深夜的北京一条胡同里,放开嗓子唱《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艾艾是我除了猫之外走得最近的人。很多时候,她就像我的精神支柱。她关心我的生活起居、情绪变化等一切与我相关的东西。她是我陪一个女朋友去她所在的医院堕胎认识的。我们一见如故,成为了密友。
艾艾的生活像我一样没有男人。她是一个早已不对任何男人心存幻想的成熟女人。她说我之所以还为爱所悲是因为我对男人还心存一份天真的幻想,这将成为我的致命伤。
在这样的夜里,我很想给艾艾打个电话,告诉她在这一刻是我在想着她。对艾艾,我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有一次,她被单位派到上海去学习一段时间,她走的那天,我像丢了魂似的。我接通她的电话,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叹了一口气就挂断了电话。结果艾艾猜到了打电话的人是我,于是为了我她放弃了这次学习的机会。
我对艾艾的思念,我想她是会有感应的。
艾艾,身为独身女人的艾艾,你才是最聪明的女人,不为爱所喜不为男人所悲。艾艾,亲爱的艾艾,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也会这样地想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