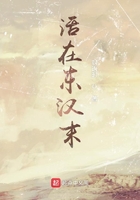一
唯一的,香山的一片荷叶捂住了那时整个的夏天。
我少年开始的时光只属于那时的绿荫,从香山的影子里压迫下来,以后所有的夏天,我都在那片湖泊的阔叶下获取那种沁人的阴凉,获取与湖与山息息相关的那份奢侈的宁静。
不断地使我的少年时光无限地萎缩,无限地扩大。
如果我知道那种日子以后不再有,我就不会那样轻易离开。
当然,也不可能长久地躲藏在叶下,我真的是多么留恋那时的荷叶,或是追忆与荷叶有关的日子。
我没有参与它们的枯萎,正如同没有经历生机勃发的成长。
当满天繁星一弯弦月悬挂在湖泊上方,黑色蜻蜓、一跃而出的鲤鱼和以后凋谢的荷花花瓣制造出大量的流言蜚语……沉默,迅速与湖水一样,还原,成为另外一种天然。
我想,如果我的生命中仅仅享受着自然里这种最茂盛的时光,那么不仅仅是一种幸运,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是肯定充满了同样美和痛苦的缺憾。
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一片荷叶,它与我和夏天同时相遇,一定带走了许多的夏天。至今,覆盖着我的,是很多能够把人焚烧成灰烬的夏天,是这个季节必须到来的那一片唯一的荷叶。
连天的叶子抵达天际,而我,只属于那一片。
我在复述荷叶的此刻,忘记了其他的许多种类的叶子。
当我正走向当年的湖边小路的时候,忘记世上还有许多的路。
二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条河?
初夏,我走在一条河的河堤上,几乎与大地平行,如果不走在这里,在别处根本看不到这条河。
两边是望不到边的棉花地,绿油油的杆子在近处看稀稀朗朗,远一些的地方是青乎乎、黑压压的,直抵天际。
我走在这里,感觉走在香山无垠的中间,通江的河道在极其松软的沙质土壤中穿行,显得格外地汹涌,本身很缓慢的河水,也充满着一种极其强大的穿透力和破坏力,两岸的青纱大量地剥落、沦陷。河水不断地冲刷着,带走刚刚崩塌的泥沙的同时,也不断地加深了河床的深度……
我一个人走在高低不平的河提上,瞬间感觉像走在一只巨大的布谷鸟的脊背上,在瓦灰色的翅膀中间,边栖息边警觉地张望着,翅膀无限地张开、延伸,朝着河道两边盲目地飞翔……
远远的黑色版块的村落和悬浮在半空淡蓝色的山林仿佛在翅膀上一直地滑翔,保持香山一种特有的安详、宁静和与生倶来的平衡。
河水比想象的更加混浊,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充满耐性,使我在不断下陷的感觉中,感受翅膀不停地竭力扇动,在随时的坠落中保持自身的平衡。
河流像从天而降的铁楔打进香山的沙壤里,村庄、湖泊和草滩上徜徉的牛羊在棉花地扇起的翅膀上面被迫地飞行。
飞行或者坠落?香山以自然的形式演绎,不同于世界的其他地方,因为我的到来,从此也证明了这种形式的无处无时不在。
深陷,沦陷的这些关于这条河的词汇,在一片江滩的圩区沙地上悄悄发生着断裂,形成了一个通江河道,但是也仅仅在河道的范围内发生改变,不延伸,不暗喻,几乎不与世俗世界发生任何干系。
但是,少年时期给我带来巨大愉悦和震撼的河流,为什么常常在我的生命里出现?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包括情感、挣扎,幸福与苦痛。可惜的是,除了飞行与坠落的自身形式,我至今不知道这条河任何内在的征象,就如同生命中继续发生的一切。
离开了无法离开的香山已经多年,我是一直在坠落还是在飞翔?
三
油菜花开,轰轰烈烈地开了。
我站在它的边缘,如同站在那个遥远的、自从出生就生活的城市,那同样无法参悟的喧嚣嘈杂的一切,巨大的芳香把我阻隔,拋弃在它的外围。我知道,今生再也无法站在油菜花的中间,就如同我从此不能进入的城市喧嚣而丧失理智的内部。
一种外在的力量来自征服、拒绝和诱惑,来自与自然一同伪装成的不可抗拒的一切。我以后的日子不是进入,而是在竭力寻找一种与之抗衡的力量的过程,这会不会耗尽生命中所有的色泽?
我站在一株油菜花前面,我会不会成为它们的颜色,或者影子?
现在,我早已离开了那里,在另一个城市小区的窗前,七月的热浪从天而降,我为什么仍然看见铺天盖地的油菜花……
我从来没有生活在它们的中间。
四
香山是一座普通的山。
没有更多的人知道它的名字,它矗立在皖西与赣东的交界处,像所有边界和边境名字一样孤立、冷傲,像天下的生字一样的冷僻。
南边的江水长流不息,北面才是我曾经去过的小村庄,很安静的样子,散落在湖泊低洼的滩地之间,当然还有高高的杨树,土坯屋,油坊和一直在菜地边溜达的小狗。我更多的时候活动在它的南边,那里有一直汹涌的江水。
为什么这天然的屏障却带来不断汹涌冲击的一切?
其实我常常爬上香山的山顶,凝望着江水,平缓,凝滞,好像从此不再流动一样,一旦我走下山脚,又感觉到江潮猛烈的撞击,整个夜晚的香山仿佛在喘息,在叹息,发出一阵阵低沉的空鸣。
这是为什么?我想,阻隔可能是一种假象,一种破坏,一种与生倶来的不甘和不屈。
我生命中难道一定也会出现香山,才会常常在想象中完成智慧的突破和超越。
这是一种力量吗?
是否与亘古矗立的香山一样,在我的外在与内在的心灵世界不间歇的抵抗中,几乎与生倶来,绵绵不绝!
五
香山,夜幕低垂。
它在那个夏夜落在我少年身体上面的时候5像纯白的胚布一样,柔若无物,却充满了许多……像一种温柔,一种默契,整个身心都柔软地安顿在新鲜的草席上,窗外的杨树丫上面有黑黑一团的影子,那是一个八哥的巢,它们睡在叫天空的地方,难怪比我高了。
我只要一翻身,就听见棉布上面发出月光微弱的声响,纯银的皱褶有时候在身体里发出很大的脆响。我很久难以入眠,月光常常从木格的窗户直接涌进来,把我抵到土坯砖墙角,不能动弹。
偶尔传来一阵狗吠,震落了湖边荷叶上无数的露珠,不安地蛙鸣传来,水田的镜子被突然打破,紧紧抱住自己,一条小花蛇半浮在水面上,阴险,柔美,若无其事,而棉花地里的小路迅速消失在湿漉漉的雾气中……
我一直睁大眼睛,虽然看不清周围的一切,在不应该失眠的时候,我失眠了。我为什么在黑暗里辗转反侧?
这是我在香山,在少年时期发生的最大的困惑,甚至是后来所有困惑和焦虑的根源。许多年之后出现的这种心理体验立即让我就想起了香山的夏夜,或者重新回到那个夜晚。
香山,老槐树站着入睡,夜色温驯,鸡犬安宁。
像老祖母一样,颤巍巍的村庄一直没有走远,慈祥的微笑就这样还停留在江边的草滩上。江风吹来,古老的故事和传说亲近,遥远,压不住湖泊边的一点点曙白,掩不住爬上窗顶的黄瓜花那种娇柔带水的焦急。我完全溶化在一种水做的时间里,与我在多少年之后生活的海边连接在一起,没有边界,没有缝隙……我在那样的夜色里长大,在那样的夜色里获得香山给我的永久地安静。
生命中的许多与香山纠缠在一起,不知道是一种幸运还是悲哀?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这种联系的内在根源,我一直在远离香山的日子里,寻找香山。
六
她的背后是一条河。
我从一看见她开始,她就一直坐在土坯草屋的门口,动或不动,就像河里的水。
稻场上总是晾晒着新收下来的棉花,与她黑色对襟的衣裳形成强烈对比。
她与周围,除了沉默一样,其他所有都不一样。使我当时单调贫乏的词汇出现一个词,而我终于不敢确认,不能说出。
偶然她对我招手,塞给我一把花生和蚕豆什么的,我立即跑得老远,放在草地上面端详半天,我没看出有什么不同,但是肯定有什么不同。许多黑蚂蚁在中间爬来爬去,最后静静地在草滩上发呆。
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七岁,那年秋天乘小木船去对岸帮人家收棉花的时候淹死了,当时船上面装了20多个人,全部都是她们那样的年纪,只救起来几个人……
每次经过老人,我低下头默默走过,坐在河埂上,看着不远的她漠然不动,河水也静静流淌。
其实她离河很有一些距离,在我眼里和河总是重叠在一起,缓缓流动的河水变幻成她的影子,这种错觉总是出现在我以后的日子。可能因为她与那条河联系在一起,也就变成与河相关的东西,虽然看不见流动,似乎也没有声音,但是在我心中却形成一股湍急的暗流。那是我不能抵挡的,也无法抗拒。
后来她的儿子娶了我的表妹,也就是我舅舅的二女儿,所以那种暗流变成公开的秘密。
老人露出很少有的笑容使我失去了感觉,我面对她有时候像独自面对这条河。
她还是像以前那样坐在河边,河水混浊,深不见底,是我少年时光就无法进入的暗河。
堤岸,时刻不断地发生崩塌,河水还是那年的河水。
七
香山。巨大的采石场。
香山被劈成一半。阳光轰鸣的细胞四分五裂,到处纷飞,血肉模糊的语言被彻底打碎,被一阵阵炮声瞬间打开。黄昏,我看见漫天飞舞的黄表纸把香山包围着,输送带、翻斗车,把香山迅速运到远处。我感觉到极度痛苦和呻吟之中,空气被无形的手搅动着,昏暗中的香山的脸部在抽搐,在变形。
现在,我发现四处都是碎石片尖锐的反光。在浓重的硫黄刺鼻的味道里行走,仿佛一直走进香山麻木空洞的内部。
大大小小的采石场围绕着山体,仿佛那些贫乏无力的虚词,附着在山腰上面,显得多余和累赘,在月光里慢慢升腾、膨胀和水肿起来。这里,在长江北岸唯一耸立的大山,脚下不远处是一座湖泊,周围再就是平坦无边的棉花地,日夜开采不停的石头彻夜运往外地。
堆积成山的白色石子堆积着晚上的月光,我眼前仿佛出现虚浮,虚幻的巨大的墓碑。我长久地徘徊着,许多的香山从我这里消失了,我再也无法表达什么我想,无法表达也是一种表达。
多少年来,我的香山总是在不能表达的时候突然出现。我久久注视着山下的风景,流淌的江水、榨油坊、湖边的水牛以及山脚下空无一人的废弃的农舍,此刻,全部都在我的沉默和迷失里面慢慢沦陷。
江风缓缓地吹过,我想,香山是不是正在每块石头上喘息,复活?
八
香山的声音在石头里消失,在石头里复活。
轰隆隆开山的炮声、人的嘶喊和号子、钢钎和挖掘机械以及川流不息的运载车辆的声音仿佛都在石头里面响起。
这些不再空洞的象声词,逼迫石头无法保持最后的安宁和沉默。
因为钢钎在炮声的间隙中持久地响起,石头的语言布满香山每个角落,更多的老人和小孩在不远处用手中的小铁锤不停地把碎石砸成一块块的石子片,所以这种声音变得格外单调、机械、持久。
石头在无法忍耐的痛苦沉吟中,完成了自己一次次地麻木地轮回,为什么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常常听到的蛙声都是那么的尖锐,像无数在空气中卷曲的刀片把香山之夜划得血肉模糊。我想,这是一种惯性,如同所有的石头竭力保持寂静一样,语言中的香山在不断适应的惯性里坠落,在另一个自我的深渊里保持新鲜的平衡。
我,还有那么多的人深陷在这个深渊里,把石头搬来搬去,把自己搬来搬去。
而我,注定在另一场永远没有的硝烟里,在香山之外,享受虚无的幸福和宁静时刻。
我也许是街道上一颗遗失的石子,是香山遥远的梦。
九
怀念!
对于我,对于香山,都是一场失语的悼念。
我童年许多夏日的时光,都在这里度过。我后来去过许多名山大川,它们都和香山有着一样令人仰望的高度,威严挺拔。
我知道一样的形状是无法堆砌真实的香山的。在山脚下,在四月的油菜花和八月的棉花地无边的尽头,耸立云天的香山拔地而起。
绵延几公里的香山上,林木茂盛,是一个长满松树和水杉的大林场。很小的时候我从远古时期叫做盛唐湾的地点下水,乘小轮船逆流而上,在华阳港再乘木船渡江,在香山脚下的小渡口上岸。这是一个既定的航程,像定语一样,坚定,无法更改。
虽然还有许多路通向这里,但是从童年开始,我去的路只有这一条。语言的流放地,突然这个词语像石头一样挡在我的面前。
我在走进香山的过程,是一次语言状态的感悟和体验的行走。在香山的周围,滋生了大量陌生的语感,许多陌生的物质,比如各种各样的农具、动物和植物,都迅速在这里找到语言表达最合适的位置。
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穿行在最初的山林里,香山以宽厚、沉默接纳了我,收容了我。
香山,让我在认识这个世界的同时,也接纳了香山,成为它的一部分。
最初的世界在这里打开,还原成为词汇,在骨髓里沉淀下来,终于给了我一个本真世界毫无掩饰的美好、危险和恐惧,而那里生活的人,使是我认识更多人性的本和善良。
后来,我经历了许多的城市和乡村,车站和码头,有时候时间会不经意地突然地转向,感觉时间猛烈地折回,迅速返回到香山。这时有我太公、太婆、外婆和舅舅的墓地,埋葬我亲人的地方,就是心灵永久的净土。
虽然我在不停地行走,仍然感觉走在香山。
但是,真相告诉我,我离香山总是越行越远。我是一个永不休止的行者,背负着石头,终日流浪,疲惫不堪,即使生命僵硬了,那也是山下的一块石头,我经过世上,就是经过破石头,每个里面都有一座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