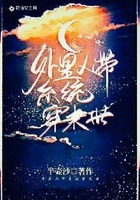缘分是很奇怪的东西,它让人们在不期中相会,让两个本来天南地北的男女相爱。放在人群里,他们也许都很普通,甚至难以在茫茫的人海里,一眼辨认出对方的模样。或者说,他们都太出色。按照他们本身心里的界定,对方是无法打破自己高傲的壁垒。但缘分却让他们鬼使神差地遇见了,甚至相爱了。也许这就是上帝的游戏。当张爱玲看到甫德南?赖雅时,便进入了上帝最新开局的一场游戏。
她并不是还做着公主梦的女孩子了,她也是有过爱人的,有一段过去的女人。曾经的爱人,胡兰成,始终是她心里的一道疤痕。在她离开他之后,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爱交给另外一个人。但在她与赖雅相逢时,忽觉得心里一暖:“这张脸好像写得很好的第一章,使人想看下去。”
她向他走进一步,听他在说什么。原来,他是在讲笑话。她听了几句,也不自觉笑起来。他的目光,恰好在这时候移到了她脸上。他看到的是一个成熟的、眯着眼睛笑的黄种女人。她的身材并不像自己的同胞一样娇小,看起来高挑而又伶仃。她的下巴仰起来,那笑容很快收起来之后,眉眼间有些冷淡的意思。但,那冷淡中,分明还有些别的。或许是掩藏起来的一点温热。
这相视中的默契,带来了第一次交谈。这次的交谈,让张爱玲感到惬意而温和,这个大了她几乎三十岁的男人,是异国的一盏灯。他并不那么明亮,只是暖暖地烧着,有一点让人安心的光芒,昏昏的,显得闲适又安静。
他甚至有些像她的父亲。她记得许多年前,自己还小,母亲还没有与父亲决裂,父亲的阿芙蓉癖也不是那么严重。那时候的父亲,是个温文尔雅的男人。他身上虽然带着些遗少的味道,却并不妨碍他活得优雅而考究。他本来是一个温柔而博学的男人。
她想,若是生命中没有那么多变故,父亲老了以后,也会是这个样子吧?他不应该被生活折磨成一具让她恋慕又恐惧的行尸走肉。他应该是,应该是赖雅这个样子的。幽默,博学,又很温柔。
也许这只是臆想,但与赖雅一起时,张爱玲确凿地感受到了温暖与片刻的安宁。让人厌倦而恐惧的生活,终于留给她一点宽慰。
与赖雅几次交谈之后,她知道他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男人。他写剧本,写小说赚钱,然后将它们统统花掉。旅行,美餐,他不会吝啬,但也不是一个静好而安稳的居家男人。不过,她喜欢他的生活方式,她也急迫地需要一个依靠。
他们就这样一起了。
张爱玲对赖雅的爱,与她对胡兰成的爱不同。对胡兰成,是歇斯底里、不顾一切的爱,如野火一般燃烧过去,不管不顾的决绝。而对赖雅,则是对父亲般的依恋。
然而,命运注定不公,这份如奇迹一般的爱情,没过多久便遭遇了一场危机。原来,文艺营收留作家们的时间,是有限定的。赖雅的最后期限到了,他不得不离开生活安逸的文艺营。
分别在即,但张爱玲对此又能做什么?她的一身中,经历了太多的分离,送走了太多的人。她必须保证自己生活的安稳。
赖雅离开的日子,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张爱玲只能看着这个即将离开她的男人,她那父亲一般的爱人。
实际上,喜欢漂泊的赖雅,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良配:他并没有钱,也不会过日子,他所能提供给张爱玲的,只是心灵上的依靠。即便再标榜自己喜欢物质,张爱玲更加需要的,还是一个能够懂她的男人。
她的经济条件本就很不宽裕,在送走赖雅的时候,她却将自己手中为数不多的钱都给了他。一个看透世情的女人,一个认为花爱人的钱就是幸福标志的女人,在两次恋情里,都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幸福。她够聪明,却不够幸运。
这段如冬日阳光一般的感情,看似就要结束了。但是,在分别之后不久,张爱玲发现自己怀孕了。
一个幼嫩的生命正在她体内孕育,那是她生命的延续。张爱玲对此感到困惑又惶恐。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母亲,她从小就没有体验到真正的母爱,她不知道怎样去做一个母亲,她缺乏母性的温柔与怜悯。
于是,她给赖雅写了信。这个已经六十五岁的“浪子”得知这个情形,终于打算安定下来了。他不再如年轻时一样,有无限的精力去冒险。他老了,这个世界上最尖新的东西,属于年轻人。
于是,他立即给张爱玲写信,向她求婚。在求婚的回信还没有送到张爱玲手中时,她决定,要去找他。
这情形,与多年前是多么相似。那时候,她独身上路,去温州寻找一个叫胡兰成的男人。那时候,她心怀忐忑,他在那边过得怎样?是不是还想着她?但她披星戴月地去到他身边时,发现他已经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这是如同死亡一般沉重的绝望,一颗心脏的枯萎。
多年后,她再次上路,风尘仆仆,千里迢迢,去寻找另一个男人。她想,他会怎样呢?是不是也和当年的那人一样,同别人在一起,她被踢出局,成为一个可笑的失败者?不过,不论如何,她一定要找到他。他是她在这个陌生国度,唯一的依靠。
她到达那座美国北方小镇时,看到了他。在那一瞬间,她心中一紧:他身后,有没有跟着一个女人?
但这个有着慈父模样的爱人,走到她身边。他来迎接的是,是他的新娘,他向她求婚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幸福,在瞬间淹没了她。她不是没有人爱着的女人了。他是她的磐石,她是缠绕在他身上一株藤,开花结果,依靠在他的身上。
但生活永远是这样戏剧化:当她等待着温暖时,意外总是在下一个转角等她。每每当她发现自己收之桑榆,却又被告知失之东隅。她抬起头,想要安稳地过下去,把漫长时光、琐碎生活过成一帖褪色了却又喜庆的旧年画,生活立即给她迎头一棒。她在角落里养伤,好不容易再次鼓起勇气,结果却仍然是头破血流。生活永远是绵长而真实的:即便是王子和公主,结婚之后生活还在继续。
与赖雅结婚后,张爱玲的生活并没有更加容易。生性自由的赖雅,不愿意再负担一个孩子,于是建议张爱玲把胎儿打掉。本就不知如何做母亲的张爱玲同意了。那个代表着她生命延续的孩子,再也不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贫贱夫妻百事哀”,张爱玲与赖雅都只能依靠写作赚一点聊以度日的微薄钱钞。在之后漫长的十一年里,他们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
在这期间,张爱玲的作品产量是很大的。但它们并没有在美国获得成功,这让她灰心丧气。而赖雅年龄毕竟大了,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他摔断了股骨,又几度中风。在他们十一年婚姻的最后两年里,赖雅瘫痪在床,全靠张爱玲照料。
在生活方面一窍不通,甚至需要他人照料的张爱玲,负起了生活的重担。这一次的婚姻,实际上并没有给她带来依靠,反倒是对她生命力与希望的透支。
对于这段婚姻,张爱玲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记录。只有赖雅的日记,一字一句,将这漫长的十一年记录。而这日记的笔调,也从明媚渐渐转为绝望。
这一段婚姻,到底给张爱玲带来了什么?它在她本就伤痕累累的心脏上,添了一条新鲜的伤口。十一年的爱恋与现实的困苦纠缠、折磨,让她在余下的生命里,永远地向旁人关上了通往心灵的门。
她如彼岸花般的遥望
在张爱玲和赖斯婚后的第二年,她的母亲黄逸梵在英国病逝了。
“母亲”是一个柔软的字眼。但凡说起母亲,人们心里便会温柔起来。“母亲”永远代表童年的摇篮,轻柔舒缓的摇篮曲。母亲是爱,是童梦里最美好的微笑。但对于张爱玲而言,“母亲”却是一个让她爱恨交织的人。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出身名门。她的祖父黄翼升是清末的水师提督,父亲黄宗炎是独子,但她的母亲说起来有些让人唏嘘,她是一个买来的农村女人。她有幸留下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上的女人,生得木讷,并不美貌。她坐着,似乎有些紧张,缩着脖子,双手放在腿上。
水师提督的公子,为什么会看上这样的女人?原来,黄宗炎的原配夫人多年无所出,为了延续香火,家里便从长沙乡下买来一个女子做小妾。不过多久,这女子有了身孕,而黄宗炎也前往广西做官。谁知不到一年,黄宗炎便在广西染病去世了。而留在南京家里的姨太太,则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不久后也去世了。而那对龙凤胎中的女孩子,便是黄逸梵。她原本的名字,叫作黄素琼。
出生在这样的人家,黄素琼自幼便接受严格的封建教育。她被要求做一个温顺的官家小姐:要低眉顺眼,背要微微弓着,让自己显得更加没有存在感。当然,缠足也是不可逃脱的。
黄家的所有女人,无一例外的,都裹了足。用明矾、布条,将幼嫩的双足裹起来。五指折断,弯向脚心。剧烈的疼痛折磨着年幼的黄逸梵,但她又是无力反抗这命运的。在那个封建的男权社会里,女人畸形的小脚,让她们无法快速行走,甚至连站立,都是颤巍巍的。这让男人们有了强烈的征服欲,让他们感到,这些女人,是不得不依靠于他们的。
这样的心理,在中国的白蛇传说中直接将脚化为蛇尾,与西方的人鱼传说中脚被化为完全失去行走能力的鱼尾类似。
张爱玲的《对照记》里,有一张黄逸梵少时的照片。背景大概是家里的大厅,有一方木桌子,桌上放着瓷器与西洋钟表,背后则是雕花的木门。照片上的女孩子不过十岁左右,斜坐在一张圈椅上头。她头发团了一个如道人一般的发髻,穿着浅色的衫裤,都滚了边,领口绣了一溜的花,很是精致。她手上握了一柄团扇,大抵画着竹子,一丛丛墨竹在扇面上铺开。她身后,则站着一个年纪与她相仿的少女,手中也握着团扇。这应当是她的侍女。
令人感到一阵不忍的是,两个女孩子裤脚下面,都露着裹过了的小脚。黄逸梵穿着一双绣鞋,斜面上密密匝匝地绣着花。那鞋子尖尖的,短短的,几乎不到一掌长。这是一双让她终生感到羞耻的脚,是男权社会发展演变出的畸形产物。
这个女孩子是聪明的。虽然,她心里有无数反抗的呐喊,但她在家里保持沉默,作出乖顺的表象。也许她想,等到自己长大了,总有一天,能够过上自由的生活。
童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当年的女童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又长成美貌的青年女子。她并没有遗传到生母的平庸,反倒拥有令人讶异的美貌。
当然,即便成年了,她也是没有自由的。她被迫嫁给了遗少张廷重。这个男人初看时,还是好的,温文尔雅,又有学识。但他身上带着她讨厌的陈腐的味道,让她感到窒息。
有人说,嫁到夫家,最难处的是婆媳关系与姑嫂关系。对于黄逸梵来说,却并非如此。婆婆早就去世了,小姑张茂渊,却和她非常投契。张茂渊是个活泼而有见地的女子,她的生长环境,也比黄逸梵要自由许多,这让黄逸梵非常羡慕。她尤其羡慕的是,张茂渊能够去学校里读书。
张爱玲后来回忆自己母亲时,这样说:“她是个学校迷。我看茅盾的小说《虹》中三个成年的女性入学读书就想起她,不过在她纯是梦想与羡慕别人。后来在欧洲进美术学校,太自由散漫不算。一九四八年她在马来亚侨校教过半年书,都很过瘾。”(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对黄逸梵来说,也许她并不是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求知欲,她只是想走到外面的世界去,想要自由。家庭是温暖的,是一个保护巢,但她厌倦了家里如一团死水一般的生活,她想要行走,想要去看这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世界。
她一直在酝酿,直到生了两个孩子——张爱玲与张子静,她还是没有放弃。许多希望外出闯荡的女人,在有了孩子之后,都会静下心来,将自己整个投入家庭当中。但向往自由的黄逸梵却并没有这样。她如同一阵风,一阵无情的风。对于自己的孩子,她没有太深的感情,她自我,她最急迫的事情,就是去呼吸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
在张爱玲的记忆里,母亲总是郁郁寡欢的:“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家庭生活不是她的全部,她属于更广阔的世界。
很快,机会就来了。小姑张茂渊要外出留学,这让黄逸梵也一起激动起来。她不想自己的年华在幽深寂静的院落里腐坏,她要跟着张茂渊一起走。这样的想法,在那个年代毫无疑问是惊世骇俗的。但黄逸梵坚持着,她也有自己的借口:小姑外出留学,她要做她的监护人,照顾她。
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让一个坚定的女人放弃她的理想。黄逸梵就这样把她的家庭远远地抛在身后了。迎接她的,是一个全新的、未知的世界。黄逸梵的人生之门,这才算刚刚开启。
在国外,她看到了这个世界有多大。她学习油画,参加各种新式的活动。很快,她就成为一个新派的人。
当她和张茂渊再次回国时,曾经那个身上还能看到些传统闺秀气质的黄素琼,已经被一个完全西化的黄逸梵所代替。在《对照记》里,存着好多张黄逸梵的照片。真是极美的一个女子,烫着卷发,穿西式的连衣裙与高跟鞋。她的五官长得非常精致而深邃,竟有些欧洲人的意思。在照片上,她带着似有若无的笑容,双眼熠熠地看着镜头,如同一个派对上的女王。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张在海船上的照片。黄逸梵站在甲板边缘的栏杆前,侧着身子。她裹着头巾,头发在颈后绾起来。她穿着无袖束腰的连衣裙,逆光让她的身形成一个美好的剪影。
回到国内的黄逸梵,不愿自己的女儿也成为一个温顺的闺秀,便坚持要带她去学校,并且教她钢琴与绘画。她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但她的一举一动,都让张爱玲非常羡慕。这样一个如同“女神”一般的母亲啊……
见识到世界广大的黄逸梵,当然是不愿意再与抽鸦片、下堂子、娶姨太太的张廷重一起生活了。她果断地和丈夫离了婚,并和小姑张茂渊一起搬了出去。这小姑子张茂渊也非常看不惯哥哥的生活习惯。
两个留过洋的女人,租了一所漂亮的房子,请了白俄的厨师与司机,过着小资的生活。受到继母与父亲虐待的张爱玲一度与母亲居住在一起,母亲的冷漠与高姿态,西式的“自由”与无情,都让张爱玲又爱又恨。
当然,对于黄逸梵来说,安定不是她的本性。自由的风,只会在某个地方暂驻,而不会永远停留。不久之后,她又出国了。
与多年前那个和小姑一起第一次来到国外,对一切都感到无比生疏而惊讶的女子相比,这一次的黄逸梵,是一个熟门熟路的旅行者,是一个生命的书写者。她的旅行经历,简直可以用传奇来形容。她去过许多国家,多年后,女儿张爱玲继承了她惯用的行李箱。那箱子上满满地贴着各国轮船的标签,这是一个旅行者得到的徽章。
在张爱玲的记录中,黄逸梵在国外的生活,时刻都充满了趣味,当然也免不了危险。张爱玲在她的文字中记录道:
“她画油画,跟徐悲鸿、蒋碧薇、常书鸿都熟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