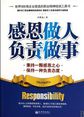赵德峰埋的地方,自然是家里的祖坟。青年男子在外暴毙,比未出嫁的女子要好很多,至少尸骨可以被埋在家中坟地。但是死者为大,即便他年纪小,葬了之后,别人若要开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看赵姑父如今脸色黑的锅底一样,就知道,他是不晓得赵德峰被开棺的事情的。
“赵官人休要生气。若不是如此,怎么能叫你儿子沉冤得雪?”吴处厚洋洋自得,对赵姑父完全不放在眼里。当年这老头是做过大官儿,也曾穿过紫衣裳,甚至比眼前这姓杨的还要有几分威势。可是他家世已经完全败落了,落毛凤凰不如鸡,早些年的传言,他吴处厚刚入官场的时候,也听过一两分,如今不踩他个满脸花,而且还帮他儿子申诉冤情,不感激反倒摆脸子,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
瞧着赵姑父眼看要冲上前去,几个有眼力劲儿的衙役立刻上前,水火棍一举,架在赵德峰脖子上,生生将他压的趴伏在地。江嵋清晰的听到,赵姑父骨头磕着地,发出咚的一声大响。
等赵姑父再抬起头,额上已经因为挣扎,蹭出一长道血痕,头发也散落开来,露出里面花白的部分。更重要的是,江嵋看到他脸上,两行长泪,从浑浊的眼睛里流出来,瞧着落魄极了。
杨渔之踏步上前,怒斥出声:“吴大人,还不叫这些官差放手!你刨人祖坟,错在前面,不自认错处,赔礼道歉,尔敢不敬长者,做出这样的事体。”
那陈官人也是满脸的悲呛,直觉得自己命不久矣,却不再管这件事,只是摇头。
吴处厚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摆摆手,叫人放开赵姑父。赵姑父被杨渔之扶起来,半天说不出话。
“来人呐,把那仵作叫来。”吴处厚说完,又招手对那亲随附耳两句,亲随点点头,才走出去。下面几人都觉得其中有猫腻,可是却不晓得是什么。
过一会儿,进来一名仵作,先对吴处厚行过礼,才得了他吩咐,朗声道:“当初的罪人赵德峰,不是自己个儿死的,亦不是什么暴病身亡,他生前中了毒,尸骨里头能验出来的。”
“中毒?”江嵋忍不住小声呢喃。本来她搀扶着的杨纪,身子却渐渐的停止了颤抖,很自然的站直身子,变的一切如常。
江嵋想到的,是当初孙潮安告诉自己,为了不让卿娘拉她下牢,所以才给赵德峰喝了毒酒,叫他神思恍惚,自个儿说出真相。难道那仵作查出来的就是这毒?
而自己这公公,怎么听到了中毒后,身子也不抖了,难道是自己看错了,这老人心中并没有什么不妥,刚才只是因为年纪大了,或者因为炸逢赵姑父,心思动荡,所以身子没受住。
赵姑父却像没听到般,若非杨渔之搀扶着他,他已经要瘫软在地。他目光痴痴盯着眼前地砖,嘴里小声叫着:“我儿!我儿!你年纪轻轻,叫为父白发人送黑发人,死后也不得安宁。你若是有魂,给吵得不得投胎转世,叫我这做父亲的,可怎么办。”
吴处厚看堂下没人理自己,有些尴尬,道:“底下的杨氏一家,还不肯伏法认罪,如今人证物证全有。”
杨渔之扶着赵姑父,杨纪则一语不发。吴处厚更加得意,摸摸颌下短短的胡须,哈哈笑着:“既然你们认罪,我便叫人写下罪状,自个儿签字画押吧。”
江嵋忍不住,挺身出来:“你这昏官,我们有什么罪。你眼见得谁给我家里表弟下毒?而且那毒是什么毒,你们可知道?就这般的妄断。那边的仵作,你可说出来,那是什么毒啊?”
仵作愣了愣,没开口说话。吴处厚摆手:“刁妇,莫废话。你一个女子,三番五次咆哮公堂,若不是念顾你是妇人,早就打的你皮开肉绽,不想吃苦头,就站在后面老老实实,别再废话。”
正说着,吴处厚往门外远处瞧过去,见远远的来了个人,瞧着是赵佶模样,心里就犯了嘀咕,这祖宗难道又要上堂不成?
几步路远,不过几息功夫,赵佶就走进来,穿着一身暗色的精干衣裳,瞧瞧堂上,淡淡说道:“吴大人,你先在此地,我要回京一趟。”
吴处厚急忙跑下来,也不顾正在审案,对着赵佶就是一个大礼:“您这是?”
“我来有自个儿的事儿,如今有了点头绪,要 回去查证一番。”赵佶英气勃勃,看都不看吴处厚,却瞧了瞧江嵋,眉目间似乎有些话想对江嵋说。
吴处厚心里鬼精,赶紧笑道:“那下官一定得给您辞行。”转身对着堂上一挥手:“先退堂。”竟然是把审案当做儿戏一样。
赵佶瞧瞧吴处厚:“你倒是有几分心思。”吴处厚听了夸奖,高兴的什么一样,这位赵十一,可比他那位皇帝哥哥更得高太皇太后的喜欢,到时候美言几句,可有的他好处。
吴处厚刚要再奉承几句,说几句是下官本分之类,赵佶就开了口:“你在这儿等着,还是和我一起回去?”
“回去?”吴处厚有些糊涂,指指自己 鼻子:“小底还得审案,哪儿能回去。”
“这案子,不要审了,按着当初报上去的来。不要惹得皇兄和祖母厌弃。”赵佶一开口,就是拿皇帝和太皇太后的帽子压人。
吴处厚暗地里叫苦,他为了这案子,连自己高升的官儿都不顾,挂印跑进京城自荐,这会儿回去,再轮到下次任命,这么久时间,等着吃灰么。那边那位皇后的师姊,一个多月都不管不问这案子,他还以为是出家人清高,想不到刚再上堂,居然就找到了赵佶?不应该啊。
他来的时候也渐多,听说了杨家的事情,这位杨家的姑娘,是不守闺誉惯了的。以前便常常上街游耍,抛头露脸,后来更是听说闹出来什么关系清白的大事儿,被送到山上道观住了好久。婚礼上又死了丈夫,拜堂的是另外的男子,如今父亲兄长被抓,反倒在家大兴土木,盖起来新房子。
吴处厚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中间是怎么回事。可是赵佶已经命令下来,他又不能不办。若是他能拿出来硬骨头,跟赵佶扛着,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吴处厚哪儿是这种人。
但是若叫他回京,怎么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