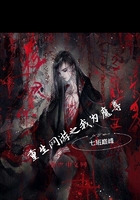随后,继续恢复死寂。
这是每日地牢里最有生气的时刻,隔壁牢房的所有犯人都会被这个叶都尉钦点,狱卒送最后一顿饭的时辰才被送回来,送回来的时候,有些人在哭喊,有些人在叫骂,然后是鞭子抽在身上的“啪啪”响和哀叫声。
骂了几日,便没声了,回来的脚步声却越来越少,越来越轻。
连胤轩给映雪的牢房是个独立小间,与其他牢房隔了厚厚的墙壁,木柱子前则是一条走廊和一堵墙,似是有意隔开。
映雪静静坐在属于自己的小角落,双臂抱着双膝,将下巴搁在膝盖上。门外的声音她已经听腻了,眼皮半天都不眨一下,一直保持这个姿势瞧着暗夜里觅食的老鼠。
那模样,更似个木娃娃,看是看,眸里却没有神采。
而距离那日,连胤轩又将她关了三日,这三****天天派人来地牢逼她喝水吃东西,却从此不再在食物里下毒。
其实不需要人逼迫,她也会吃,有没有毒她都无所谓,因为对她来说,这段日子就是行尸走肉,死了,是她逃不出他的手掌心。活着,会时时刻刻忍受痛苦煎熬。所以她不想动,不想说话,不想去想任何东西,只想这样静静的抱着自己。
这几日,她陡然开始喜欢上这样的黑暗,喜欢这样的宁静,暗夜里,一个人,感觉不到任何东西的存在,甚至感觉不到自己。
她需要这样的感觉。
“呵!”有人在暗夜里轻笑,无声无息闯入了她的世界,“你倒是喜欢上这样的日子了,这肥肥黑黑的老鼠真的有这么好看吗?”
话音落,一个墨色身影瞬息飘落在牢门前,比墨更浓的黑,金色护腕,手拿长鞭,脸上戴青狼银钩面具,露出闪亮的眼睛和薄厚适中的唇。
这个暗夜使者披散着墨发,着墨色披风,一身墨黑透着暗夜的幽深神秘,他在笑,但她相信他绝对是心狠手辣的。
她坐在角落里对他的出现并不惊奇,没有动,没有恼:“你的伤,可是好了?”一出声,声音竟是嘶哑的。
“什么伤?”他微微思索,很认真的跟她交谈,“噢,你是说月圆之****发病的日子,这个不怕告知你,十六那****只需喝生血便能解我体内的狼滴子,月缺或无月,我都没问题。当然了,也要靠你将我的藏身之地保密才算没事。”
他又撩撩木栅门上的粗大铁链子锁,道:“需要我帮你拧开它吗?”
“不必。”映雪轻轻摇头,制止他:“我喜欢呆在这里,这里很好。”
“既然你说不必,我也不多此一举。”他十分爽快,安静将手放下,望着牢房里:“你的竹清院最近不太安静,每日卯时一刻便有人来院子里叽叽喳喳,一大堆大小丫鬟拿着筒子采什么露珠,吵人清闲,你可管管?”
“你觉得我现在有本事去管吗?”映雪朝他扯出一抹淡淡的笑痕,言不由衷:“我没有本事管他府上的事,也不想管,你还是另寻他处吧。”
“好,那就不换了,我习惯这里。”他也不难为她,银钩面具随着他走近的动作在天窗透进来的月光下闪着一层薄光,那低沉的声音再次不冷不热传来:“其实我在卞州呆不了多长时间,等身上的伤养好便回淮州,绝不再打扰你。今日来此,是想向你赔个不是。”
“为何?我们并没有交集。”映雪眉头轻抬。
“我们是没交集,但我银面也绝不能做个忘恩负义之人,那日劫持淮州兵器库兵器之人其实是我,却让你爹爹代为受罪……”
“爹爹他不会做这种事。”她的声音很轻,却在暗夜里将自己缩得更紧。
银面望进那片黑暗里,一身墨色比起这暗黑更显肃穆神秘,沉声道:“这两个被鞭尸的人,据说是在逃跑途中自杀,有没有偷兵器无从可知。但我倒是知道宇文祁都的手段,被他捏在掌心的人,是绝对捡不回一条命的。枉你有飞天之术,只要他想要你死,你绝对见不到明日的太阳。”
“那你帮我救回他们的尸首。”映雪终于有了回应,撑起酸软的腿从黑暗里走出来,只见得一张精致凝白的脸蛋,已惨白如纸颧骨高耸,她在月光下瞧着那个银面男子,干涸的大眼里有丝乞求的波澜,“救下他们,帮我安葬。”
“救不回来了。”银面微微心软,盯着她,眸光在面具下流淌:“他们的尸首在城墙上暴晒了三日,已被扔入西魉河沉尸。现在,宇文祁都正以长公主金步摇的事寻景亲王府麻烦,一口咬定那日晚宴上的刺客是长公主,呵呵,这老家伙能不能搬走这块绊脚石,银面还真想知晓呢。”
“沉尸了。”映雪将他后面的话并未听进去,只是用指紧紧抓住柱子,静静望着银面身后那个高高的天窗,“是我害的。”
银面一愣,止住了话头,望见牢里的女子微微仰着头,盈盈水眸里闪烁一种绝望,她及腰长发披泻,没有挽云鬓,一袭白色单衣,单单薄薄裹在她瘦削的身子骨上,那副身子骨却又透着坚强。
他知道她在无声哭泣,将泪珠子偷偷藏在了心里,流不出泪来。遂破天荒管起闲事来:“银面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映雪身子一颤,将凝视月牙的目光收回来,凝泪瞧着他:“帮我救两个人。”
东漓右偏居一直在闹,小孩童的哭叫声几乎掀开绛霜的屋顶。她正在逗弄温祺送给她的那只鸟雀,练习轻吟浅唱,却时不时被外屋的哭叫声打乱。终是恼了,掀开帘子走出去。
“千蓉,你怎么照看的?怎么老是让他哭?”
千蓉正一手端着果子,另一手拿颗葡萄,半蹲在沥安面前哄他,被主子这样一恼,连忙站起身来:“小姐,他在哭着要芷玉,不肯吃东西。”
“那芷玉人呢?”她柳眉一挑,不悦的搜寻屋子的每个角落。
“小姐,芷玉一大早让小王爷叫去了,现在还未回。”
“快去把她找回来,以后有人叫,要先知会我,知道吗?”绛霜瞧瞧那满脸鼻涕泪水的六岁小孩童一眼,吩咐旁边的大丫鬟:“带他出去走走吧,半柱香时间内一定要回来。”
“是的,小姐。”千蓉出去叫芷玉了,紫烟牵着沥安的手走出去。
她们甫出去,有丫鬟来报说亚父来了,等在花厅里。
绛霜细眉一蹙,冷道:“亚父不去前殿见丞相大人,跑我这里做什么?”
“奴婢不知道,亚父只说要见小姐您,说是有事。”
“那好,先备茶水,我马上到。”
“是的,小姐。”
半刻,她握着圆扇轻移莲步走到了花厅,向老者盈了盈身:“亚父。”
亚父连忙从椅子上站起身,揖手道:“老夫今日来是想跟三小姐谈谈小公子的事,小公子年岁过小,爱哭闹,老夫是想将小公子交由府里的奶娘照看几日,以免打扰王爷和三小姐清眠。”
“呵呵,亚父多虑了,小公子在绛霜这里过的很好,根本不会打扰到王爷。”绛霜微微一笑,恭恭敬敬请亚父入座,让丫鬟备了茶水,再道:“再说有芷玉照顾着,亚父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屋子里的十个丫头也比不过芷玉,只要有那丫头在,亚父尽可放心。来,亚父请喝茶。”
亚父眼露忧色,端起瓷杯啜了口清茶,又问道:“王爷来看过小公子吗?”
“看过几次。”绛霜用圆扇轻轻扇着风,随意说着,又问道:“那丞相大人来王府是为何事?绛霜听说丞相大人拾了青楚姐姐的金步摇,这次是来特意送到府上,可是真的?绛霜还以为是为姐姐的事而来。”
亚父捋着胡子笑道:“三小姐从来都是如此聪慧,府里的事皆能知个一二,呵呵,丞相大人这次确实是为金步摇的事来,不过那支金步摇并不是长公主的,长公主正在陪宇文丞相确认。”
“噢,是吗?那就好。”绛霜莞而一笑,随即宽了宽心,笑靥如花:“今日亚父既然来了,那绛霜就请亚父顺便帮忙算算与王爷的姻缘可好?绛霜听说姐姐也常找亚父掐算,准得很,所以亚父可不能偏心。”
亚父眸光微闪,瞧着这个娇俏的女子:“三小姐与王爷早已是缘定今生,天作之合,又何须老夫赘言。”
“亚父此言差矣。”绛霜停下扇香风的动作,眉儿挑了挑:“谁都知晓这世事变幻莫测,诡异多端,又有道是‘天为棋盘星为子,地为琵琶路为弦’,无人敢认定这一时就是一世。不瞒亚父,自从姐姐过门,绛霜这心里头就不塌实,总感觉会有什么大事发生……”
“既然‘天为棋盘星为子,地为琵琶路为弦’,那老夫更不敢卤莽断言了,呵呵。”
绛霜瞧亚父一眼,也不恼,道:“女子处事,以德为首,不曾想姐姐竟做了毒害王爷的事,妹妹为她感到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