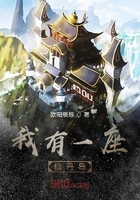是金沙江翻滚的浪涛把他的心卷走了么?他伫立桥栏,面向下游,专注莽莽然奔泻直下的江水,整整过去一个小时了。神情凝重而虔诚,偶尔,脸上泛起一个深深的笑意。特别是当视线落到湍流的旋涡上时,他会强烈地感到流水那活跃的生命:旋涡是流水的笑靥,呼啸是流水的絮语。他自作多情地认为,流水是特意唱着欢歌,迎接重返故乡的游子!是呵,一去二十二年了。人生能有几个二十二?刚下火车就奔金沙江而来,打算溯江而上,踏着童年的脚印,从坐落金沙江边的母校后门,翻石龙庵的龙背,过上中坝的沙滩,到铺满卵石的下中坝……可惜,洪水淹没了整个上下中坝,水溢母校后门的门槛,石龙的龙背也全无了踪影。于是,他只得绕道而行,到这座不知新近哪年修的金沙江桥上来了。桥中央是铁路;人行道上人们行色匆匆;各式车辆徐徐流过慢车道,喇叭喧声大作。而他,真是“心远地自偏”哪,竟身在桥上却不见桥影!桥于他是陌生的、冷淡的,隔膜得使人惆怅的。而这金沙江水却是熟悉的、多情的、甜蜜中带着苦涩的。跋涉过无数的高山峻岭、丛莽激流,从没有哪儿像金沙江水这么令人销魂!勾起多少金色的往事,引出多少美好的形象!不过,他总是小心翼翼地筛选着记忆,谨慎地逃避着,别越过记忆深处那紧紧封锁着的小门。他怕,怕触到那扇小门里面的她……此刻,思绪飞到了离别故乡的时候:他没能考上梦寐以求的“清华”,分配到贵州的一所跃进大学,学了水电。几个同学为他送行,大家谈笑风生,根本不懂得依依惜别。可是,当火车启动的刹那间,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电影般硬切进一组镜头:
金沙江岸。
蓝天明净,骄阳高悬。
沙滩灼灼泛白,潋滟江波金红闪烁。
……
四个孩子背着水壶、干粮、赤着脚(鞋提在手上)一跳一跨,坚定地行进着。这是他和她跟着大哥、二姐去下中坝,捡令人神往的琥珀!
从此,这组镜头随着他走南闯北,在那些清醒的旅途,睡梦的长夜,欢乐的瞬间……
现在,这组镜头从水中冉冉升起,使他一下越过二三十年的光阴,故地重游一番。一种令人窒息的幸福涌上心头,他冲动地举起双手,紧紧扪着胸口,那有节奏的怦怦的跳跃,是心灵欢乐的呼喊:捡琥珀,捡琥珀哟!多么令人心醉!他神思奋飞,情不自禁地挥动两手,仿佛要抓住时间,让它倒转,转到童年那支前进着的队伍那会儿,只要在那儿停留一分钟,不,一秒钟也行,一秒就足够了。
江边上长大的孩子,哪一个不是沙里滚,水里泡的?小时候的打闹、嬉笑、恶作剧,一幕幕全展现在他的眼前:
把湿河沙捏成团,照对方头上扔。打得双方满头、满身是沙,连耳朵心也灌满了沙,眼睛都睁不开了,沙包蛋就打得最安逸了。而这时候,她会一屁股坐到沙滩上,假装喘着气说:“我走不动了,站不起来了。”这是耍赖,赖他背她回家哩。
在沙滩上挖个坑,捡几枝黄桷树丫搭上,覆盖些树叶,再用河沙把坑隐蔽起来,人躲得远远的。等一个洗衣的大姐或淘菜的婶婶一脚踩进“机关”,把菜或衣服撒了一地,咒骂着不得不重新去淘洗的时候,她会躲在他背后,吓得扯着他的衣服,胆怯地催促:“快逃吧,快逃吧!”这胆小鬼,也不怕扫了大家的兴。
然而,最惬意的是到下中坝去捡石头!那不是一般的石头,是透明得像宝石般的化石,有红的、白的、透明发青的、起一层层云花的。不过,自从大哥给二姐、他和她讲了琥珀的故事,他们就不捡化石了。琥珀使他们魂牵梦萦,至今还记忆犹新。
故事说,好多万年以前,一个晴朗的早晨,大森林里的大松树上,一只红蜘蛛在精心织网。它老了,觉得很寂寞,想起自己的同类,引起无限的忧思:它们织网,利用网捕食昆虫,使大家都怨恨地躲开它们,它们只得孤独地守着网,没有一个相亲相爱的朋友。红蜘蛛决心从自己开始,织一张不伤害生灵的网,让飞累的小蛾们栖息,创造一个友爱的奇迹。刚巧,一只绿飞蛾撞到红蜘蛛的大网上了,倒霉的绿飞蛾!它挣扎着想摆脱困境,却连整个身体都给粘住了。红蜘蛛诉说着自己美好的心愿,并想帮助绿飞蛾。刚一动,绿飞蛾就粗鲁地骂开了。也难怪,它从祖奶奶那儿就知道布下天罗地网坐吃现成的蜘蛛,哪相信有悔过的蜘蛛?等红蜘蛛一靠近,扭住便打,结果,一个断了腿,一个折了翅膀。见它俩如此野蛮,松树忍不住掉下眼泪来,眼泪是松脂,刚好滴到它们身上,将它们紧紧裹住。好多万年过去了,松脂变成了琥珀,透明中,红蜘蛛和绿飞蛾清晰可辨。
多么多么想捡到那样的琥珀呀!并不在于它是形象的历史,孩提的心只能容纳故事本身……于是,四个孩子摒弃一切娱乐,凡是节假日都向下中坝挺进。她年纪最小,连跑带跳的,小嘴唧唧喳喳地总问个不停。一会儿,摇着头问:
“当真有那样的琥珀呀?红蜘蛛不吃绿飞蛾了,会不会饿死呢?”
一会儿踩进水里,浇着水问,“这水流到哪儿去呢?它流走了就没有了吗?”
每逢过石龙庵,庵里的大黄狗龇牙咧嘴,远远朝他们狂吠,她就战战兢兢地问:“狗为什么要咬人呢?人会不会咬呢?”等大黄狗跳出大门,气势汹汹跑上石级,她吓得揪住他衣服的后摆,哇哇哀求:“回家吧,我不要琥珀了!”这时,大哥和二姐气呼呼掉开脸,甩开大步直往前走,不再答理她。他呢,尽管吓得心都提到喉咙上了,当着她的面,却硬把胸脯挺得高高的,得拿出男子汉的气概呀!从地上胡乱抓起一把沙(顾不及找石头了),嘴里命令她:“别跑,一步一步走!”那强装勇敢的声音哟,格外悲壮。每次过了险关,她总要感激地喊一声:“小三哥!”满脸放着光彩,无限崇拜地说:“你真正勇敢呀!”
“小三哥,你真勇敢呀!”那纯真而稚气的呼喊,从遥远的过去飘进耳里,他通身透过低频电般颤巍巍的快乐,而心尖尖却感到了焦灼的痛!他怕触到她,竭力逃避着想到她。可是,偏偏总要记起她,每一个甜蜜的回忆,都夹杂着痛苦唤起她……时间像金沙江边这些松散、永恒的河沙,埋藏了美好的童年,然而往昔的意象却屹立在时间的沙土之上了。他苦笑着拍拍秃顶的脑门,该进城去看看了。
县城变化不大,中心区街道依旧,只有那路面的石板被代之以乌黑的柏油;昔日的老屋毗连,高耸的药房“同仁堂”还在,可远没当年的气派了。也许是他见多识广了,连当年县城最洋气的“前盐银行”大门也变得小器了,这儿原有的县城唯一的水门汀阶沿,是孩子们“开汽车”的大马路:她半蹲着,他和二姐各拉着她一只手,叫着“嘀嘀”,往前猛跑,她的脚“哗”地在水门汀上滑行,“汽车”便开驶了。那时,县城只有一辆美式吉普摇晃着跑过,她立志长大了要去造汽车,专门给县里的人造五颜六色的汽车。可惜,她连高中都没毕业。
他心里直泛苦……拥挤的人群像潮水一涌一涌地流过去,夹在人的缝隙中几乎透不过气来;踮起脚尖,也只能看见人们的脸。唉,自己又干瘪又矮小,四十多岁了,毫无引人注意之处。但,当年他可是小县城里的风云人物,是两百米跨栏的省纪录创造者。有线广播站两次三番报道过他,唯一那家照相馆还挂过他的大相片。一去二十二年,真可谓乡音无改鬓毛衰了。
时髦的大姑娘小伙子手挽手,旁若无人地和着录音机响着的音乐节奏,扭摆着走路。年轻人叫什么科?迪斯科?对,迪斯科!他宽容地笑笑,这些娃娃呀,说不定刚参加工作呢,就知道抓住“生活”,尽情享乐了!究竟生活于他们是什么?腻人的卿卿我我、标新立异的打扮、扭屁股的迪斯科?人心不古呀,当年的青年可没这么开化。
他和她同班,父母又是同事,所以上学和放学总走在一路。班上的淘气鬼讨厌极了,朝他们扮鬼脸,从背后扔石子;最气人的是把他和她的名字连在一起乱吼。有一天,他逮着一个乱吼的娃娃打,打得人家鼻血长流,害得爸爸亲自去赔礼道歉,还付了医药费。那以后,没人敢乱吼了,可他和她也再不敢说话了,像隔了一堵神秘的墙似的。高中,他们还是同班。有什么办法呢?小县城就那么两所中学,连同班同学好些都是原来的。现在想起来都好笑,皮没长抻,人没长醒,就知道授受不亲了。他和她只说过一句话,真的。那是高一上期,语文老师讲评作文的时候,念了她题为《琥珀》的作文。她描写了琥珀的故事,详细刻画了四个孩子捡琥珀的执著。全班为之惊叹,他突然发现她是块当作家的材料。下课时,他忍不住故意从她课桌前走过,眼望前方,目不斜视地说:“如果题目是《寻觅》,才能升华主题。”
“不,我仅仅向往,”她的头转向窗外,看着新栽的桉树的树梢,毫不掩饰她过分实际的性格弱点,坦白地说,“不是寻觅!”
寻觅!应该寻觅!至今他也说不清琥珀何以能如此深刻地烙在心里,可是寻觅的潜在意识却始终主宰着他的生活。记得在那个秋风萧瑟的夜晚,一伙“革命”暴徒袭击了他们的住地,用汽车把队里的人统统拖到另一个村子“修工事”,不料遭到另一派“革命者”伏击,队里的人趁机逃走了,好些人甚至逃回城里与家人团聚去了。他却一一跛连夜走了七十多里路,赶回住地收拾自己办公桌上没来得及收的资料、图纸……这,一桩小事!他干的尽是这类小事,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也没有奋勇的搏击。是的,在人生跑道上跨栏,他没能创造出惊人的纪录,他只是执著地追求着要把现代文明输送到绵亘古老的山区。当那些低矮的茅屋闪着白金般的亮光的时候,列宁那句“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的名言,就会像故乡的金沙江水一样,从他心里汩汩流过,而这,正是他所寻觅的……不过,不管承认与否,他都无法抗拒,心灵深处那团忽明忽暗的阴影……如果有人问他,特意绕道八百公里(父母早已调离)重返故乡究竟为什么?他该如何回答呢?是对故乡的依恋,因为这儿有他生命的一部分?是迷恋下中坝的琥珀,想找回儿时那热烈而虔诚的梦?不,不完全是……
他怎么老在这个面摊前徘徊?呵,摊子后面是她过去的家!他们“打游击”、“躲猫猫”就在这里!而今,闭上眼睛也能在院子里横冲直撞,能准确地说出进门右边横竖第十七块砖上,有条裂缝,可插进十二根香水香;横竖第二十一块砖是活“机关”,可以藏三本书进去;男厕所左门坊上刻了个乌龟,乌龟尾巴底下刻了个椭圆的蛋,蛋上刻着经常打她的狗娃的名字……她还住这儿不?望着小院的门,他心中紧张起来,要是她刚好从里面走出来——不,他已多次下了决心不找她,与其说没有必要找,不如说不好意思、不敢找……就远远地看看她,只要她安然无恙就放心了。是的,汹涌的浪涛已经把旋涡旋卷过去了。但既然见到了,为什么不说说话?懊悔像一条睡醒的毒蛇,时刻在撕咬着自己的良心,难道不应该亲口对她说“过去的过错已经完成了对我的教育”么?说?说了就轻松了?笑话!他绝不是来寻求自己良心安宁的浅薄之徒!
一个老太婆端着挂面,却用眼睛盯着他看。他无法摆脱此刻对小院的眷恋,下意识地替自己找了个借口:想吃什么哩,并立刻感到饥肠辘辘。
“吃点什么呢?”温柔得略带献媚的声音,像猜透了他的心思,“有醪糟蛋、挂面。”
故乡的醪糟是以醇甜醉人闻名的。他要了碗醪糟蛋,坐下继续想心事。大卫的戒指上刻着“任何事都会过去的”,但,自己怎么恰恰相反,任何事都不会过去?是因为正义与上天同在么……那是个狂热的年代,人心像火,大地在燃烧。他们班守候三个土高炉,把炒菜锅、锅铲、铜锁、铜门环投进炉子,铸上一砣砣的钢,为一千零八十万吨指标添分子加原子。他们豪情满怀,不回家,站着睡觉!究竟炼了多少钢?班主任老师瞪圆眼睛,望着天大声说:“估计,大家估计!”数字越估越大,仿佛那一座座火焰山在熔化钢铁的同时,把舌头、脑子也一齐熔化了。
“哟,挂面里有虫!”老太婆没牙,说话不关风,把虫字念成“穷”了。
“五角。”一碗醪糟蛋重重地放到他面前的桌上,“什么虫?我看你是老眼昏花了!”温柔的声音吐出的却是恶言。
“你眼尖,自己来看。”老太婆没发火。
他好奇地侧目而视,见老板娘把头伸近碗,手指从碗里捡起什么,指头一捏一搓:“是块渣渣。婆婆快尝尝,差什么味,我给你加……”
“我不吃了,退钱吧。”
“退钱?亏你说得出口哟!没几十斤也有几十岁嘛,两角钱就把眼睛打瞎了呀!”
他厌恶这种市井叫骂,低头快吃着,再也没有了回首往事的情绪。
“醪糟蛋五角一碗,先付钱呵!”
他急忙放下匙子,掏钱递过去,刚好与老板娘视线相碰——两人立刻惊呆了,天!
她?他惊悸地辨认着;他?她意外地审视着。
二十多年了,成了路人!
“难道——”他犹豫着不敢、不愿相信。
“是你!”她终于认出了他。最初的惊愕过去了,望一眼手里捏的五角钱,迟疑一下又递过来,“是你就不能收啰,算我请客吧。”
他仓皇地站起身,怕烫似的推回她握钱的手:“不,不,你也不容易——”
“一碗醪糟蛋还是蚀得起的。”她把钱放到桌上,“虽说是小本生意。”接着,像对常见面的熟人,三句话不离本行地抱怨物价上涨,生意艰难,再不看桌上那张五角一眼。
这意外的相见使他狼狈不堪。尴尬地瞟着桌上的五角钱,他突然明白,她只不过客套地“请请”他,再听她那种说不出有种什么滋味的言语,他心里骤然冒起一种羞愧、悲凉的情绪。
“哎,究竟多少年不见了?”她是善于察言观色的,这是为他而扭过来的话题。
“二十三年半。”他机械地回答。
“真精确!算算看,还是大跃进那一年——”“那一年”三个字在她喉咙里咕哝一声,冒个泡似的又滚进肚里去了。她静静地坐下,陷入沉思。沉思的神情扫荡了刚才一脸的俗气。是的,二十三年以前,公安跃进,她父亲因为“历史问题”抓进了劳动教养所。等她知道,从热火朝天的土高炉边赶回家时,母亲已经奄奄一息了。临终前,母亲对她说:“你父亲虽说是个讲求实际、精明忠厚的会计师,新中国成立前却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对我们党犯了罪。你要划清界限,洁身自好;划清界限,走自己的——路……”话没说完就断了气。几天之内,她失去了父亲和母亲。毫无思想准备,成了罪人的女儿。她觉得人们突然冷淡她,躲开她,她像一只家兔被抛到荒郊野外了。
“你,你还好吗?”他笨拙地寻话说。
“托福!”她心不在焉,“还是你好。”
他神经过敏地觉得她话中有话,逼出一个干巴巴的笑,清了喉咙,却又无话可说。
她看着左手的手纹,专注得目不转睛;他呢,正襟危坐、一动不动,盯着看她看手纹。
几乎同时,他俩想起了同一件往事……
那是高二上学期。班长在第一个班会上宣读她申请助学金的申请。她低垂着头,前额几乎碰着课桌。是虚荣?不,她觉得自己像个乞丐。班长像布施者,要同学们表态。
“她没有生活来源了。”一个经常赤着脚的乡下学生说。他是助学金享受者。
“我们班工农出身的同学多,”胖乎乎的团支书意味深长地盯着乡下同学说,“而助学金是有限额的。这是老师一再交代过的。”
风把玻璃窗吹得“砰”地关上了,仿佛人的嘴也关上了,教室里悄无声息。
班长为难地站着:“老师开会去了,让我们自己讨论。”他巴望大家放开发言。
“老师在不在我们都不要含糊嘛。”团支书不看班长,“要求进步的同学带头表态。”说着点了他的名,他上期末写了入团申请书。
他慌乱起来。他知道有同学错误地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与她的关系;他也明白团支书的潜台词。想到这是借以表现清白和接受团组织考验的机会,他激动地站起身。可,说什么?她是独女,没人供养了,这是事实;但助学金就那么点点,是应该优先考虑工农出身的同学……突然,一个变通的主意涌到脑子里,他暗地为两全其美的办法高兴:“她家里还有可以变卖的东西。”
“未必叫她背着衣裳到大街上叫卖?”一个女生难过地嘀咕,“人家一个女娃娃……”
是呀,能叫胆怯的她背东西上街叫卖么?他不知所措地坐下。教室里传来开抽屉、咳嗽和打哈欠的声音。
团支书沉吟少顷,像是克制住了心中隐隐升起的温情,使劲伸了个懒腰,朝班长点点头:“表决吧!”
班长盯了天花板一眼,闷声闷气地说:“赞成给助学金的举手。一、二——只有两票。”
举手的是那位不怕被挤掉助学金的乡下同学和那位温情主义的女生。
“反对的举手。一、二——也是两票。”班长的语调变得幸灾乐祸。
举手的是贯彻阶级路线的团支书,还有正在争取入团的他。
“不包括本人,五十票弃权。”班长公事公办的口吻,“赞成和反对的均未超过半数,请示老师再定。”
“不用请示了。”她抬起一双与世无争的眼睛,躲避着同学们惊异的目光,自甘认命地说,“我收回申请,真的,我收回……”接着,强忍不住的呜咽代替了说话。
第二天,她没到校,并且从此在教室里销声匿迹了。直到这个班毕业、各奔前程的时候,才有人提起她,说她从乡下亲戚家回到了县城,嫁给一个二级汽车修理工。团支书摇着胖脸,无限惋惜:“咬咬牙就能念完高中的,何必嫁碗饭吃!”他呢,为她在生活道路上节节退让叹息,心里叨念着:造不成汽车也当不成作家了……
“快吃,冷了!”她推推碗,从往昔的心酸中跳出来,又恢复了老板娘的精明,“你在哪儿工作?肯定是大城市的高楼里。”
“在有河流的地方。你呢?”废话!像一匙泼到桌上的醪糟水,捡不起来了。
“这不是!”她倒无所谓,“第三产业军——个体户。”
“她家里还有可以变卖的东西。”多么可耻的声音!他惶恐地左右瞅瞅,竟然是自己当年说的!一时的懦弱,铸成了终生的重荷!他汗毛倒竖,多少年郁积起来的良心的怨诉涌到嘴边,立即就要溢出来了。
有两个人坐下来。她丢开他,忙不迭地接待顾客去了。
他吞咽着醪糟蛋,没有醇甜,而是又苦又涩。看看正在顾客面前“王婆卖瓜”的她,担心她又与人争吵,胸口阵阵发紧。
他吃完醪糟蛋的时候,她正好忙完,踅身过来了。她歉然地搓搓手:“生意太忙……”说得恳切,眼睛含着笑。
“毕竟从小一起长大的!”他心里想着,眼前立刻又切入了“金沙江岸,沙滩灼灼泛白,四个孩子背着水壶、干粮、赤着脚……”的那组镜头。
“记得小时候吗?”他激动起来,“在河边打沙包蛋、挖机关、去下中坝——”
“总要路过石龙庵。”她眼里闪过一道光亮,可瞬息即逝了,怏怏地坐下,哑然一笑,“那只大黄狗吓死人啰,每次多亏你保护我。”
他不寒而栗:当她真正需要保护的时候,自己在哪里?
“狗为什么要咬人呢?人会不会咬呢?”这甜丝丝的声音从历史深处飘来,他沮丧地捶捶秃顶的脑门,自己几乎咬了她了……
“你回来有什么事吗?”她不喜欢提童年。
“专门想去下中坝……”他不由自主地总是提起童年。
“怎么?还想去捡琥珀?”她那开始衰老的脸不胜惊讶,“你真相信有那种琥珀?”
“去寻觅,要用我后半辈子的生命,去寻觅!”只有人,才可能有这种感情(理智、道德、美)上的寻觅,他热烈而虔诚地跑回故乡,本身就是一种寻觅。
“小三哥!”她扯开喉咙大笑,笑得前躬后仰,“你真勇敢呀!”那没遮没拦的笑,像金沙江水淹没下中坝一样,淹没了她脸上一切可能放光彩的部分。
望着她,他瞠目结舌。少顷,悲愤地站起身,跺了一脚!尽管人类没有力量战胜死亡,但是,人类应该制止早衰和夭折呀!
看到他这种神情,她惊诧地停止了笑。默默注视片刻,欣慰地长吁一声:“你还是童年的样子!”继而脸色陡然阴沉,眼皮微微一瞌,悲戚地说:“而我——我的童年就像流过去的水,匆匆逝去了,不再回头了!”
多么凄怆的语调!“水流到哪儿去了呢?它流走了就没有了吗?”她儿时的声音飘过来,缭绕在他的耳际,经久不散:“水流到哪儿去了呢?它流走了就没有了吗?”……哪儿去了?……没有了吗?……是的,她的童年像流水一样流走了,可今天这般凄怆的情境却留下了!自己的童年也像流水般流走了,可今天却牵心挂肠地返乡来了。他精神亢奋,怀着神圣、庄严的感情,审视、追逐着流走的水,思潮澎湃,一种新的启示潜入心里:那坦荡的沙滩,不正是静如明镜的流水冲积的么?那陡峭的悬岩,不正是柔如清风的流水砍削的么?那数不清的卵石,不正是软如云絮的流水磨圆的么?波涛滚滚的金沙江,奔来眼底,咆哮的水声贯耳,他更加强烈地又一次感到了流水那活跃的生命。其实,生命就像水,水的自我实践是永无休止地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逝即是行啊!天行健,过去的逝去了,而历史却前进了!他冲动地喊了她一声,为自己悟出一点人生的真谛,猛然从沉湎怀旧中脱颖而出:
“今天,我能回答你流水的去向了!流水不会逝去,一切都不会不留痕迹地逝去。逝去的一切铸成了今天,并将向明天延伸;逝去的一切是今天和明天的土壤、阳光、空气和水……”
1982年春节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