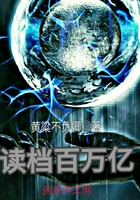秦心去开车帘子,虞鸢拦住了她的手,摇头对她说:“看看情况再下去。”
“你的手......”秦心看着虞鸢袖口处一小片的湿红,是车窗撞开的木碴刺上的,连忙取过包裹,准备找药,“不要紧罢?”
“这么点儿小伤,当然不要紧。”虞鸢漂亮的眼神闪过一丝感动,对她说,“来人这么蛮恨,定是了不得的大人物。”
大人物——
大人物?
虞鸢轻巧的一句话刺痛了她的耳膜。
这三个字就像是一方烙铁,焦灼着她所有的愤怒。仿佛她一时间失去了仔细的考量,恨不得立刻跳下车去与那位所谓的大人物理论。
她冲口而出,语气戏谑。
“大人物?大人物就可以随便欺负人么?”
车厢之外,赶车的颀长男子也忍不住想要与之理论。
“是你们撞了我的车。”秦策跃然下车,并不恼怒,对那车夫淡淡道:“无论是谁的车马,也不能霸着整条路不是。我的车已经被撞坏了,既是贵人,理应不缺这点儿赔车钱罢?”
“让开让开!我家公子急着赶路,没这个时间去管你的破车!”蛮横的车夫轻蔑的看了秦策一眼,就准备扬鞭。
“倒霉。”秦策掸了掸衣衫上的土,上车来探,就准备扶虞鸢和秦心下马,“看来我们只能走回去了……”只看到虞鸢一个人坐在车里,忙问,“阿心呢?”
转身,瞧见粉衣少女张开双臂,拦在路中间,那人的马车陡然停下,车夫怒道:“死丫头片子,到一边去!”
“你把我们的车撞成此番模样,就这么走么?”秦心丝毫不惧,甜美的声线一字一句地讲出,“堂堂长安,天子脚下,你家公子就算家世再显赫,身份再高贵,也不能不顾王法和道理罢?况且,你家公子有要事需理,难道我与兄长就是闲着等你们来撞的么?”
字字圆润,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她不依不饶,“要么赔我们车钱,要么烦劳你家公子走下车来,让百姓评评理,孰对孰错,好歹是个交代。”
“李安,早些说过你,莫要多事。”
车内男子的声音清淡如云,修长白皙的手指轻轻挑起车厢的紫烟绣丝枲,一身洁白崭新的白衣,翩翩丰姿温润如玉,面容清湛的宛如天外飞仙,明眸轻瞥车下之人。
唇色一瞬间苍白,似有恍惚。
“阿心?”
男子低柔唤着,依然叫着她的乳名,眉目淡淡地舒展,但是少却了熟稔。
那么的陌生。
是谁,一边吃着红豆糕,一边流着眼泪,还不忘了夸她,阿心,你真好。
是谁,曾经耐心地教着她,轻敲着她的脑袋,笨阿心,这么简单的诗还要看书?
又是谁,在她哭泣的时候,揽她入怀,温柔揩去她脸颊之上的眼泪,不哭了,刚才是我不对,我不该拿阿心开玩笑的,下次不会了……
可是车上之人?
秦心看着李睦旨,鼻子酸涩,想哭。
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当初他轻巧抽身的时候,她是怎样度过了那段日子,每每难受的时候坐在偌大的院子里吹冷风,只希望他能够在身边,哪怕是给她个回话,或者只是一句我有苦衷,她也能够理解他的。
而她千万分的思念和苦痛,最终换来了一个他亲手烧毁秦府的结局。
她恨。她恨到了牙根,恨到了骨血。
眼眶肿胀得厉害,秦心仍是倔强地仰起头,让自己能够直视曾经亲密宛如形影的他,微微点头,“李公子。”
一瞬间,他坐在车里,温柔而复杂地看着她,相顾无言。
而她质问,“你的车夫仗势欺人,你也不管的么?”
“嗯……”李睦旨低弱地应了,对她说,“是我方无礼了,理应我赔你车钱。”
公子,这是在赔礼么?驾车的李安目瞪口呆地看着秦心,并不知道面前的小丫头和少爷究竟又怎样的过往,慌忙张口劝阻道,“公子,你不能……”
“给我银票。”李睦旨定然截断李安的劝阻,低低地吩咐。
“是,是……”李安取过银票,恭敬地递给李睦旨。
李睦旨就要下车,却听到秦心冷漠道,“叫他送来罢。你是王公贵胄,你亲自送来的银票,我害怕没有性命用。”
李睦旨不回答,只是缓缓牵起白衣衣袂,淡然坐回车里,扯下了白玉勾,紫烟绣丝枲施施然飘下。
接过李安送来的银票,秦心只感觉鱼刺哽喉,却仍然是清了嗓子对车内之人道:“下次,请你记得,管好你的下人。”
慌忙转身。
一行泪,终于流了下来。
身后,马车啷当前行,飞啸着远离了她。
到了陈宅,官兵已经撤走,秦心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钥匙插进锁孔,没想到哗啦一下,锁居然开了。
北国的秋,风是格外凛冽,落叶飘了满地,无人清扫,踩在倾心园的地面上,细碎的脚步格外清晰。冰凉的石桌石凳,枯黄的草木,***也尽数凋残,秋风一掀,枯菊伴着寒风卷上了天。
打开房门,也和外面一样的冷清。家具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尘,轻轻一吹,土腥味肆意飘散。
秦心顿觉悲从中来。
第二日一大早,秦策一起床,未有吃饭,就匆匆忙忙赶了出去,被虞鸢拦住。虞鸢柔声问道:“你要去找谁?”
秦策深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像是自言自语,“我们,我们还能找谁呢?”
“倒是有一个人一定会帮你们。”虞鸢的语气斩钉截铁,“但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去求他了。”
秦策全神贯注地盯着虞鸢,“谁?”
“李睦旨。”
“他……”一提到李睦旨,秦策面色惨白,“我们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让我们去求他?除非我死。况且,是他逼得我们走投无路,他只怕是巴不得我们秦氏十八口全部下地狱,免得扰了他的好梦,他又怎么可能会帮我们救陈默?”
“有一句话是,解铃还须系铃人。”虞鸢斜睨着秦策,手抚着他的胸膛,轻轻笑着,“不记得了?”
“陈默的入狱又不是他在背后作梗,解什么铃,系什么铃?”秦策疑惑道,半响了才反应过来,顿时惊愕万分,“鸢儿!你的意思是…….!”立刻自己又推翻了想法,摇头,“不可能,不可能,他害我们尚能找出理由,他害陈默,实在是没有理由。”
“怎么不可能?”虞鸢虚虚哼了一声,“李睦旨乖滑的很,他要做什么事情,定然不会让人猜中。那些表面上越像是他做的事情,倒真有可能不是他做得。要我看啊,秦家被害,就与他关系不大。但陈默被害,十有八九是出自他之手。”
秦策被虞鸢说的晕头转向,“照你这么说,他就更不可能救陈默了。”
“那不见得。”虞鸢右手遮唇,对秦策悄声附耳道,“你不试,又怎么会知道呢?我有个办法,只不过是要你心爱的妹妹吃些亏。但我可以保证,只要你舍得用此法,陈默定会留着性命回来......”虞鸢将方法告之,秦策呆滞了半天,傻了一般,听到一半,忽然大声叫出来,一把别开虞鸢的手,“不行!不行!这个方法太险了,一旦出了差错,阿心的一辈子就毁了。”
“舍不得孩子可是套不住狼呢。”虞鸢伸出纤细如葱根的手指,为秦策理了理衣裳,“陈默犯下的可是死罪!大理寺审核的朝廷要犯,你以为是那么容易就能救的么?秦心不过就是小小的牺牲,比起一条性命,算的了什么?”
“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秦策面色痛苦,语调都变得起伏了起来,“我知道是我无能。但我绝对不会让阿心去冒这个险。”
秦心刚好从房间里面出来,听秦策这样说,满腹疑惑,不自觉地又退回了房子里。待秦策真正出了门,秦心这才恍恍惚惚地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