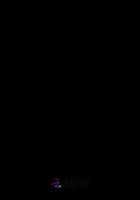连试了几次,都是一样,半点反应也没有。我索性放弃了华语,用了英文都没反应,看来不是系统语言的问题。
难道俺装机用的是盗版系统,这就不能玩了?
心中一阵惊慌,感觉头脑太乱,我只能颓然发动了密语,推出了系统。
拔下身上的各种传感器接头,我又把机器检查了一遍,没什么故障。又把程序代码过了一遍,两个小时后除了找到了几个不太重要的bug之外,一无所获,整个系统简直是完美。
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只能继续尝试,重新在身上贴满了传感器,又一次的进入了系统。
很可惜,还是没反应,我简直要抓狂了,在这么个绝对安静绝对黑暗的地界并不好玩,其承受的巨大压力难以想象,特别是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
到底是为什么?
这种地方不敢多待,我试了几遍之后匆匆退出了。
煮上一壶咖啡,我点上根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慢慢的将所有过程滤了一遍,看看自己以前在陈教授实验室时的状态与现在有什么不同。
积了一堆烟头,依然毫无头绪,我还是我,除了当了一回植物人外并无改变,如果说真要有改变,那就是碰到了阿东,学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东西而已,难道就是因为这个?
想起陈教授所说的有一部分人群会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原因,不能联入这个世界,难道我基因有了突变,成了这部分人群?
不对啊,这种千载难逢的好事不会落到我头上吧,几千年来人类都没进化了,我就突变了?
硬件与软件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就算陈教授做的有什么bug,在我这里也该补足了,看来还得从我自己的方面去找原因。
记忆中陈教授对这种不能接入的原因及解决方法有过大量的研究,但是我从没接触过,毕竟咱是实实在在体验过的,更不不担心,这次碰到了才会束手无策。
上网找了半宿资料,逐渐唤回了陈教授这方面的记忆,我才大致有了一点了解。大体来说,这种东西与信仰有关。
我当时在陈教授实验室做的时候,并不感觉这有什么,因此心中空空荡荡,无牵无挂,说句白话,那就是全身心的相信陈教授做的都是完美的。
在这种状态下,我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想到失败的可能,就像老子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我说的要有光,其实想的并不是创造光,潜意识里估计就是想开灯……
到了今天咱自己玩,心中那种不安,对未知的恐惧,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会对我的心理产生微妙的影响,叠加在一起,估计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并不是不相信自己会创造光,但是,正因为我相信了,这才坏了大事,因为我心中已经想了。
就像我们走路,我们根本不会去想自己能不能走路,因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旦想到,我会走路,可以走路,这就落了思维的陷阱,按佛家的说法那就是着了相。
此种解释是陈教授的理解,按他的说法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从他的记忆中还发掘出了一件秘事,那就是在他决定让我做实验之后,特地花了极大的精力催眠、暗示、引导我,以便让我更容易的进入角色。
回想起陈教授的所作所为,还真有这么点意思,我恍然大悟。不过催眠可能无效,陈教授的记忆也证明了这一点,我精神抗性似乎不错,俗话讲就是神经粗大……
知道了原因就好办,总有解决的方法。
略略想了一下我就拟定了行动方案,先静坐,洗涤浮躁的心灵,进入那种定的境界。
与平常打坐不同,此时我在不停的暗示自己,我就是上帝,我就是创世主,我是佛陀,我是三清,我是至高无上的至尊,我是无所不能的,我要唤醒阿东……
这些乌七八糟的暗示语不管有没有用,我反正把它们深深的印在了心底,按理说这是潜意识区,有什么影响我也就顾不上了。
三天来我什么事情都不做,每天就在重复这个过程,当真是虔诚无比,有没有效果不知道,反正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有一种超脱的感觉,一切尽在掌握中……
在未知面前要谦卑……
也许是极大的压力面前才会有动力,这些日子过的很充实,虽然单调了一点点。
准备功夫做足,我这才进行了第三次的尝试。
又进入了那个虚无的地方,这次我倒没有急吼吼的动作,宛如福至心灵般的又开始入静。
当然了,此时我是没有身体的,那什么姿势之类的没有意义,只是单纯意义上的入静,等再次出来的时候心中已经毫无一物。
没来由的冒出了道德经中的文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恒无欲,以观其妙;恒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心中似有明悟,我微微一笑,缓缓说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声音并不大,至少我是轻声所说,只是回荡在这个虚无的空间似乎在往极限远处延展,渐行渐远,渐行渐响,直到最后宛如洪钟大吕,来回震荡,似乎激出了一道道的波纹。
四周的空间微微一亮,似乎破开了一道口子,所有的存在找到了出口,往之急泄,我同样也被吸引,冲了进去。
眼前豁然开朗,又是那个熟悉的世界,我细细一瞧,这不就是我以前创造的那个虚拟实境吗?
心中略略一感应,我身形一晃已经来到了当年竖起撑天巨碑旁边。
这碑记录了我与阿东共同的日子,不知过了多少年,依然屹立在那里不倒,只是越加的高耸,带了些岁月的沧桑。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
只是阿东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