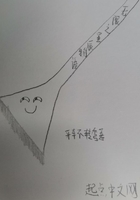周岁酒在那一天的晚上举行。下午,艾山仔细洗了头发,把下巴和脸颊刮得很干净,然后,穿上了那条袍子。他在洗脸盆上面的那一块残缺一角的镜面里打量自己,他感觉自己打扮得还算整洁,他尤其喜欢母亲给他缝制的这件礼服长袍,他喜欢那淡绿色而不是红色、金色或亮紫色的镶边。但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长相平平:他的鼻梁有点儿扁平了,毫无特点的嘴巴不大不小,也许他脸上唯一好看的地方是他的长睫毛,可这算什么呢?他又不是个姑娘,并不需要这样的长睫毛。
五点多的时候,艾山往阿克木老人的家走去,他没有骑马,因为阿克木老人的毡包离诊所这里走路只需要三十多分钟。他走在余晖渲染下的草坡上,穿着白袍。路上,他看见一些归牧的牛群,还有几个骑马赶来的临近地方的牧民,其中有一两个裹着色彩鲜艳的头巾的妇女。他听见赶路的人含糊的、由远而近的交谈声,以及归牧的人单调的吆喝声,但他什么也没有听清楚。他想着他自己的事,对自己不够满意,还有些说不清楚的不安,但他仍然兴奋、快乐。当他看到站在阿克木家那个大毡包外面的一群女孩儿时,他才恍然大悟,他所一直担心、害怕的正是她们。而她们正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做着手势,有两三个女孩突然神秘兮兮地朝他看过来,似乎她们正在谈论着他。
他硬着头皮经过她们身边,而她们低低的笑声传进他的耳朵里,这笑也像是冲着他来的。于是,连他的耳朵也红了。他钻到毡包里去了,看到里面有更多的年轻女人,但也有很多男人。阿克木老人的小儿子嗓门很大地迎接他,这个腼腆的外地年轻人的到来似乎让他脸上有光,他拍着艾山的肩膀,好像他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后来,一些脸熟的人走过来和他说话,还有几个找他看过病的妇女。他觉得舒服了一点儿,不那么热了,他的心跳逐渐平稳,开始悄悄打量周围的人。慢慢地,有不认识的年轻女人上来和他说话,她们问他有关胳膊上莫名其妙起的小水疱,被马咬后留下的伤疤还有突然出现的眩晕,有个女孩儿说她的耳朵里经常有轰鸣声,还有个女人说她夜里老是做吓人的梦,问他有没有什么药可以治。不管那是否是可笑的问题,他总是细心地替她们分析,尽量找到答案,但每一次,他都对自己的回答不满意,过后总觉得那样的回答太仓促含糊了。客人们走来走去,而他似乎就一直站在他进来之后选定的一个地方,一个灯光稍暗、不容易引起注意的地方。
吃饭的时候,艾山被邀请坐在重要人物的一桌,那一桌上有主人阿克木老人、他的长子、二儿子还有两个牧区的干部、三四个他不认识的、年龄较长的牧民。他觉得别扭、难受,却找不到借口推辞。有人开始悄悄议论这个坐在尊长者之间的年轻人了,他显得多么年轻、害羞呀!一个可爱的、涉世未深的人。
当别人和他说话时,艾山总会专注地听着,很有礼貌地点头,而大部分时间,他只是低头盯着眼前的杯子、盘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隐约地感到有一道目光不断朝他看过来,但每当他循着感觉的方向看过去,他却只看到一些因为欢笑而颤动、闪烁的女人的身影。他不好意思朝那个方向一直寻找,但他觉得那双眼睛就隐藏在那些影子中间,它悄无声息地注视自己,于是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个表情都落在这目光构成的透明的网中,无一逃脱。他又开始不安了,他调整着自己的位置,一点点地侧过身子,可他觉得他并没有摆脱那道目光,它就像一个轻盈灵巧的飞虫,在他发梢、衣领和背后飞动。
那些人劝他喝酒,他们让他喝了太多的酒,因为他不会拒绝,因为拒绝要说很多客套、聪明的话,看起来他还不会。所以,他的脸涨红了,他用手扶住自己那低垂的额头。突然,他抬起头,他那双明亮的眼睛飞快地朝一个地方看过去。只此一下。然后,身边的人又和他说起话来了,他于是带着儿子般亲昵而温顺的神情看着那个长者,眼睛里闪动着惊奇的亮光。在旁人看来,这年轻人已经有点儿醉意了。可他自己却正为一个发现而欢喜,他似乎找到那双眼睛了,他刚才捉住一双迅速闪开的、有些惊慌的眼睛。她坐在一群女客人中间,娇小,毫不突出,但她那双眼睛,她垂在脸庞两侧的黑头发……一瞬间,他的心里被一种欢喜、甘甜、涌动着的东西充满了。但他如何能确定那就是那双眼睛呢?也许它早就躲开了他,而她只是不经意地碰上了他的目光。他假装专注地听旁边的人对他说话,而他一句也没有听到心里。在心里,他有些迟疑、迷惑,还有种说不出的快乐。
酒席松散了,人们又开始四处走动,有的人到毡包外面去了。这中间,一些女人们从她们坐的地方起身,围到满周岁的男孩儿和他母亲坐的桌子那儿,她们逗那孩子,孩子却不解地哭起来。有些住在较远地方的人开始告辞了,阿克木老人站在靠近门的地方,和要离开的客人告别。但不少人兴致还很高,男人们还在喝酒,准备闹腾一阵。这时,他突然发觉她不见了。迷迷糊糊中,他也站起身,走到外面去了。他看见天空中的半轮月亮和一些稀疏的星星,还有一些人骑着马离开的影子。也有人骑着摩托车走了,那起初尖锐的震动声慢慢变得廖远、寂寞。一些女孩儿在不远处站着,围在一块儿说笑。在这些影子里,他都没有找到他要找的那个人。他向堆着干草垛的空地那边走去,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是想往更远的地方走。在他那双朦胧的眼睛里,干草垛就像贴在夜幕上的剪影,像是在草原的另一边。
他有点儿累了,在一个草垛下面坐下来,夜里的凉气渗透了他的袍子,可这凉意多么清爽。他嗅闻着干草松软的香气,不知怎么想起了炉膛里刚拿出来的热香的馕,他仿佛又看到一双柔软的女人的手,看到在奶白色的晨雾里显得乌黑湿润的女人的头发,仿佛听到了纱一般轻柔的女人的说话声……但最后这一点似乎并非幻想,因为他真的听到了女孩儿的说话声,这说话声越来越近,他发现已经到了干草堆的后面。
“是真的吗?可是……可是,你都对他说了什么?”一个女孩儿压低着声音、激动地说。
“没有,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怎么能说呢?”另一个女孩儿声音微微颤抖地说。
“可他怎么知道的?他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他好像发现了,我感觉他已经知道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一个女孩儿喃喃地说:“感觉,多奇怪的感觉。”
“你不会对别人说吧?”声音颤抖的女孩儿怯怯地问。
“啊?你怎么想的,我当然不会!”爱激动的女孩儿几乎叫出来。
“好了,好了,你不会说的,我知道。我只告诉过你一个人。”她说。
坐在那儿的艾山一动不动,几乎不敢呼吸,幸好他被掩藏在草垛浓黑的阴影里面。于是,那声音就从他身边经过,两个女孩儿边走边说,趁着月光往毡房那儿去了。他知道其中没有她,但他仍然觉得她们每一个的影子都很美。他无意中听到了她们的谈话,她们的秘密,可他不知道她们是谁,她们爱上了谁。这一切,在他想来也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