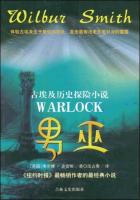来到这个劳改农场工作后,我还是第一次出差,带一个犯人保外就医。一起去的还有另外两个干事,老刘和老陈。我们开了一辆押犯人的面包警车去地区总医院,我不会开车,就坐在后座。
从监狱到市里去,有段很长的山路。路道狭窄,路面被运煤的大车辗坏了。他们说,单是这段路,就得耗上将近三个小时。路面的柏油早就蚀光了,剩下一条曲折的、布满大小坑洼的土路。路面上那层厚厚的灰黑色煤屑,一过车就荡起来,遮住人的视线。一路上,我们也聊聊天,但大部分时间,只听见汽车在路上颠簸时发出的声音,有时是吱吱呀呀的金属部件磨擦声,有时像一头爬出深沟的牲口发出的沉重吭哧和喘息。
犯人躺在隔离栏后面,我一转头,就能越过那些细钢筋杆看见他,但我尽量不去看他。他在后面不时发出让人难受的呻吟声,我猜想颠簸让他的身体某个地方很疼痛。后来,车在一个山路转弯的地方几乎和一辆运煤的大车打照面,于是干事老陈猛打方向盘躲闪,我们这些人差点被从座位上甩出去。这时候,我听见犯人发出一声尖厉的喊叫。车子稳下来以后,老陈和老刘一边痛骂大车司机,一边总结化险为夷的经验。我这时朝犯人扫了一眼,发现他的身体从刚才趴着的地方被甩到靠近车门的地方。他似乎想挣扎着爬回原来的地方,于是费力地蠕动着躯体,铺在他身子底下的那条破毯子就被扭成了一团疙瘩。看来这个人的脊椎病得很厉害。我当然不能叫车停下来,给他调整躺卧的姿势,但我看着那个徒劳无功地蠕动着的躯体有些心烦,就说:“你别再动了,你越扭越不舒坦。”
“什么?他在干什么?”爱咋唬的老刘马上大声问道。
“没事儿,他躺偏了,想挪回去。”我带着嘲笑的口气说。
“你还挺知道舒服的,想舒服你别犯罪啊,你进了监狱还想舒服?躺好!”老刘从前面对犯人发威。
老陈也冷笑了一声,说:“曹大余,你最好老实点,别以为你得个病就有优待了。因为要送你去医院,我们几个刚才差点搭上命,他妈倒霉着呢。你不想想,你是个什么坏东西?这时候你后悔了吧?你这种人就是坏事儿干太多,报应来了。要让你这种人都舒服了,那他妈就没天理啦。”
犯人害怕了,他不再试图蠕动着爬回原来的位置了。他保持面朝下趴着的姿势,把小手臂垫在脸的下面。毯子已经皱成一团,他的大部分身体都贴在车厢的铁皮上。但他穿着犯人的冬衣,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他仍然不时发出呻吟,我尽量置若罔闻。我想,老陈说得对,他现在忍受的一切不过是对他以往恶行的惩罚。
这个曹大余从小死了父亲,没人管教,和附近的不良青年混在一起,成了他村里谁也不敢惹的地痞恶棍,偷、抢、殴打其他村民、侮辱妇女,什么坏事都干过。据说,有一次他母亲劝阻他,他不知道怎么昏了头,竟然顺手拿一个耙子朝老人扔过去,把老人的脚严重砸伤。他的恶行在监狱里广为流传,于是,在他两年多来的服刑期间,其他的犯人都看不上他,时常要找他的麻烦。初来的时候,我不了解这回事儿。但后来,他们都告诉我,曹大余的事儿你不要管,这样的恶棍,该修理一下。
有天下午,我刚走进办公楼的过道,有个老妇人朝我迎面跑过来,到了跟前的时候,突然跪下了。我吓了一跳。她说:“别再打他了,别叫人再打我儿啦……”这时,从后面追上来的两个警卫把她拉起来,赶出去了。这个老人,就是曹大余的母亲。原来,她探监的时候看见儿子又被打了,就冲到办公室里闹,看见穿警服的就下跪,叫饶了她的儿子。后来,她又来闹了一次。我们只好叫为首的几个犯人收敛点儿。那以后,我感到安心了一点儿。不,我一点儿也不同情曹大余,可我是新来的,我觉得还是一切照规矩来比较保险。
四天前,我们接到曹大余紧急保外就医的通知,要从厂部医院转到地区总医院去。有干事去厂部医院打听,得知曹大余的脊椎长了肿瘤,属正常疾病,排除了殴打所致的可能。我们去厂部医院接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走不成路了。护士给他在车后面铺毯子,把他面朝下安置下来。我们站在一旁冷眼看着。可能,其他两个人和我想的是同样的问题:这个虚弱得没法走路的人就是那个恶棍曹大余吗?
我们谁也没和犯人搭腔,就开车上路了。
山路就快走到头了,老刘建议下车抽烟透气,屁股已经颠疼了。我就要推开车门的时候,听见犯人嘟哝了一句什么。
“你说什么?”我故意大声问。另外两个人此时都已经下车了。
“王干事,报告……我……我想小便,我真憋不住了。”他嘶哑着嗓子说。
“坐在后面真是倒霉”我想。
“你等着吧。”我没好气地说。
我下了车,发觉外面冷得很,空气也好得多。那两个人正说笑着,老刘也递给我一根烟,我们就站在那儿说了一会儿闲话。看他们都把第一根烟的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了,我才说:“那家伙要小便。”
“事多儿!”老刘不耐烦地说。老陈却没有搭话,又拿出一根烟燃着了。
我等了一会儿,又问:“怎么办?我看他自己不行。”
“怎么办?叫他憋着。”老陈高声说,是要叫曹大余听见。
我们都笑了,但我笑得有点儿难看。我知道,因为犯人是向我报告的,事情就变成了我的。他们的意思是叫我自己解决。
我问:“要开手铐吗?”
“像他这种病,开不开都一样。”老陈模棱两可的说。
于是,我从他那儿要了手铐钥匙,走过去拉开后面的推拉门,要犯人坐起来。
“王干事,我不能坐,坐不起来,我后面……太疼了。”曹大余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瞪了他一眼,拉着他的双腿把他半个身子拉出来,打开了他的手铐。这时候,他的两条腿挂在车门外,上身却还是使不上劲儿。我懊恼地看着那晃荡在车门外的两条瘦腿,我知道老刘和老陈也在看着我。这时,我又听见犯人急促地哀求:“王干事,我快憋不住了。”
我上去抱住他的腰,把他拖下来,身子斜靠到车门上。可能我拖拉时用力太猛,他哀号起来。我的心竟然揪了一下。随后,我在一边厌恶的扶着他。等我再度把他的手铐起来,面朝下推进车里时,发现他把尿洒在棉裤上不少。
“王干事……”他又想说什么。
“进去!”我生气地喊,“老实躺着!”
我脸色阴沉地走过去把钥匙还给老陈。他还开玩笑说:“那家伙没尿裤子吧?”
我笑了笑,没回答。
老刘说:“是其他人我就帮,这个坏蛋就得治他,就让他尿裤子。”
我说:“说得容易!尿到车里不还是你刷车?”
老刘嘿嘿笑了,说:“这我可没想到。你小子脑袋灵光着呢。”
又坐到车里继续赶路的时候,我对刚才的行为有些后悔。我不应该那么粗暴地拖拉一个病人。但我知道,我的每一个同事,每一个知道他所犯下的罪恶的人都可能这么干,或者会更糟。老刘和老陈把烂包袱扔给了我,如果我不接,他们可能任由曹大余尿在车里、泡在自己的尿液里。
我看着坐在前面的那两个人的沉稳的背影,觉得和他们比,我确实有些幼稚、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