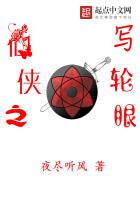司马谈所谓道家,即是《汉书》所谓杂家。不过《汉书》分类时,把古代思想史里的老子、庄子、田骈、列子等等列为“道家”,把道家的范围收小了,故《吕氏春秋》和《淮南王书》都收不进去了。其实老子、庄子一班人都是色彩鲜明的思想家,他们何尝有“道家”之名?“道家”一个名词,不见于秦以前的古书。《庄子·天下篇》(不是庄周所作)所举老聃、关尹、墨翟、禽滑厘、慎到、彭蒙、田骈、宋钘、尹文、庄周等人,都称“道术”。道即是路,术是方法,故不论是老聃,是墨翟,是慎到、尹文,他们求的都是一条道路,一个方法,尽管不同,终究可称为“道术”。故秦以后的思想,凡折中调和于古代各派思想的,使用这个广泛的道术原意,称为“道家”。道家本有包罗一切道术的意义,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也。故司马谈所谓道家,正是《汉书》所谓“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这是“道家”一个名词的广义。
但道家虽然兼收并蓄,毕竟有个中心思想,那便是老子一脉下来所主张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自然变化的观念,即是司马谈所谓“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道。因为这个大混合的中心思想在此,所以“道家”之名也可以移到那个中心思想系统的一班老祖宗的身上去,于是老子、庄子一系的思想便也叫做“道家”了。这便是“道家”一个名词的狭义。
道家之名,大概起于秦汉之间,于今不可详考了。汉功臣陈平曾说:
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此话见于《史记》(五十六),不知是陈平真有如此先见之明,还是后来道家造出这样的报应故事。若陈平真有此话,则是道家之名在前二世纪时已成立了。以我所知,道家之称,这是最早的一次。以后便要算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话了。依司马谈的话,道家是用老子的“无为”思想作中心的大混合,是一个杂家。《汉书·艺文志》的“杂家”有《吕氏春秋》和《淮南王书》,其实这两部书都可以代表那中心而综合儒墨阴阳名法各家的道家。故我用《吕氏春秋》来代表汉以前的道家,用《淮南王书》来代表秦以后的杂家。其实都是杂家,也都是道家,都代表思想混一的趋势(适按,此节应全删,此章应改题《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的贵生主义
《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的宾客所作。吕不韦本是阳翟的一个商人,用秦国的一个庶子作奇货,做着了一笔政治上的投机生意,遂做了十几年的丞相(前249—237),封文信侯,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史记》说:
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史记》八十五)
吕不韦死于秦始皇十二年(前235)。此书十二世纪之末有《序意》一篇的残余,首称“维秦八年”,当纪元前239年。此可见成书的年代。
《吕氏春秋》虽是宾客合纂的书,然其中颇有特别注重的中心思想。组织虽不严密,条理虽不很分明,然而我们细读此书,不能不承认他代表一个有意综合的思想系统。《序意篇》说:
维秦八年,几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吕不韦)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圆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大圆即天,大矩即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哀,灾日隆。”
这是作书的大意。主旨在于“法天地”,要上揆度于天,下考验于地,中审察于人,然后是与非,可与不可,都不能逃遁了。分开来说:
天曰顺,顺维生。
地曰固,固维宁。
人曰信,信维听。
第一是顺天,顺天之道在于贵生。第二是固地,固地之道在于安宁。第三是信人,信人之道在于听言。“三者咸当,无为而行。”无为而行,只是依着自然的条理,把私意小智平下去。这便是“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一部《吕氏春秋》只说这三大类的事:贵生之道,安宁之道,听言之道。他用这三大纲来总汇古代的思想。
法天地的观念是黄老一系的自然主义的主要思想(这时代有许多假托古人的书,自然主义一派的人因为儒墨都称道尧舜,尧舜成了滥调了,故他们造出尧舜以前的黄帝的书来。故这一系的思想又称为“黄老之学”)。而这个时代的自然主义一派思想,经过杨朱的为我主义,更趋向个人主义的一条路上去,故孟子在前四世纪末年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又说当时的三大系思想是杨、墨、儒三家。杨朱的书,如《列子》书中所收,虽在可信可疑之间,但当时的“为我主义”的盛行是决无可疑的。我们即使不信《列子》的《杨朱篇》,至少可以从《吕氏春秋》里寻得无数材料来表现那个时代的个人主义的精义,因为这是《吕氏春秋》的中心思想。
《吕氏春秋》的第一纪的第一篇便是《本生》,第二篇便是《重己》;第二纪的第一篇便是《贵生》,第二篇便是《情欲》。这都是开宗明义的文字,提倡的是一种很健全的个人主义,叫做“贵生”主义,大体上即是杨朱的“贵己”主义。(《不二篇》说“阳生贵己”,李善注《文选》引作“杨朱贵己”。是古本作“杨朱”,或“阳朱”)其大旨是: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也者,可以托天下。(《贵生》)
倕,至巧也;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玑,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重己》)
这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本意。本意只是说天下莫贵于吾生,故不以天下害吾生。这是很纯粹的个人主义。《吕氏春秋》说此义最详细,如云:
身者,所为也。天下者,所以为也。审所为所以为,而轻重得矣。今有人于此,断首以易冠,杀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饰首也,衣所以饰身也。杀所饰,要所以饰,则不知所为矣。世之走利,有似于此。危身伤生,刈颈断头以徇利,则亦不知所为也。不以所以养害所养。能尊生,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禄,则必重失之。生之所自来者久矣,而轻失之,岂不惑哉?(《审为》)
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轻也。夫生岂特随侯珠之重也哉?(《贵生》)
以上都是“贵生”的根本思想。因为吾生比一切都重要,故不可不贵生,不可不贵己。
贵生之道是怎样呢?《重己篇》说:
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高诱注,适,节也)
《情欲篇》说:
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
怎么叫做“由贵生动”呢?
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止。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贵生》)
这样尊重人生,这样把人生看作行为动作的标准,看作道德的原则,这真是这一派个人主义思想的最大特色。
贵生之术不是教人贪生怕死,也不是教人苟且偷生。《吕氏春秋》在这一点上说的最分明:
子华子(据《吕氏春秋·审为篇》,子华子是韩昭侯时人,约当前四世纪的中叶。昭侯在位年代为前358到333)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分是一部分,故叫做亏。亏是不满)。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服字高诱训“行也”,是错的。服字如“服牛乘马”的服,在此有受人困辱羁勒之意)。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皆知其所甚恶(《墨经》云,知,接也),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谓也。故迫生不若死。
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贵生》)
正因为贵生,所以不愿迫生。贵生是因为生之可贵,如果生而不觉其可贵,只得其所甚恶,故不如死,孟轲所谓“所恶有甚于死者”正是此理。贵生之术本在使所欲皆得其宜,如果生而不得所欲,死而得其所安,那自然是生不如死了。《吕氏春秋》说:
天下轻于身,而士以身为人。以身为人者如此其重也!(《不侵》)
因为天下轻于一身,故以身为人死,或以身为一个理想死,才是真正看得起那一死,这才叫做一死重于泰山;岂但重于泰山,直是重于天下。故《吕氏春秋》又说: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朱。坚与朱,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犹此也。(此下引伯夷、叔齐饿死的事)……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轻。有所重则欲全之,有所轻则以养所重。伯夷、叔齐此二士者,皆出身弃生以立其意,轻重先定也。(《诚廉》)
全生要在适性,全性即是全生。重在全性,故不惜杀身“以立其意”。老子曾说: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乃)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吕氏春秋》解释此意道:
惟不以天下害其生也者,可以托天下。
又说:
天下轻于身,而士以身为人。以身为人者如此其重也!
明白了这种精神,我们才能了解这种贵生重己的个人主义。
儒家的“孝的宗教”虽不是个人主义的思想,但其中也带有一点贵生重己的色彩。孝的宗教教人尊重父母的遗体,要人全受全归,要人不敢毁伤身体发肤,要人不敢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这里也有一种全生贵己的意思。“大孝尊亲,其次弗辱”,这更有贵生的精神。推此精神,也可以养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人格。所不同者,贵生的个人主义重在我自己,而儒家的孝道重在我身所自生的父母,两种思想的流弊大不同,而在这尊重自身的一点上确有联盟的可能。故《吕氏春秋》也很注重孝的宗教,《孝行览》一篇专论孝道,甚至于说:
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
这是十分推崇的话了。但他所引儒家论孝的话,都是全生重身的话,如曾子说的:
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
又如曾子“舟而不游,道而不径”的话;又如乐正子春下堂伤足的故事里的“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其身,不损其形,可谓孝矣”的一段话,都可以算作贵生重己之说的别解。《孝行览》又说:
身也者,非其私有也,严亲之遗躬也。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
这正是一种变相的贵生重己主义。
《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
《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根据于“法天地”的自然主义,充分发展贵生的思想,侧重人的情欲,建立一种爱利主义的政治哲学。此书开篇第一句话便是: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备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则亦失所为修之矣。(《本生》)
政府的起源在于“全生”,在于利群。《恃君》篇说: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犬,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
这里可以看出《吕氏春秋》的个人主义在政治上并不主张无政府。政府之设是为一群之利的,所以说:
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恃君》)
所以说:
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
所以说: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
政府的功用在于全生,故政府的手段在于利用人的情欲。《用民》篇说:
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无所不用。用民有纪有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充,实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
《为欲》篇说:
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夫无欲者,其视为天子也,与为舆隶同;其视有天下也,与无立锥之地同;其视为彭祖也,与为殇子同。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寿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劝。舆隶,至贱也;无立锥之地,至贫也;殇子,至天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禁。
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
从前老子要人“无知无欲”,要“我无欲而民自朴”,要“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墨者一派提倡刻苦节用,以自苦为极,故其后进如宋钘有“情欲寡浅”(欲字是动词,即“要”字)之说,以为人的情欲本来就是不要多而要少的(《荀子·正论》篇、《正名》篇,《庄子·天下》篇;看我的《古代哲学史》第十一篇第三章三,第十二篇第一章二)。这种思想在前三世纪很受严重的批评了,最有力的批评是荀卿的《正名》和《正论》两篇。荀卿很大胆地说: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正名》)
《吕氏春秋》从贵生重己的立场谈政治,所以说的更彻底了,竟老实承认政治的运用全靠人有欲恶,欲恶是政治的纪纲;欲望越多的人,越可得用,欲望越少的人,越不可得用;无欲的人,谁也不能使用。所以说:
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为得欲无穷也。(《为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