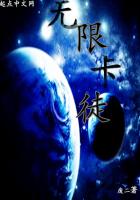两《记》最古之篇,共推《夏小正》,谓与《禹贡》同为夏代遗文。果尔,则四千年之珍秘矣。然自朱熹、方孝孺已大疑之,谓恐出《月令》之后。其实《夏小正》年代勘验甚易,因篇中有纪星躔之文——如“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三月,参则伏”;“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等,天文家一推算,当可得其确年也。其最晚者,如《王制》,据卢植云,汉文帝时博士所作。虽尚有疑问(说详次条),如《礼察》、《保傅》之出汉人手,则证佐凿然(《礼察》篇有论秦亡语)。如《公冠》篇载“孝昭冠辞”,则为元凤四年以后所编著,更不待问矣。要而论之,两戴《记》中作品,当以战国末、西汉初百余年间为中心,其中什之七八,则代表荀卿一派之儒学思想也。
《礼记》之编纂者及删定者
手编《礼记》者,谁耶?汉、隋《志》,《史》、《汉》《儒林传》及各注家皆未言及。惟魏张揖《上广雅表》云:“周公著《尔雅》一篇。爱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尔雅》为《礼记》中一篇,说详末段。)揖言必有所据。然则百三十一篇之编纂者或即叔孙通也?但通以后必仍多所增益,如《保傅》、《礼察》、《公冠》等明出孝文、孝昭后,是其显证。至次第续纂者何人?则不可考矣。
刘向校中书时所谓《礼记》,实合六部分而成。《隋志》云:“向检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孔子三朝记》、王氏史氏《记》、《乐记》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案《汉志·礼家》:“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家》:“乐记二十三篇。”《论语家》:“孔子三朝记七篇。”凡二百十五篇(《隋志》少一篇)。今《三朝》七篇,明载《大戴》,而郑康成《礼记目录》有“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此于《别录》属乐记……”等语,知今本《礼记》各篇,不仅限于“记百三十一篇”之范围内,而《明堂阴阳》等五种皆被采入,故《礼记》实合六部丛书为一部丛书也。王氏、史氏盖皆叔孙通以后继续编纂之人,惟所纂皆在百三十一篇外耳。
大戴删刘向、小戴删大戴之说,起于《隋书·经籍志》(原文前引)。二戴武、宣时人,岂能删哀、平间向、歆所校之书,其谬盖不待辨。至小戴删大戴之说,据《隋志》谓:“小戴删定为四十六篇,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乐记》,乃成今本之四十九篇。”后人因有以今本《礼记》除《月令》、《明堂位》、《乐记》外余四十六篇皆先秦旧籍,惟此三篇为秦汉人作者。此说之所由起,盖以四十六合大戴未佚本之八十五恰为百三十一篇,乃因此附会也。然此说之不可通有二。其一,两戴《记》并非专以百三十一篇为原料。如《三朝记》之七篇、《明堂阴阳》之三十三篇、《乐记》之二十三篇皆有所甄采,已具如前述。合两《戴》以就百三十一篇之数,则置书中所采《明堂》等五种诸篇于何地?其二,两《戴》各篇,并非相避,其最著者,《哀公问》、《投壶》两篇,二本今皆见存,《曲礼》、《礼器》等七篇(详见前《大戴》目录条附语)亦皆《大戴》逸目。又如《大戴》之《曾子大孝》篇全文见《小戴·祭义》,《诸侯衅庙》篇全文见《小戴·杂记》,《朝事》篇一部分(自“聘礼”至“诸侯务焉”)见《小戴·聘义》,《本事》篇一部分(自“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杀以见节”)见《小戴·丧服四制》。其余互相出入之文尚多。然则二戴于百三十一篇之记,殆各以意去取,异同参差,不必此之所弃即彼之所录。牵附篇数以求彼此相足,甚非其真也。
最后当讨论者,则为马融补三篇之问题。云马融补三篇者,盖务节《小戴》为四十六篇以合《大戴》之八十五,求彼此相足。其削趾适屦之情,既如前述。《小戴》四十六篇之说,不知何昉。藉曰有之,则《曲礼》、《檀弓》、《杂记》各有上下篇,故篇名仅四十六耳。《小戴》篇数之为四十九,则自西汉时已然。《后汉书·桥元传》云:“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说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者也。《曹褒传》云:“父充持庆氏礼,褒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庆氏学遂行于世。”则褒所受于庆普之《礼记》亦四十九篇也。孔颖达《正义》于《乐记》下云:“按《别录》,《礼记》四十九篇。”则刘向所校定者正四十九篇也。而郑目录于《王制》下云:“此于《别录》属制度。”于《月令》、《明堂位》下并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益足明此三篇为《别录》所原有,非增自马融也。
内中《王制》篇之来历,据《正义》引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书。”(《经典释文》引同)陈寿祺谓卢说本《史记·封禅书》。据《索隐》引刘向《别录》谓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等篇。以今《王制》参检,绝不相合,非一书也(见《左海经辨》)。《月令》篇之来历,据郑目录云:“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钞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篇中有“命太尉”语。太尉,秦官,故郑君断此为秦人书。)寿祺亦力辩其非(文繁不引)。以吾论之,《王制》、《月令》非后汉人续补,殆为信谳;然恐是秦、汉间作品。两《戴记》中,秦汉作品甚多,又不独此二篇也。后儒必欲强跻诸周公、孔子之林,非愚则诬耳。
尤有一事当附论者。《汉志》“乐记二十三篇”,今采入《小戴》者只有一篇。郑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谓从二十三篇之《乐记》采出也。《正义》云:“盖合十一篇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其余十二篇为《戴》所不采,其名犹见《别录》,曰则:《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也(并见《正义》引)。观此尚可知当时与《礼记》对峙之《乐记》其原形何如。今此十一篇者见采于《小戴》而幸存,其中精粹语极多,余十二篇竟亡,甚可惜也。
以上关于《礼记》应考证之问题略竟。此书似未经刘歆、王肃之徒所窜乱,在古书中较为克葆其真者,此亦差强人意也。
《礼记》之价值
《礼记》之最大价值,在于能供给以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者流——尤其是荀子一派——学术思想史之极丰富之资料。盖孔氏之学,在此期间始确立,亦在此期间而渐失其真,其蜕变之迹与其几,读此两《戴记》八十余篇最能明了也。今略举其要点如下:
一,孔门本以“礼”为人格教育之一工具,至荀子则更以此为唯一之工具,其末流乃至极繁琐极拘迂,乃至为小小仪节费几许记述几许辩争。读《曲礼》、《檀弓》、《玉藻》、《礼器》、《郊特牲》、《内则》、《少仪》、《杂记》、《曾子问》……等篇之全部或一部分,其琐与迂实可惊。观此,可见儒学之盛即其所以衰。
二,秦、汉间帝王好大喜功,“封禅”、“巡守”、“明堂”、“辟雍”、“正朔”、“服色”等之铺张的建设,多由儒生启之,儒生亦不能不广引古制以自张其军,故各篇中比较三代礼乐因革损益之文极多,而大抵属于虚文及琐节。但其间固自有发挥儒家之政法理想及理想的制度,极有价值者,如《王制》、《礼运》……等篇是也。
三,为提倡礼学起见,一方面讲求礼之条节,一方面推阐制礼之精意及其功用,以明礼教与人生之关系,使礼治主义能为合理的存在。此种工作,在两《戴记》中,颇有重要之发明及收获。《礼运》、《乐记》、《礼察》、《礼三本》、《大传》、《三年问》、《祭义》、《祭统》……等篇,其代表也。
四,孔子设教,惟重力行。其及门者,亲炙而受人格的感化,亦不汲汲以鹜高玄精析之论。战国以还,“求知”的学风日昌,而各派所倡理论亦日复杂。儒家受其影响,亦竞进而为哲理的或科学的研究。孟、荀之论性论名实,此其大较也。两《戴记》中亦极能表现此趋势。如《中庸》、《大学》、《本命》、《易本命》……等篇,其代表也。
五,儒家束身制行之道及其教育之理论法则,所引申阐发者亦日多,而两《戴记》荟萃之。《大学》、《学记》、《劝学》、《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及《曾子》十篇等,其代表也。
要之,欲知儒家根本思想及其蜕变之迹,则除《论语》、《孟子》、《荀子》外,最要者实为两《礼记》;而《礼记》方面较多,故足供研究资料者亦较广。但研究《礼记》时有应注意两事:
第一,《记》中所述唐虞夏商制度,大率皆儒家推度之辞,不可轻认为历史上实事。即所述周制,亦未必文、武、周公之旧,大抵属于当时一部分社会通行者半,属于儒家理想者半,宜以极谨严的态度观之。
第二,各篇所记“子曰……”、“子言之……”等文,不必尽认为孔子之言。盖战国、秦、汉间孔子已渐带有“神话性”,许多神秘的事实皆附之于孔子,立言者亦每托孔子以自重。此其一。“子”为弟子述师之通称,七十子后学者于其本师,亦可称“子”。例如《中庸》、《缁衣》……或言采自《子思子》,则篇中之“子”亦可认为指子思,不必定指孔子。此其二。即使果为孔子之言,而展转相传,亦未必无附益或失真。此其三。要之,全两部《礼记》所说,悉认为儒家言则可,认为孔子言则须审择也。
就此两点而论,《礼记》一书,未经汉以后人窜乱,诚视他书为易读,但其著作及编纂者之本身,或不免有若干之特别作用及成见,故障雾亦缘之而滋,读者仍须加一番鉴别也。
读《礼记》法
读《礼记》之人有三种:一、以治古代礼学为目的者。二、以治儒家学术思想史为目的者。三、以常识及修养应用为目的者。今分别略论其法。
以治古代礼学为目的而读《礼记》者:第一,当知《礼记》乃解释《仪礼》之书,必须与《仪礼》合读。第二,须知《周礼》晚出不可信,万不可引《周礼》以解《礼记》或难《礼记》,致自乱其系统。第三,当知《礼记》是一部乱杂的丛书,欲理清眉目,最好是分类纂钞,比较研究,略如唐魏征《类礼》、元吴澄《礼记纂言》、清江永《礼书纲目》之例。(魏征书今佚。《唐书》本传云:“征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太宗美其书,录置内府。”《谏录》载太宗诏书云:“以类相从,别为篇第。并更注解,文义粲然。”)第四,当知此丛书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代之作,其中各述所闻见所主张,自然不免矛盾,故只宜随文研索,有异同者则并存之,不可强为会通,转生。以上四义,不过随举所见;吾未尝治此学,不敢谓有心得也。居今日而治古代礼学,诚可不必;然欲研究古代社会史或宗教史者,则礼学实为极重要之研究对象,未可以为僵石而吐弃之也。
以治儒家学术思想史为目的而读《礼记》者,当略以吾前段所举之五事为范围;其条目则(一)儒家对于礼之观念,(二)儒家争辩礼节之态度及其结果,(三)儒家之理想的礼治主义及其制度,(四)礼教与哲学……等等,先标出若干门目而鸟瞰全书,综析其资料,庶可以见彼时代一家学派之真相也。
以常识或修养应用为目的而读《礼记》者,因《小戴记》四十九篇,自唐以来号为“大经”,自明以来列为“五经”之一,诵习之广,次于《诗》、,久已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其中精粹语有裨于身心修养及应事接物之用者不少,故吾辈宜宝而读之。惟其书繁重且干燥无味者过半,势不能以全读。吾故不避僭妄,为欲读者区其等第如左:
第一等,《学》、《中庸》、《学记》、《乐记》、《礼运》、《王制》;
第二等,《经解》、《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大传》、《礼器》之一部分、《祭义》之一部分;
第三等,《曲礼》之一部分、《月令》、《檀弓》之一部分;
第四等,其他。
吾愿学者于第一等诸篇精读,第二、三等摘读,第四等或竟不读可也。右有分等,吾自知为极不科学的、极不论理的、极狂妄的,吾并非对于诸篇有所轩轾。问吾以何为标准,吾亦不能回答。吾惟觉《礼记》为青年不可不读之书,而又为万不能全读之书,吾但以吾之主观的意见,设此方便耳。通人责备,不敢辞也。(右专就《小戴记》言,其《大戴》各篇则三四等居多也。)
《礼记》注释书,至今尚无出郑注、孔疏右者。若非专门研究家,则宜先读白文,有不解则参阅注疏可耳。若专治礼学,则清儒关于三《礼》之良著颇多,恕不悉举也。
《大戴礼记》因传习夙稀,旧无善注,且讹误滋多。清儒卢文弨、戴震先后校勘,始渐可读。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汪照《大戴礼记补注》,皆良著也。
附论《尔雅》
《尔雅》今列于《十三经》,陋儒竞相推挹,指为周公所作,甚可笑。其实不过秦、汉间经师诂经之文,好事者编为类书以便参检耳。其书盖本为“记百三十一篇”中之一篇或数篇,而《大戴》曾采录之,张揖《进广雅疏》所谓“《尔雅》一篇,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也。臧庸列举汉人引《尔雅》称《礼记》之文,如《白虎通·三纲六纪》篇引《礼·亲属记》,文见今《尔雅·释亲》;《孟子》“帝馆甥于贰室”,赵岐注引《礼记》,亦《释亲》文;《风俗通·声音》篇引《礼·乐记》,乃《尔雅·释乐》文;《公羊》宣十二年何休注引《礼记》,乃《尔雅·释水》文。此尤《尔雅》本在《礼记》中之明证也。自刘歆欲立古文学,征募能为《尔雅》者千余人讲论庭中,自此《礼记》中之《尔雅》篇,不知受几许挦扯附益,乃始彪然为大国,骎骎与“六艺”争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