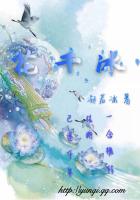想不出藏哪里更保险。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四处找地方,放哪儿都不放心。姐姐又在院子里催,让我快点,一起去西大街看看。她也急着想知道西大街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只好咬咬牙决定塞到床底下,为了防止谁钻床底往里看,我把一双没洗的臭袜子放在床边,那个臭,瞎子也能熏出眼泪来。出门前我还想看看绣球和四只小狗,姐姐等不及了,拉着我就跑。我就对着墙角的草窝吹了一声口哨,绣球听见了,对我说:“汪。”四只小狗也跟着哼了四声。
路上有人和我们一起跑。快到西大街,碰见我妈在街口跟韭菜说话,她拉着韭菜,让她晚上到我们家吃饭,韭菜甩着胳膊不愿意。姐姐说:“妈,西大街有景呢,你不去看?”
“回家,”我妈说。“有什么好看的!”
“那边到底啥事呀?急死我了。”
“太上老君下凡,”我妈有点不耐烦。“跟我回去!韭菜,听姨的话,姨拿好吃的给你。”
韭菜还是不愿意,嘟着嘴说:“看。看。我要看。”
我谨慎地说:“是不是何老头?”
我妈瞪了我一眼,“回家做饭去!”
姐姐已经拽着我跑过去了,我妈在背后喊也不停下。
猜得没错。人群围在大队部门外,踮着脚往紧闭的门里看,什么都看不到,脖子还在顽强地伸长。然后三两个人咬耳朵,表情含混,我凑上去听,只大概弄清楚,何校长被关在里面。姐姐问旁边东方他妈,东方他妈说,谁知道,听说跟丫丫有关,谁知道。姐姐还想问,周围静下来,支书吴天野走出大队部的门,挥挥手说:
“回去,都回去!有事明天说。”
人群就散了。姐姐歪着头问我:“跟丫丫有关?”
我哪知道。
丫丫就是韭菜。差不多有二十岁了。是个傻大姐,头脑不好使,见人就笑,然后问你吃过了没有。七年前她还叫丫丫,被何老头收留了才改名韭菜。叫丫丫的时候,韭菜是个孤儿,她九岁时她爸死了,接着她妈在某一天突然不见了,听说跟人跑了,再也没回来。丫丫整天在村子里晃荡,追着谁家的猫或者鹅玩,到了吃饭时间就有人叫她。那时候吴天野就是支书,他让各家轮流管丫丫的饭,只要她还活着,养到哪天算哪天。除了三顿饭,丫丫的其他事就没人管了,她整天蓬头垢面,脸脏得像个面具,下雨天也会在外面跑。后来何老头来我们这里当校长,他觉得丫丫可怜,吃百家饭却没人管,就跟吴天野说,干脆他收留丫丫吧。何老头是外乡人,听说是从北边的哪个大地方来的,一个人,一来就当校长。我爸曾说过,看人家里里外外都戴着礼帽,就是当校长的料。
丫丫被人领到何老头门前那天,何老头正坐在门口择别人送的韭菜。何老头握着一把韭菜站起来,说:“还是改个名吧,就叫韭菜。”
就叫韭菜了。叫丫丫顺嘴了的还叫丫丫,其他人叫韭菜。两天以后,丫丫就变成一个干净清丽的韭菜了,何老头帮她梳洗了一番,还给她做了两身新衣服。见过大世面的人说,丫丫满好看的嘛,跟城里来的一样。城里人长啥样我没看过,如果韭菜像城里人,我猜城里人起码得有四样东西:干净,白,好看,有新衣服穿。韭菜洗过脸竟然比我姐还白,真是。
再后来,韭菜干脆就把何老头当爸了,平常也这么叫。何老头很高兴,好像有个傻女儿挺满意的。他还教她认字,做算术题。我怀疑花一辈子也教不好,像我这样头脑一点毛病没有的,复杂一点的算术题都弄不懂,我不相信她一个傻子能明白。想也不要想。不过其他方面还是有点成效的,比如说话和看人。过去韭菜一说话就兜不住嘴,口水一个劲儿地往下挂,现在不了,总能在口水挂下来之前及时地捞回去;看人的眼神也集中了,过去你站她对面,就觉得她是在看另外两个人,而且在不同方向上,她涣散的眼神像鸡鸭鹅一样,两只眼能各管各的一边事。也就是说,现在只要韭菜老老实实不说话,就比好人还好。当然,你不能给她好吃的,一见到好吃的,她的嘴和眼立马就散了。
我们都知道何老头对韭菜好,可是东方他妈的意思是,何老头被抓跟韭菜有关。
有人喊我,一听就是大米。身后跟着三万、满桌和另外两个跟班的。“小狗长多大了?”大米问。“送我一只怎么样?”
“还小呢,”我说。其实我做不了主,小狗满月后送给谁,由我爸妈决定,绣球还没产崽就有一大堆人排着队要。我不想让大米知道我做不了主,他们会瞧不上我。
我姐说:“大米,你爸为什么把何校长抓起来?”
“问我爸去,”大米说。“关我屁事,又不是我关的。”他对屁股后头的几个挥一下手,他们就跟着他走了。他的一挥手让我羡慕不已,还有他的一声浑厚的“走”,多威风,就是跟我们小细胳膊小细腿和尖嗓子不一样。大米临走的时候又嘱咐,“记着给我留一只啊,越多越好。”
“没有了,”我只好说。
“你说什么?”
“爸妈都把它们送人了。”
“操!”大米说,“还没生下来我就要。就没了!”他扔出一颗石子,打中十米外的一棵槐树。“就一只破狗,操,不给拉倒!”
回到家,韭菜坐在厨房帮我妈烧火。烧火的时候她比正常的女孩都端庄。姐姐又问我妈,为什么把何老头抓起来?我妈白她一眼,示意韭菜在,姐姐就不敢乱问了。韭菜在我家吃的晚饭,吃了一半停下来,说:
“韭菜不吃了,爸还没吃。”
“留着呢,”我妈说。“你吃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