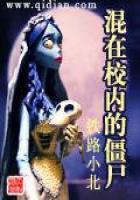有一次,它居然跳进我的空茶杯里,隔着透明的玻璃瞅我。它不怕我突然把杯口捂住。是的,我不会。
白天,它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它就在父母的再三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
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尽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它。只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趴在我的肩头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小红脚刚好给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我轻轻抬一抬肩,它没醒,睡得好熟!
还咂咂嘴,难道在做梦?
我笔尖一动,流泻下一时的感受:
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囚绿记
陆蠡
这是去年夏间的事情。
我住在北平的一家公寓里。我占据着高广不过一丈的小房间,砖铺的潮湿的地面,纸糊的墙壁和天花板,两扇木格子嵌玻璃的窗,窗上有很灵巧的纸卷帘,这在南方是少见的。
窗是朝东的。北方的夏季天亮得快,早晨五点钟左右太阳便照进我的小屋,把可畏的光线射个满室,直到十一点半才退出,令人感到炎热。这公寓里还有几间空房子,我原有选择的自由的,但我终于选定了这朝东房间,我怀着喜悦而满足的心情占有它,那是有一个小小理由。
这房间靠南的墙壁上,有一个小圆窗,直径一尺左右。
窗是圆的,却嵌着一块六角形的玻璃,并且左下角是打碎了,留下一个大孔隙,手可以随意伸进伸出。圆窗外面长着常春藤。当太阳照过它繁密的枝叶,透到我房里来的时候,便有一片绿影。我便是欢喜这片绿影才选定这房间的。当公寓里的伙计替我提了随身小提箱,领我到这房间来的时候。
我瞥见这绿影,感觉到一种喜悦,便毫不犹疑地决定下来,这样了截爽直使公寓里伙计都惊奇了。
绿色是多宝贵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乐。我怀念着绿色把我的心等焦了。我欢喜看水白,我欢喜看草绿。我疲累于灰暗的都市的天空,和黄漠的平原,我怀念着绿色,如同涸辙的鱼盼等着雨水!我急不暇择的心情即使一枝之绿也视同至宝。当我在这小房中安顿下来,我移徙小台子到圆窗下,让我的面朝墙壁和小窗。门虽是常开着,可没人来打扰我,因为在这古城中我是孤独而陌生。但我并不感到孤独。我忘记了困倦的旅程和已往的许多不快的记忆。我望着这小圆洞,绿叶和我对语。我了解自然无声的语言,正如它了解我的语言一样。
我快活地坐在我的窗前。度过了一个月,两个月,我留恋于这片绿色。我开始了解渡越沙漠者望见绿洲的欢喜,我开始了解航海的冒险家望见海面飘来花草的茎叶的欢喜。人是在自然中生长的,绿是自然的颜色。
我天天望着窗口常春藤的生长。看它怎样伸开柔软的卷须,攀住一根缘引它的绳索,或一茎枯枝;看它怎样舒开折叠着的嫩叶,渐渐变青,渐渐变老,我细细观赏它纤细的脉络,嫩牙,我以提苗助长的心情,巴不得它长得快,长得茂绿。下雨的时候,我爱它淅沥的声音,婆娑的摆舞。
忽然有一种自私的念头触动了我。我从破碎的窗口伸出手去,把两枝浆液丰富的柔条牵进我的屋子里来,教它伸长到我的书案上,让绿色和我更接近,更亲密。我拿绿色来装饰我这简陋的房间,装饰我过于抑郁的心情。我要借绿色来比喻葱茏的爱和幸福,我要借绿色来比喻猗郁的年华。我囚住这绿色如同幽囚一只小鸟,要它为我作无声的歌唱。
绿的枝条悬垂在我的案前了。它依旧伸长,依旧攀缘,依旧舒放,并且比在外边长得更快。我好像发现了一种“生的欢喜,”超过了任何种的喜悦。从前我有个时候,住在乡间的一所草屋里,地面是新铺的泥土,本除净的草根在我的床下茁出嫩绿的芽苗,蕈菌在地角上生长,我不忍加以剪除。后来一个友人一边说一边笑,替我拨去这些野草,我心里还引为可惜,倒怪他多事似的。
可是每天早晨,我起来观看这被幽囚的“绿友”时,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于一枚细叶,一茎卷须,都朝原来的方向。植物是多固执啊!它不了解我对它的爱抚,我对它的善意。我为了这永远向着阳光生长的植物不快,因为它损害了我的自尊心。可是我囚系住它,仍旧让柔弱的枝叶垂在我的案前。
它渐渐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变成柔绿,变成嫩黄;枝条变成细瘦,变成娇弱,好像病了的孩子。我渐渐不能原谅我自己的过失,把天空底下的植物移锁到暗黑的室内;我渐渐为这病损的枝叶可怜,虽则我恼怒它的固执,无亲热,我仍旧不放走它。魔念在我心中生长了。
我原是打算七月尾就回南去的。我计算着我的归期,计算这“绿囚”出牢的日子。在我离开的时候,便是它恢复自由的时候。
芦沟桥事件发生了。担心我的朋友电催我赶速南归。我不得不变更我的计划;在七月中旬,不能再留连于烽烟四逼中的旧都,火车已经断了数天,我每日须得留心开车的消息。终于在一天早晨候到了。临行时我珍重地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我把瘦典的枝叶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向它致诚意的祝福,愿它繁茂苍绿。
离开北平一年了。我怀念着我的圆窗和绿友。有一天,得重和它们见面的时候,会和我面生么?
鹰之歌
丽尼
黄昏是美丽的。我忆念着那南方的黄昏。
晚霞如同一片赤红的落叶坠到铺着黄尘的地上,斜阳之下的山冈变成了暗紫,好像是云海之中的礁石。
南方是遥远的;南方的黄昏是美丽的。
有一轮红日沐浴着在大海之彼岸;有欢笑着的海水送着夕归的渔船。
南方,遥远而美丽的!
南方是有着榕树的地方,榕树永远是垂着长须,如同一个老人安静地站立,在夕暮之中作着冗长的低语,而将千百年的过去都埋在幻想里了。
晚天是赤红的。公园如同一个废墟。鹰在赤红的天空之中盘旋,作出短促而悠远的歌唱,嘹唳地,清脆地。
鹰是我所爱的。它有着两个强健的翅膀。
鹰的歌声是嘹唳而清脆的,如同一个巨人底口在远天吹出了口哨。而当这口哨一响着的时候,我就忘却我底忧愁而感觉兴奋了。
我有过一个忧愁的故事。每一个年青的人都会有一个忧愁的故事。
南方是有着太阳和热和火焰的地方。而且,那时,我比现在年青。
那些年头!啊,那是热情的年头!我们之中,像我们这样大的年纪的人,在那样的年代,谁不曾有过热情的如同火焰一般的生活?谁不曾愿意把生命当作一把柴薪,来加强这正在燃烧的火焰?有一团火焰给人们点燃了,那么美丽地发着光辉,吸弓暗我们,使我们抛弃了一切其他的希望与幻想,而专一地投身到这火焰中来。
然而,希望,它有时比火星还容易熄灭。对于一个年青人,只须一个刹那,一整个世界就会从光明变成了黑暗。
我们曾经说过:“在火焰之中锻炼着自己”;我们曾经感觉过一切旧的渣滓都会被铲除,而由废墟之中会生长出新的生命,而且相信这一切都是不久就会成就的。
然而,当火焰苦闷地窒息于潮湿的柴草,只有浓烟可以见到的时候,一刹那间,一整个世界就变成黑暗了。
我坐在已经成了废墟的公园看着赤红的晚霞,听着嘹唳而清脆的鹰歌,然而我却如同一个没有路走的孩子,凄然地流下眼泪来了。
“一整个世界变成了黑暗;新的希望是一个艰难的生产。”
鹰在天空之中飞翔着了,伸展着两个翅膀,倾侧着,回旋着,作出了短促而悠远的歌声,如同一个信号。我凝望着鹰,想从它底歌声里听出一个珍贵的消息。
“你凝望着鹰么?”她问。
“是的,我望着鹰,”我回答。
她是我底同伴,是我三年来的一个伴侣。
“鹰真好,”她沉思地说了;“你可爱鹰?”
“我爱鹰的。”
“鹰是可爱的。鹰有两个强健的翅膀,会飞,飞得高,飞得远,能在黎明里飞,也能在黑夜里飞。你知道鹰是怎样在黑夜里飞的么?是像这样飞的,你瞧,”说着,她展开了两只修长的手臂,旋舞一般地飞着了,是飞得那么天真,飞得那么热情,使她底胜面也现出了夕阳一般的霞彩。
我欢乐底笑了,而感觉了兴奋。
然而,有一次夜晚,这年青的鹰飞了出去,就没有再看见她飞了回来。一个月以后,在一个黎明,我在那已经成了废墟的公园之中发现了她底被六个枪弹贯穿了的身体,如同一只被猎人从赤红的天空击落了下来的鹰雏,披散了毛发在那里躺着了。那正是她为我展开了手臂而热情地飞过的一块地方。
我忘却了忧愁,而变得在黑暗里感觉奋兴了。
南方是遥远的,但我忆念着那南方的黄昏。
南方是有着鹰歌唱的地方,那味峡而清脆的歌声是会使我忘却忧愁而感觉奋兴的。
草戒指
铁凝
初夏的一天,受日本友人邀请,去他家作各,并欣赏他的夫人为我表演茶道。
这位友人名叫池泽实芳,是国内一所大学的外籍教师。我说的他家,实际是他们夫妇在中国的临时寓所——大学里的专家楼。
因为不在自己的本土,茶道不免因陋就简,宾主都跪坐在一领草席上。一只电炉代替着茶道的炉具,其它器皿也属七拼八凑。但池他泽夫人的表演却是虔诚的,所有程序都一丝不苟。听池泽先生介绍,他的夫人在日本曾专门研习过茶道,对此有着独到的心得。加上她那高髻和盛装,平和宁静的姿容,顿时将我带进一个异邦独有的意境之中。那是一种祛除了杂念的瞬间专注吧,在这专注里顿悟越发嘈杂的人类气息中那稀少的质朴和空灵。我学着主人的姿态跪坐在草席上,细品杯中碧绿的香茗,想起曾经读过一篇比较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文字。那文章说,日本的茶道与中国的饮茶方式相比,更多了些拘谨和抑制,比如客人应随时牢记着礼貌,要不断称赞“好茶!好茶!”因此而少了茶与人之间那真正潇洒、自由的融合。不似中国,从文人士大夫的伴茶清谈,到平头百姓大碗茶的畅饮,可抒怀,亦可瓷肆。显然,这篇文字对日本的茶道是多了些挑剔的。
或许我因受了这文字的影响,跪坐得久了便也觉出些疲沓。是眼前一簇狗尾巴草又活泼了我的思绪,它被女主人插在一只青花瓷笔筒里。
我猜想,这狗尾巴草或许是鲜花的替代物,茶道大约是少不了鲜花的。但我又深知在我们这座城市寻找鲜花的艰难。问过女主人,她说是的,是她发现了校园里这些疯长的草,这些草便登上了大雅之堂。
一簇狗尾巴草为茶道增添了几分清新的野趣,我的。心思便不再拘泥于我跪坐的姿态和茶道的表演了,草把我引向了广阔的冀中平原……
要是你不曾在夏日的冀中平原上走过,你怎么能看见大道边、垄沟旁那些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呢?
要是你曾经在夏日的冀中平原上走过,谁能保证你就会看见大道边、垄沟旁那些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呢?
狗尾巴草,茎纤细、坚挺,叶修长,它们散漫无序地长在夏秋两季,毛茸茸的圆柱形花絮活像狗尾。那时太阳那么亮,垄沟里的水那么清,狗尾巴草在阳光下快乐地与浇地的女孩子嬉戏——摇起花穗扫她们的小腿。那些女孩子不理会草的骚扰,因为她们正批下这草穗,编结成兔子和小狗,兔子和小狗都摇晃着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也有掐掉草穗单拿草茎编戒指的,那扁细的戒指戴在手上虽不明显,但心儿开始闪烁了。
初长成的少女不再理会这狗尾巴草,她们也编戒指,拿麦秆。麦收过后,遍地都是这耀眼的麦秆,麦秆的正道是被当地人用来编草帽辫的。常说“一顶草帽三丈三”,说的即是缝制一顶草帽所需草帽的长度。
那时的乡村,各式的会议真多。姑娘们总是这些会议热烈的响应者,或许只有会议才是她们自由交际的好去处。那机会,村里的男青年自然也不愿错过。姑娘们刻意打扮过自己,胳肢窝里夹着一束束念黄的麦秆。但她们大都不是匆匆赶制草帽辫儿,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们编制的便是这草戒指。麦秆在手上跳跃,手下花样翻新:棱形花结的,字花结的,扭结而成的“雕”花……编完,套上手指,把手伸出来,或互相夸奖,或互相贬低。这伸出去的手,这夸奖,这贬低,也许只为着对不远处那些男青年的提醒。于是无缘无故的笑声响起来,引出主持会议者的大声呵斥。但笑声总会再起的,因为姑娘们手上总有翻新的花样,不远处总有蹲着站着的男青年。
那麦秆编就的戒指,便是少女身上惟一的饰物了。但那一双双不拾闭的粗手,却因了这草戒指,变得秀气而有灵性,释放出女性的温馨。
戴戒指,每个民族自有其详尽、细致的规则吧。但千变万化,总离不开与婚姻的关联。惟有这草戒指,任凭少女们随心所欲地佩戴。无人在乎那戴法犯了哪一条禁忌,比如闺中女子把戒指戴成了已婚状,已婚的戒指戴成了求婚状什么的,这里是个戒指的自由王国。会散了,你还会看见一个个草圈儿在黄土地上跳跃——一根草呗。
少女们更大了,大到了出嫁的岁数。只待这时,她们才丢下这麦秆、这这草帽辫儿、这戒指,收拾起心思,想着如何同送彩礼的男方“嚼清’——讨价还价。冀中的日子并不丰腴,那看来缺少风度的“嚼清”
就显得格外重要。她们会为彩礼中缺少两斤毛线而在炕上打滚儿——倘若此时不要下那毛线,婚后当男人操持起一家的日子,还会有买线的闲钱么?她们会为彩礼中短了一双皮鞋面嚎陶,倘若此时不要下那鞋,当婚后她们自己做了母亲,还会生出为自己买鞋的打算么?于是她们就在声声“嚼清”中变作了新娘,于是那新娘很快就敢于赤裸着上身站在街口喊男人吃饭了。她们露出那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臂膀,也露出那从未晒过太阳的雪白的胸脯。
那草戒指使在她们手上永远地消失了,她们的手中已有新的活计,比如婴儿的兜肚,比如男人的大鞋底子……
她们的男人,随了社会的变革,或许会生出变革自己生活的热望;他们当中,靠了智慧和力气组有所获者也越来越多。日子渐渐地好起来,他们不再是当初那连毛线和皮鞋都险些拿不出手的新郎官,他们甚至有能力给乡间的妻子买一枚金的戒指。他们听首饰店的营业员讲着18K、24K什么的,于是乡间的妻子们也懂得了18K、24K什么的。只有她们那突然就长成了的女儿们,仍旧不厌其烦地重复母亲从前的游戏。
夏回来临,在垄沟旁,在树荫里,在麦场上,她们依然用麦秆、用狗尾巴草编戒指;棱形花结的。字花结的,还有那扭结而成的“雕”花。
她们依然愿意当着男人的面伸出一只戴着草戒指的手。
却原来,草是可以代替真金的,真金实在代替不了草。精密天平可以称出一只真金戒指的分量,哪里又有能够称出草戒指真正分量的衡具呢?
却原来,延续着女孩子丝丝真心的并不是黄金,而是草。
在池泽夫人的茶道中,我越发觉出眼前这束狗尾巴草的可贵了。难道它不可以替代茶道中的鲜花么?它替代着鲜花,你只觉得眼前的一切更神圣,因为这世上实在没有一种东西来替代草了。
一定是全世界的女人都看重了草吧,草才不可被替代了。
傅雷家书
傅雷
一九六○年一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