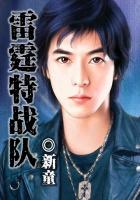人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就这样两年后,我又怀上了一个儿子。
我们给他起名为铭明,因为那时,我感觉他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的生活。
铭明被小心地呵护着,我们不愿让他再参与军队事物,哪怕是从政。他照着我们的安排,活的单纯快乐。
直到有一天,设计般的,他进入了托尼的训练基地,灰沉的天空下同龄人扭曲的神色深深地映入他的脑海,死一般的寂静中偶尔爆发出不甘的哭喊,泪水与血水交织在一起。
在劝说父亲无效后,年仅七岁的铭明不知用了什么方法集结了一只军队,利用他出入便利的身份,打开了训练场的大门,致使三分之二的受训者流失。而这些受训者又将训练内情公之于众,托尼名声大败,不得不屈居刚刚提官至将军本和他平起平坐的无面之下。
让事情更加不控的是,铭明人间蒸发似的消失了。我动用了所有力量找他,发现所有线索都中断在卡尔得拉,无法跟进分毫。
铭明的消失让我重新审视自己。
我发现失去了兰的我变得冷血无情,变得暴戾,变得已经看不见这个世界的真实与美。
我发现我的心已经被复仇给蒙蔽了。
我失去了女儿,却硬生生把七岁的儿子也给逼上了绝路。我错了,然而一切已经无法挽回。
失去铭明更加激怒了托尼,他变得更加善怒,更加残忍,他嚷嚷着要让所有人付出代价,他还要加强训练营的强度。
付出代价的,难道不是自己吗?丧失了爱与快乐的能力,站在痛与恨的边缘。
我好累。
我请求托尼放手。他深深看我一眼,没有挽留。
收拾了行囊,轻简上路。我打算先去卡尔得拉看一眼,然后回动车组干自己的老本行。
然而在出发的第二天,就收到了自己的死讯。正在逛书店的我听到广播里的消息时大惊失色,开什么国际玩笑,我好端端地站在这里呢。
转念一想,又明白了托尼的意图。
真是绝啊,像这样把一个人永远得逼出自己的生活,永远得忘掉她,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没有软肋的人。
我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纵容他。然后默默地易容改貌,成为了现在的任博士,专心专研医学。
我走之后,托尼又干出许多业绩,也曾多次反超无面,风光无限。随着年龄增大,他让位于无面,退居幕后。他训练营中的孩子逐渐进入各个机关部门,实际上,他还是那个消息最灵通的最大的赢家。
我以为我会就这样看着他,然后平静无波地过完自己的一生。
直到几年前,这个孩子进入了我的视线。她叫若兰,但她浑身上下都是小兰的影子。
我不知道托尼为什么选择把若兰这样送过来。但当我得知若兰这样的生活之后,内心潜藏多年的愤恨像干柴遇到烈火一样被点着。
我决定不再容忍,我决定结束这一开始就错误的一切。
后面的行为你也知道了。
故事讲到这里,任博士住了嘴,对林让扯出一缕疲惫的微笑。
林让默默得点点头,沉声道:“任博士,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托尼将军就是想让你为他的一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你说什么?”任博士的脸色骤变,几十秒后,她的神情慢慢放松,哑然失笑,“真是不吃亏的性格。”
“任博士,您的儿子,我会尽全力帮您找到。”林让深鞠一躬,转身离开。
若兰心不在焉地问道:“他要去哪里?”
任博士温和地笑了笑:“去找真正伤害林黎的人。”
邓皓合上了翻阅半个晚上的卷宗。
邓囸完成了改良枪支的最后一步制作。
于杰冷冷地挂断了电话。
林让的背景消失在黑暗中。
托尼府的警报声终于停止。
动荡的夜晚又重新回归平静,仿佛像一面幽深的湖水,你从来无法知道接下来等待你的,是什么。
遥远的边境,一颗流星划过天际,陡峭的三崖之上,寒风呼啸。一个青年抬起了头,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默默地,他攥紧了手中的剑。
旁边的侍卫恭敬地说:“大人,您决定出征了吗?”
青年没有答话,只是重重地拍了拍侍卫的肩头。
那一瞬间,病床上林黎的眉头轻轻皱了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