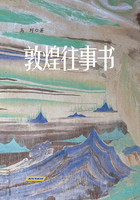樊娴都的身心已经非常的虚弱,看着百事缠身的儿子们能赶回来看望自己一眼,就已知足了,嘴角处随即掠过了一丝心满意足的微笑。但瞬息间,她那忧闷的脸上又阴云密布了。此刻,她的心里很清楚,也知道儿子们眼下的处境,更意识到刘家将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折,而这个转折,非同寻常,要么青云直上,要么万劫不复。把握这个转折的,就是自己眼前的儿子们,她不能因为自己而分了他们的心。
樊娴都那一如往常柔和坚毅的目光,逐个在儿女和跪倒在地的宗室子弟们的身上注视片刻后,随之,抖动着嘴唇,微弱的声音说道:
“缤儿,举大事要紧,你怎么来了?”
刘寅忙哭着安慰道:“娘,您老放心,孩儿把一切都布置好了。您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刘秀、刘仲、刘黄、刘元、伯姬也一齐围上来,跪伏在母亲的身边哭泣声声。
樊娴都把六个儿女逐一打量了一遍,精神似乎好了些,脸上绽出几丝笑意道:“娘的路走到头了,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你们都能平平安安地过上一辈子。伯姬也长大了,娘却来不及给她找个人家,秀儿——”
刘秀含泪应道:“娘,孩儿听着呢!”
樊娴都缓了口气,接着说道:“你大哥一心想着大事,伯姬的事娘就交给你了,记住,一定要给她找个称心如意的人家。”
刘秀抹了一把眼泪说:“娘,您放心,孩儿一定会办到。”
樊娴都呼吸渐急,声音越来越低,但她还是尽量抬高点声音说:“你们都起来,都,起来,人常说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咱们刘家不能和别人比,你们也别学人家孩子悲悲切切的。你们能来看娘,娘已经很是满足了。娘心里也明白,你们可都是成大器的,千万别因为家里的琐事影响了前途,若是那样,见了你爹,他会责怪我的。你们都给我起来,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再不起来我可要真的生气了!都起来,起,起——”樊娴都有气无力地喘息着说不下去了。
“娘,您可千万别这样说,真真是折煞我们了!”刘寅带着哭腔说,“我爹在世时,整天忙于官衙里的事,是您把我们养育成人,要是没有您多年来的教诲,我们兄弟哪能有半点出息?现如今我们大了,却只顾忙活自己的事,都把娘您给忘了。娘,您打不了,就骂我们几句吧!”
“是啊,娘——”刘秀不忍再听娘和大哥说下去,强忍着眼泪说,“娘,您和大哥说的,都有道理,我们如此的付出,不但要复兴汉室,使国泰民安,也要完成我爹多年兴复汉室让天下人太平的夙愿,这都是我们做儿女的应该做的。可这话又说回来,不管找什么样的借口,总之是我们不孝,只顾顺着外边,竟没能为您分半点心,反倒要您为我们担忧。娘,我们没有尽到做儿女的义务,您还是骂我们几句,我们心里会痛快点儿!”
刘寅、刘秀的话让大家更伤心了,全家人全都跪在床前,顿时又哭声一片。
樊娴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朦胧地打量了众儿女一番,分外平静地嘱咐说:“缤儿,自古忠孝难两全,我走后,你就是咱刘家的一家之主了,要以大事为重,丧事不必亲临,不为不孝。儿的事情多着呢,不但家要管好,而且兄弟姊妹们日后的生活,也全要靠你来张罗啦,知道吗?还有,你爹临死前说过,你性情不够柔韧,容易招来灾祸。以后要提防小人暗算。这样,我和你爹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安心了。瞧,说你爹,你爹可来接我了,娘该走了,跟你爹一起走了,走了,走了——”
刘寅兄妹听娘说出了这样的话,知道是娘的大限将临了,更知道这是娘在临离开这个人世间,所做的最后的遗嘱了,哀痛之情愈抑愈强。就在大家悲痛的泪水模糊双眼时,樊娴都轻轻地合上了双眼,安详地离开了这个纷乱无常的人世。
“娘!”
一声长号,窗外瑟瑟风起,万木败落,树叶飘零。
“娘!”
悲泣声声,刘寅如万箭穿心的难受。
刘寅兄妹跪在母亲的遗体前,悲痛欲绝,泪如雨下。身后的宗族子弟、宾客豪杰也跪倒在地,哽声泣泣。刘府上下,顿时哀声一片。
正当众人沉浸在万分哀痛时分,新市兵和平林兵同时派出联络人员赶到舂陵,在这战事非常紧迫的时刻,大家不得不紧锣密鼓地匆忙张罗樊娴都的丧事。
临时搭建的灵堂前,刘寅、刘仲、刘秀、刘黄、刘元、刘伯姬几个兄弟姐妹,长久地跪立着,几天来的悲痛,已经使大家欲哭无泪,欲言无语,默默地回顾着母子亲情的历历往事。
站在近旁的樊宏踟蹰不安地倒背着双手来回踱步,姐姐的谢世,他自然是悲伤万分,可眼下的时局已到了剑拔弩张之势,几个外甥却一个比一个悲哀,他本想劝阻他们节哀顺变,可又不忍心打扰他们那份诚挚的孝心。刘寅第一次与新市兵、平林兵合作,如果因丧事突然变卦,有何信义可言?
正在樊宏焦虑不定时,一个士兵跑入灵堂内,先跪在刘寅身后,郑重地给太夫人施一大礼,随即小心翼翼地在刘寅耳边禀报:“将军,新市兵、平林兵都派人前来报信,说他们大军已经向新军军营移动,请将军如约带兵前去接应。将军是否——”
正悲哀得无精打采的刘寅闻听此言,登时来了精神,霍的一下子站起身子,双目圆睁的瞪了那士兵一眼,迅即又通的一声跪倒在地,咽回了他那即将出口的话。
紧挨刘寅身边的刘秀,对士兵的话听得一清二楚,也紧跟着刘寅同时跳了起来。但他没有跟着跪下,仍站在那里没动,目光热切地盯着大哥,静静地等着他发号施令。但刘寅双拳紧握,咬牙沉思,犹豫不决,像是对周围的人,又像是自言自语地缓缓说道:
“娘亲为我们兄妹辛苦了一辈子,特别是近来,闹腾着起事,害得她老人家也跟着我们担惊受怕的,临了也没享上一天福。按说,咱们应该守孝三年才是,守孝期间是不齿腥不杀生的。即便是眼下的形势再紧迫,再危急也不能把娘扔下来不管吧?”
刘寅的眼泪随着他对娘的愧疚之情喷涌而出,周围的人更是悲声不断,刘秀的心也被大哥的话说软了,再一次跪在地上陪着他落泪。
此景此情,让站在一旁的樊宏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作为娘舅,他知道,现在只有他,也只有他的话他们才能听进去。
为此,樊宏按捺不住满腹的激愤,大踏步地走到刘寅跟前,厉声呵斥道:“缤儿,没想到你竟然这么的糊涂啊!你娘临死时的话全被你当了耳旁风了,现在该拿主见的时候了,你却无动于衷,你娘算是白养育了你一场,太让舅舅失望了!”
“舅舅——”
“不要喊我舅舅!”樊宏打断刘寅的话说,“大战在即,你也不想想孰轻孰重,不要儿女情长,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你方才说了,你娘这些日子担惊受怕,她怕什么?还不是怕你们成不了大事,怕你们眼下干的事能不能成功!怕你犯糊涂误了大事。你犯糊涂不要紧,可这么多将士的性命都掌握在你的手上啊!你有娘,他们难道就没有娘了吗?你为你娘尽孝耽误了大事,他们就得因此而丢命!你想过没有,他们的娘到时候是个什么心情?”
“舅舅,我——”
樊宏根本不给刘寅辩解的机会,再一次打断他的插话,但当樊宏发现刘寅在自己凌厉的训斥下,面红耳赤地低下了头,这才感觉到对他指责得有点太过分了。心想,人家好坏也是统帅舂陵兵的将军,总得给留点面子吧,随即便缓和了一下语气说:
“你娘的丧事,你们兄弟不必操心,一切由我和你叔父代办吧。我想,九泉之下,你娘一定能谅解你们,不但谅解,还会高兴的!”
樊宏的这般训教,不但让刘寅口服心服,而且仿佛被舅舅狠狠地掴了两耳光似的,从里到外火辣辣的难受。刘秀突然站起,一抹眼泪,向身后的众人说道:“诸位请起,大战在即,不必哭泣,所谓大行不拘细节。此去征战,旗开得胜,匡复汉室帝业,再筑宗庙,才可告慰亡父母在天之灵。”
刘寅闻言,顿时醒悟,忙擦干泪水,站起来说:“三弟所言极是,母亲也有遗嘱,不会怪儿女不孝。丧事就交由叔父、舅父办理,其余人等,随本柱天都部出征。”
刘良、樊宏虽然心里也非常难受,但刘寅的阵前命令,不能不让他俩精神为之一振,二人同时接口答道:“刘良、樊宏遵命行事。”
其余宗族子弟、宾客豪杰也都站起身来随刘寅往外跑,刘秀兄弟也紧随其后,临出灵棚时,刘寅带头,兄弟几人向刘良、樊宏作了长长一揖,异口同声地说:
“一切拜托叔父、舅舅了!”
樊宏这才赞许地点了点头,恢复了往日的慈祥,挥挥手催促道:
“去吧,去吧!”
听着渐趋渐远的马蹄声和扬鞭声,樊宏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身站到姐姐的灵柩前,再也抑制不住的悲泪滚腮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