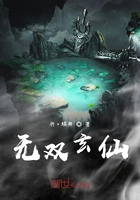晏念始终在被梦魇纠缠,介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但仍保有某种模糊的意识,他感到浑身灼热,四周影影绰绰,仿佛很多人正在他身畔忙碌,他试着睁开眼,可随即又放弃了,他感到自己正被一股莫名的恐惧笼罩,他想发出声音,但却无能为力,就像他的灵魂正被困于一副并不属于他的躯壳。
直至一阵沁入心脾的凉意忽然栖上他额头,舒适的感觉逐渐蔓延全身,是妙悟的灵药?他想着,想着,又再次屈服于汹涌的睡意。
不知过去多久,晏念从一片漆黑中苏醒,他反复眨眼,想让它们尽快适应正笼罩他的黑暗,可双耳却忽然捕捉到某种细微的声响,像是阒然的、湿漉漉的触碰,他试着挪动身体,才发觉自己深陷于绷带的纠缠,而声音仿若来自胁下的创口,并且随着触碰,还有恍惚的暖意传来。
“晏黎?”阴沉的晦色让他不自觉压低声音,或许是晏黎,正为他处理伤势,他想,他的眼睛已开始适应黑暗,“这是在哪?”他生涩地问。
没有人回应,周围依旧岑寂,除了某个幽邃的角落传来如回音般轻微的震颤,除了湿漉漉的令人不安的声音之外,没有人回应。
晏念感到惶惑、焦虑,就在此时,一缕暗淡的光线骤然投射进来,堆积于窗畔的阴霾瞬间被驱散了,幽蓝的光泽填满了原本属于黑暗的领地,晏念松口气,“晏黎?”他再次小声呼唤,然后侧过头,试图看清为自己处理伤势的人。
可是,在接下来的瞬间,晏念被前所未有的恐惧迎头痛击,头皮恍若被整块剥离般麻木到毫无知觉,他的耳膜在嗡嗡作响,他禁不住惊呼,不顾一起想挣扎起身,因为在他面前,在咫尺之内,幽蓝的光泽勾勒出一副清晰的轮廓,赫然是一头生着棕色鬓毛的巨大赤鹿,它的犄角如坚硬的荆棘般杂乱的竖立着,每一处分叉都生着畸形的骨痂,此时它正昂着头颅,向晏念露出诡谲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以及丛生的、骇人的獠牙。
晏念不顾一切地挣扎、呐喊着,试图远离正在****他伤口、吮吸他鲜血的怪物,可他的努力只是徒劳,因为他的身躯被厚厚的绷带纠缠着,并且愈陷愈深。
就在一筹莫展时,怪物却像忽然感知他的心意般开始缓缓后退,晏念已浑身虚脱,但仍在向四周摸索,试图寻找能用以防身的利器,巨大的恐惧让他不敢把注意从怪物身上移开,直至他的余光恍然察觉到某种耀目的光,正从他背后逐渐隐现。
静谧的光芒驱散了盘桓于室内的黑暗,让晏念感到温暖平和,他恍惚感到那正是令怪物退去的原因,于是他缓缓转身,试图一窥光芒的真容,然而他却亲见了自己的脸庞,亲见了那张惶恐、苍白的脸,他们彼此凝视,可这幅诡谲的景象却并未让他感到惊惶,没有畏怯,反而是前所未有的安宁,因为在那张再熟悉不过的脸庞之下,在他的背上,此时正逐渐呈现一幅被烟雨晕染的卷帙,描摹着淡而朦胧的纹路,却绽放出夺目的光辉。
翌日,晏念伴着晨曦苏醒,随即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一个长长的梦境,山间的拂晓安静的恍若时间都停滞,他掀去盖在身上的粗布棉被,发现自己胁下的伤口已被悉心处理过。
不是敌人?
他恍惚记起自己在失去意识前,高大的鲜卑武者曾这样疑问,他松口气,自己还活着并且被照顾得很好,所以他们很安全,因为善待俘虏从不是鲜卑的传统。
楼下隐约传来晏黎与苏妙悟的对话声,他猜测自己正在驿站二层的卧房中,于是嘴角浮现出释怀的笑意,尽管昏睡带来的混沌感依旧如一头暴躁的野兽般盘踞在他大脑深处,他从床榻上费力起身,之后四处打量:墙角倚着两三件农具,缺了边的陶罐仿佛高矮不一的守卫,两柄锻造粗劣的长矛横躺着,颀长的刃尖被岁月侵蚀,现出斑驳的锈迹,地板铺着厚厚的用以保暖的茅草,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霉味,与他睡过的床榻毗邻,还有七八副拾掇整齐的铺盖,驿站的内部显然比他之前所想象更加宽敞。
经过短暂休整,晏念缓缓起身向窗畔走去,虚掩的窗扇被一张残破的野猪皮遮去大半,向下俯瞰,窗外笼罩着苍茫的雾气,浓郁的让人误以为天上的云床正在大地休憩,阴沉的天色与昨时的和煦恍如隔世,不远处稀落的灌木因晨间霜冻而凝上一层细小的冰晶,此时纷纷垂下头,露出荒芜的地面。
晏念深吸一口气,让冰冷的空气直彻入肺腑,之后又长长吐出,再眼睁睁看它化成苍白的雾霭,他曾在那片荒芜的地面上与人以命相搏,如今他活了下来,晏黎与苏妙悟似乎也安然无恙,他因此而庆幸,并且有了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哥哥!”
晏黎在他背后轻声呼唤着,晏念在她声音中同时听出欣喜与疲惫两种情愫,他转过身,向她报以蕴满暖意的微笑,之后她小心翼翼走上前,轻轻拥住晏念并把脸贴上他的胸口。
他们一起下楼,昨日相遇的鲜卑武者在黎明前就离开了,经过主人热忱的自我介绍,晏念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座荒废已久的驿站,如今只剩两位希冀远离人烟的花甲老人在此寄住,而与他交谈的男主人正是驿站昔时的驻兵,他蓄着花白卷曲的胡须,肩上披着一件由兽皮拼接成的破旧大氅,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
年迈的夫妇在这片被山野环绕又鲜有人迹的山间相互护持,安享了几年平静生活,也迎来一批又一批过客,其中大部分人都向他们表示友好,也包括昨日那些隐去身份的鲜卑武者。
晏念向四周打量,驿站一层是足以容纳数十人的宽阔开间,十几张低矮的桌案杂乱无序地摆放着,地面与二层一样铺着厚厚的茅草,只在正中生着炭火的地方裸露出一片粗糙的石造地面,此时驿站的另一位主人——一位头发花白、身子略微佝偻的老妪正在火盆旁忙碌,不时用怯懦的余光偷偷瞄他。
“若不是战乱...”男主人搓着手,用沙哑的声音说道,“若不是因为战乱,这里本应是通往徐州的捷径,本应繁华、热络...可现在的王恨不得竖起高墙,把建业,把江南都像包粽子般裹得严实...”他凝望着驿站前蜿蜒的道路,恍若陷入沉思。
唉,晏念随着老人发出叹息,他望着他浑浊的双眼欲言又止,若不是因为战乱...今时,将是何时,而此处,或许也会从一座破陋的建筑发展成一座繁盛的村镇,就像赤崖堡那样。
“昨日那些武者...”他忍不住问。
“那些人啊,”老人忽然一扫愁容,敦厚地笑了起来,“是不是看着凶神恶煞的?”他把一枚干枯的草叶丢进嘴中咀嚼。
“嗯,是挺凶恶的,”晏念含糊地应着,“他们是过路客?”
“昂,是呢,说是从北地过来,要去江南,”老人回答,“他们自己猎了野物,只是借宿两宿,对我们两个老东西倒很谦和。”他说着瞧一眼正在炭火旁忙碌的婆娘,眼神中充满温柔,“怎么说呢,看着凶恶,却不是恶人,反倒是那些同宗的流民啊...”
老人的语气倏然变得愤懑,原本交叉在一起的枯槁手指也开始颤抖,“算了,这把年纪,什么都经历过了,还能学不会包容?”他以一声长叹做了结束,之后就没再说下去,可是晏念已了然于心,并且感到五味杂陈,伪善不如积恶,披着弱者外衣的恶人往往更加残忍,因为他们被生计所迫,已露出本性,露出獠牙。
“哥哥,是那些武者为你包扎的伤口,”晏黎在一旁插话道,此时她正与苏妙悟并排坐在黑匣上,“他们懂得医术,看着不像坏人。”
“那不是医术,”苏妙悟纠正道,“是急救术,想必他们是行军之人。”
晏念点点头,这场错误的争端只是因为三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于错误的地点,才招致怒火。
“他们的首领建议我们改走水路,”苏妙悟枕着自己的臂膀,向后倚在木墙上,悠然自得地说:“他说啊,在三月开春前,沿海的季风会一直向北吹拂,所以此时水路最适宜北上,”他忽然沉吟起来,“我们早该想到的。”
“早该想到的!”晏黎在他身旁吐着舌头学他说话,“苏哥哥,你早该想到的事情太多了。”
“凡事皆因果,”苏妙悟略略一怔,接着又煞有介事地说:“有些事只可悟,不可说,不然何来今时因缘?”
然而晏黎压根没有接他话的意思,“哥哥,”她自顾自对晏念说:“武者的首领好生威武。”
“只是过于沉默寡言,”苏妙悟说,“如果...”
“如果争执起来,说不定,连元茂大叔都不是对手...”晏黎再次打断苏妙悟,此前她一直认为乞活军中徐元茂是她毕生所见最孔武善战的人,“而且,还很俊秀,”她痴痴地说,“他的气质像我之前给你讲的谢千钦。”
“他们的首领,不是持双戟的武者?”晏念有些疑惑,毕竟那张黝黑的脸与俊秀相差甚远。
“不是,不是,”晏黎不住摆手,“他们的首领始终在木屋中饮酒,就在那张桌上,”她指着紧靠墙角的一张桌案说,“他散着长发,默然不语,身畔竖着一柄,一柄...”她忽然开始左顾右盼,像在寻找比对物,当她的目光落在苏妙悟身上时,瞳眸中又骤然亮起光彩,“一柄,像苏哥哥那么长的刀!”
“胡说!”苏妙悟气鼓鼓地反驳道,“我有那么短?”
“差不多吧,差不多,”晏黎捂着嘴讥笑他,“只是,他有些忧郁...”她忽又陷入黯然。
“黎儿,总有些苦痛的经历,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对我们所知的人,刻下了我们无法想象的伤痕。”晏念说。
“哦...”晏黎似懂非懂地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