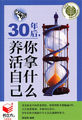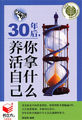从舞厅里出来,已是子夜。
看到街上飘荡着一阵阵墨色的余烬,我陡然记起今天是清明。
我的心里一下子潮湿得透不过气来。有一种力量要将我按倒在地,让我跪下。我知道我是情愿的,但我始终没有跪下,因为我站在城市的柏油路上,膝盖没有着落。
原来农历于城市是一种别扭,一种尴尬。
农历拿城市有什么办法呢?城市在农历的喂养下长大,却将农历丢在脑后,正如晋文公重耳被介子推胯上的肉解救,后却将介子推忘掉一样。尽管城市不是故意的。
城市里生长的是情人节、狂欢节什么的。
但我的心里明明已经跪下,这说明我是一个城市边缘人。
我不知道我故去的祖辈回家时发现我不在,又一看我正在灯光迷离的舞厅轻歌曼舞时会伤心成什么样子。我不由想起小时候一天在外边疯玩,妈妈叫也不回去,直到被奶奶揪了耳朵。炕桌上是让人一下子忘乎所以的香喷喷的米面。我眼里金光四射嘴里发出咂吧咂吧的声音,奶奶笑着问:“今天是啥日子啊?”我说:“吃长面的日子啊。”全家人都笑了。“你小子咋记得呢,你肚子没疼咋记得呢?”娘有点嗔怪地说。
原来桌上一年难得一次的长面,竟是为自己的生日而做。即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母亲他们也没有忘记纪念和祝福。
可是自己却忘了,而且是在清明。虽然单位比较忙,虽说离家比较远,但回趟家不是说不可能,即便回不了家,也起码在相约的时间借了星月风尘给他们道个安问个好,最起码舞厅是不该去了。
清明的巴掌好重,我被扇了一个趔趄。看着在城市的马路上飘荡的余烬,我想,眼下啥都涨价了,我不知道奶奶他们从老家里拿走的盘缠够不够花,倘若不够呢?也不知道他们的屋子是否漏雨,倘若漏了呢?更不知不久前才搬去的娘是否住得惯。走时她的腿疼得正紧,也不知在那边找到找不到郎中。就算找到,又能不能看得起我的工资刚刚发到手,但是又如何赶得上他们的车?像老家那样划地做帐头烧一包冥纸,也是枉然。因为奶奶的眼睛不好,娘的腿不好而城市又是这么车水马龙纸醉金迷的。
小时候,每当清明,父亲总要领了我们弟兄去坟院里望祖上。送去些清茶淡酒,整修一下屋子,还要挂好多好多纸条。看着一坟院白色的纸条在风里舞动,我就觉得有种亲情也在风里飘啊飘的。
再看那些没人光顾的荒坟时,就为自己感动一路,心想延续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这时,父亲往往会说,你们去给那几个坟头也烧些纸,挂些纸。我们就觉得父亲很伟大很伟大。同时有种布施的优越感,简直都将我的脚心搔痒了。
而这些,已有多少年没有做了呢?我只觉得心被扯成一缕缕呼啦啦作响的白纸条。就这样怅立在城市的夜色里,我不知该怎样收拾自己的心事。
清明已经错过,就连眼泪也追不上,何况风还是逆吹着,正好和心事相反。
伤心打落了我最后一滴清泪,但是无法打落我回望故乡的姿势。
有歌声随风飘来,听得出是《这个城市流行一种痛》。
蓦然,我发现,清明,原来是一笔债。
城市的楼房越来越多,郊区的田野越来越少,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物质的欲望越来越高,为了自己能更好地适应城市节奏,也为了体现自己的才能、价值,我们不遗余力地周旋于三教九流之中,可是唯独把最疼爱自己的亲人冷落在一旁。当有一天,为这奔波的城市生活感到疲倦时,可是亲人已经远离了我们。在这无处烧冥钱的城市清明节,除了内疚,还是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