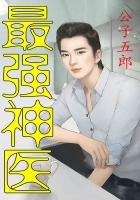顺治九年(1652年),黄富强十七岁的大儿子大龙和陈大兴十六岁的丫头金枝订婚的日子,选在了五月初三。
因为双方两家是姑舅亲,两家的大人和孩子都特别熟悉,就减少了那些过多的讲究,敖大寡妇就算男方黄家的媒人,陈大旺就成了女方陈家的媒人。这两个媒人,没有一点为难事,只不过就算起了一个来回传话的作用。
四月二十八那天上午,敖大寡妇骑着自己家的毛驴,带着黄富强家的彩礼,去了苇子峪。她没有直接去大兴家,而是先到了大旺家,说:“姑舅哥们做亲家,也需要当媒人的过彩礼,那应该咱俩一起去。我当了这些年媒人了,就数这门亲事最省心,话都不用多说。还是遇到了好世道,更是遇到了好人家啊!”
遇见敖大寡妇的乡里乡亲也都说:“黄、陈两家,那才是根本人家啊,门当户对,一点不差。大龙这个小伙子和金枝这个姑娘,十里八村也少见的,郎才女貌,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
“最近这十来年,天下太平了,咱们这里的庄稼人的日子好过多了。尤其是黄富强家,更是兴州一带三里五村的头等户,要房有房,要粮有粮,要钱有钱。别说给一个儿子说媳妇,就是一下把三个儿子的媳妇都娶到家,也不会嘬瘪子。”
媒人把彩礼过了,女方家里同意了,男方家里开始请人,准备酒菜。
老黄家把三里五村的亲戚和本村的一家不落,都登门去请,到日子来喝喜酒。
订婚那天,摆了十二桌。陈家来的人,都坐在东西两个堂屋的炕桌上,黄家的亲戚对应着作陪。本村和邻村来喝喜酒的人们,都在院子搭的席棚子里,坐好了。订婚仪式的司仪,当地叫“瓢把子”,理所当然地由威信最高、关系最好的皇粮庄头余道宽担任。
道宽在前前后后地张罗着。他看新亲和来宾已经围坐好了,开始主持了:“各位新亲老亲,各位街坊邻居,各位亲门近支,大家静一静!我宣布:黄大龙和陈金枝的订婚仪式开始!俗话说,天下无媒不成亲,首先有请两位媒人坐到上手来!”
两位媒人,面对大家,鞠了一躬,就把两个孩子家里准备的定亲信物,当众交给了经理,经理又按程序递给了两个孩子。然后,大龙给金枝戴上了那个玉镯子;金枝有点羞答答地掏出了一块绣着大花的手绢,低着头、抿着嘴、红着脸,塞给了大龙。互相交换了定亲信物,就该认亲改嘴了。
这“改嘴”,就是订婚仪式上,改变对未来公公婆婆和新郎亲戚的称呼。
首先,是富强两口子出场。金枝给黄富强装了一袋烟,点着了,又拿起茶壶,往茶碗里倒了水,端过来,不好意思地叫了一声:“爸爸,您喝水。”
“哈哈哈哈,姑舅二大爷,现在当爸爸了!”富强从衣服兜里,掏出了一个红包,递给了金枝,“金枝,拿着买头绳吧!”
金枝不像刚才那样不好意思了,她给大芍药倒了一碗茶,说:“妈,您喝水。”接着又拿了一块芝麻蜜糖递到了嘴边,还给她塞到了嘴里。大芍药乐呵呵地塞给金枝一个红包:“今天这块糖,就是甜啊!来,金枝,妈给你这俩小钱,留着买粉胭脂擦吧。”
大龙的大爷、大娘,舅舅、舅妈和近支的长辈,都乐呵呵地按顺序一一地走过来。金枝给抽烟的装一袋烟划火点着了,不抽烟的倒一碗茶水。大龙叫人家什么称谓,金枝就随着叫一遍。
认完亲了,改完“嘴”了,道宽说:“陈家把金枝养育这么大,也不容易,今天订婚了,眼看就要是黄家的人了。这二十两银子,是东家给金枝爸妈的养育费,是一点心意。”
说着,道宽把红布钱袋交给了男方媒人大旺。大旺转身递给了哥哥。
大兴急了,坚决不要:“彩礼早就过了,怎么还给这么多钱呢?我们没有那个讲究,我不能要啊!”
富强说话了:“我们虽然是姑舅哥们,但只是一门子亲戚,这回亲上加亲了,我们哥俩又成了亲家,不是更近一层了吗?那是咱们哥们的近便钱,也是改口钱啊,你必须拿着!别的不用说了。”
道宽敞开了嗓子,高声喊道:“订婚仪式到此礼成!下面,我宣布:厨房发菜,支桌就位,卖酒撒壶,油盘压桌——”
“油着——慢回身——”四个端油盘的小伙子,扯着长腔,耍着怪脸,快步如飞地开始走菜了。
北方农村典型的二八席,不一会儿就摆满了一大桌子。亲戚好街坊邻居们开怀畅饮,喜笑颜开。
忙忙碌碌的一年转眼就过去了,在收秋之前的八月初五,富强请来了敖大寡妇和大哥,还有道宽,一边吃着晚饭,一边说:“我和大芍药想八月十六给大龙和金枝结婚,和你们几位商量商量。如果你们看着行,还得麻烦嫂子跑一趟,替我去下四合礼。”
敖大寡妇快言快语:“这都是现成的事,我明天就去下四合礼,兄弟你还客气什么啊!”
大芍药拿出来准备好的一捆粉条、一包白面、一匣点心、一酒嗉子白酒。问:“嫂子,您看我准备的这些行不行啊?”
“行啊,东西肯定行。再说了,你们两家是谁跟谁啊!”
敖大寡妇第二天上午就骑着毛驴去了苇子峪,大兴客气地说:“不用那些讲究了,定下了日子,告诉我们就行了。”
“你二哥不是爱面子吗?他什么礼都不会落下的啊!你二哥还让我问你,是送亲还是接亲呢?”
大兴把大旺叫来了,一起陪着敖大寡妇喝酒。一边吃,一边定下了陈家送亲,还把送亲的人数算计好了。敖大寡妇吃完午饭,和金枝一起,在炕上歇了一会儿,就让大兴套车给送回躲兵沟了。
道宽又开始帮着操持大龙和金枝结婚的事了。他从自己家里拉来了几坛子陈酿大黄米酒、两口袋大米,又赶来了一口大肥猪。整个婚宴所用的东西,也都是他提前买来的。
这几年,黄家和陈家两家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孩子的婚事办得当然很体面。余道宽这样出手大方,差不多包揽了前前后后所有的费用。黄富强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自己家的日子过得也很不错了,给大儿子娶媳妇,不成问题。他几次要给道宽钱,都被道宽给拒收了。
道宽说:“我来到兴州这些年了,您对我,比我的亲爹对我还好呢!大龙就和我的亲弟弟一样,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我们虽然是满汉两个民族,可是比一家还亲啊!您什么也别说了,以后,我用得着你们爷们的地方还多着呢!”
黄富强最后的表态是:“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大龙、二虎和三豹,就是你的亲弟弟。明年,你建庄头府,我们爷几个,全力以赴!”
婚后的大龙和金枝,恩恩爱爱,任劳任怨,给黄家平添了喜气和欢乐。大龙整天和爸爸一起下地侍弄庄稼、起早贪黑地做木匠活,一时不闲。金枝帮着婆婆料理家务,洗洗涮涮,拿锅攮灶。
大芍药整天夸奖儿媳妇:“我们金枝,人长得俊,心眼也好,真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金枝还和婆婆一起,经常去余家,帮着翠花哄哄孩子、伺候伺候老人、拆洗拆洗被褥,就跟干自己家的活一样上心。两家的关系,走动得越来越近便。
第二年开春,庄头府的工程开始了。黄富强一家子、黄富贵爷俩和陈家哥俩,都来帮工了。他们天天早来晚走,出的力太大了,让余忠良和道宽一家,省了不少心,也省了不少钱。
最让黄家和余家高兴的是,金枝和翠花都怀上了孩子,两家的老婆婆一算计,两个儿媳妇生孩子的日子都差不了几天。
秋天到了,打粮、收租、打场,又是一个好收成。
眼见翠花和金枝两个人的肚子越来越大了,家里都不让她俩干一点活了。
翠花毕竟怀的是二胎,知道该怎么准备了,她就和金枝一起,买了布料、棉花,开始做孩子用的小被子、小褥子、小衣服,每样都是双份的,有的还是四、六、八份。
打完场了,道宽就要领着车队和庄丁,去北京交皇粮和送礼。他还特意告诉大龙,说是一起去北京,给老人、孩子买点需要的东西。
道宽说:“咱们今年的收成又不错,我们该去好好买点东西了,大龙也该出去见见世面、开开眼界。”
大龙是个很有心计的人。
他想:这次去北京,买什么东西也不能让道宽哥哥花钱了。
回到自己家里,他的爸爸、妈妈和媳妇金枝,已经给他准备好钱了。都嘱咐他,第一次出远门,千万不要舍不得花钱,更不能总让道宽花钱。
一路上,道宽给大龙讲了很多新鲜事:
满清刚入关的时候,不管是汉人也好、满人也好,朝廷都要求把前额的头发剃掉,在脑后梳上一个大辫子。其实,这是摄政王多尔衮下的命令,谁敢不执行啊!
满族成年男人的发式是剃发垂辫的,道宽比划着自己的脑袋,说就是在额角两端引一条直线,将直线以外的头发全部都剃掉,只留脑后的这一点发,把它打成辫子,垂于脑后。
这种发式,是从他的先民古俗中传下来的。
这样梳头,便于骑马打猎的生活。因为满族男人是以猎为生,打猎就要骑马。所以,我们管这种生活叫骑射生活。如果头前留头发,一抬腿上马了,风那么一刮,头发刮起来之后把眼睛给挡住了,看不见前面。
脑袋后边留一条很粗的大辫子,是为了在野外打仗或是打猎的时候,可以枕着辫子睡觉,就是枕着辫子当枕头了,很实用的。我们满族和我们的先民信奉的萨满教说,辫发生于人体的顶部,与天穹最为接近,是人的灵魂之所在。我们满族男人,都很珍惜辫发。
当年在战场上打仗牺牲的将士,古时候虽然没有条件运回故乡,但是他那个辫子必须给剪下来,给他送还故乡,也表示是落叶归根。
到了清代,八旗子弟用金银珠宝各种珍品,制成了各种各样精美别致的小坠角,系在辫梢上,随着辫子来回的摆动,看起来很好看的。
摄政王多尔衮进入北京以后,把北京当成它自己的京都了,就强制所有的男人从衣冠、发式,都承认他的统治。
顺治皇帝也下过旨意,命令庶民一律剃发蓄辫,以作为人们恭顺的标志,结果遭到汉人的强烈反对。因为,汉人束发的风俗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民族感情已经跟这种具体的发式融为一体,更何况在他们的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定式,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毁伤,这跟儒家的观点是一样的。
过去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是这种做法,说自个儿的身体、皮肤、头发、胡子,都是父母给的,不能随便把它毁伤。因为汉人是有这种意识的,所以就抵制,公然抗旨不遵。
为了安定民心,对剃发这事就不得不暂时让步,允许臣民们照旧束发,悉听其便,就是你愿意留也好,你愿意剃也好,这个暂时不做强行的规定。清军攻下了南京,再次发出剃发令,严令布告下达十天之内必须得换衣裳、剃发蓄辫,如果有违抗或者逃避的,杀无赦。
听了道宽说的这些,大龙说:“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你知道的事真多!”
道宽问大龙:“你们汉族的女人,为什么要裹小脚呢?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哈哈,我哪知道那些事啊!我从小看到的就是那样的,没有问过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就纳闷,你们大清入关以后,我们汉族的男人都和你们一样,留起了辫子。可是,你们满族的女人,怎么不裹小脚呢?”大龙笑着回答。
“这些事,是挺怪的啊!我们是闹不明白的。”
道宽和大龙一路说笑着,两天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哥俩到了北京,事办得很顺利。
跑马占圈的初期,京城地区有一百三十二所皇庄,由内务府会计司主管。后来,塞外也发展了很多皇庄,就独立出一个“三旗银两庄头处”,专门管理皇粮庄头。除了皇庄,还有王庄、旗庄。
道宽和大龙到了“三旗银两庄头处”,遇到的都是道宽的老熟人。他们见到道宽和大龙,也特别高兴,都说:“这几百个皇庄,顶数兴州道宽交的谷子和豆子好,籽粒饱满,晾晒得也干松,还没有杂质。特别是那些黍米,是别处很少有的。”就凭道宽的信誉和人缘,庄头处既管吃、又管住,还派出轿子,让道宽、大龙上街时享用。
他们在北京住了五六天,把想到的、该买的,都买了。道宽还领着大龙,去转了大栅栏和几个园子,又托内务府的人进紫禁城看了整整一天,拜访了几位朋友。
他们哥俩,又用一天的时间,专门在前门的店铺转了几个来回。那可是内务府支持开办的店铺,让道宽和大龙大开眼界啊。
小哥俩一边看,一边商量:“我们不能只在兴州种地打粮、耍手艺,挣受累钱啊,我们应该和北京人学会赚俏钱。”
“就是啊,要想办法把我们山沟的野货、山货,捣鼓到北京来卖,可以说是一本万利的。”
“咱们回去就琢磨,这次的北京不能白来!”
晚上住在内务府的客栈里,哥俩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话题:想去看看北京的学堂什么样。
第二天,他们俩又让内务府帮着联系了国子监,然后就去了“八旗官学学堂”,仔仔细细地转了、看了。
小哥俩结束了北京之行,打点行装,坐着马车,拉着大包小裹的从北京返程了。这一路上,哥俩商量着,明年春天,就开始建庄头府,还必须建学堂,一定要让自己和乡亲们的孩子念书识字。还要学着到北京做生意,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日子。
真巧,他们哥俩回来的第二天,道宽的二儿子出生了。
满族十分重视对子女的生育。妇女一旦怀孕,被视为全家的吉事。这时,婆婆就会告诉怀孕的儿媳妇一些保胎知识和传统禁忌。比如不准孕妇到别人的产房去,不准坐锅台、窗台,不许大哭大笑,不准侍奉祖先神。怀孕五个月以后,不许去马棚,不许牵马等。
小孩儿出生了,叫“落草”。古时满族妇女在炕上临产时,暖和时候,卷起炕席,铺上干净的沙面。天冷时,要卷起炕席,铺上谷草,产妇在谷草上分娩,以后便相沿成习。
小孩儿“落草”后,如果是男孩儿,要在门左悬一小弓箭,象征孩子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优秀射手。如果是女孩儿,就要在门前挂一红布条,象征吉祥。
婴儿出生的第二天,要请孩子多、身体好、正有孩子吃奶的妇女喂第一次奶,叫“开奶”。
第一个进产房看孩子的外人叫“采生人”。满族人认为婴儿长大后,性格会像“采生人”的性格。所以十分注重挑选“采生人”。
婴儿出生的第三天,要“洗三”,请儿女双全、德高望重的老太太给孩子沐浴,也称沐浴礼。沐浴用大铜盆,内放槐树叶、艾蒿,倒上热水后,前来祝贺的亲友们则将铜钱、花生和鸡蛋等放入盆内,叫做添盆。沐浴过程中,如婴儿放声大哭,则视为大吉大利,这叫“响盆”。
孩子出生后第七天开始上悠车。悠车也叫摇车,用桦树皮做成,长约三尺,宽二尺,两端呈半圆形,如同小船。后世的悠车多用椴木薄板做成,边沿漆成红色,绘制花纹,书写有吉利话,十分美观。悠车挂在房梁上,摇起来十分轻便。为了使婴儿保持胳膊、腿平直和避免翻身时掉下来,一般用布带子把小孩的胳膊肘、膝盖和脚脖子绑在悠车上。婴儿下面铺用谷糠装成的口袋,枕头要用小米或高粱米装成。因满族以孩子后脑勺扁平为美,所以使用这样的枕头。
孩子满月后正式起名,五岁前举行一次家祭,俗称“跳喜神”。一般只用一天,不杀猪羊,只杀鸡做糕,祭祀祖先神,感谢神龙送子。在大家族中公祭时,要举行“换锁”仪式。每个新生孩子每人领取锁袋一副,并拜柳求福。祭拜完毕,再把锁袋装入子孙袋内保存起来。
孩子第一次去姥姥家,无疑是件大喜事。当姑****带着可爱的外孙回娘家,姥姥一家不胜欢喜,待之如贵宾。这时,年轻母亲把孩子的脑袋往房柱上轻轻一撞,表示孩子不仅能在姥姥家住得服(惯),而且将来肯定能长得健康壮实。
八岁以前,男孩玩具以弓箭为主,也开展比箭法游戏,谁射得准,谁就受重视。女孩子则以玩秋千为主要娱乐活动。
满族没有固定的冠礼。只是由族长或萨满在祖神案前祭祀,将灵佩赐给青年男女。一般小伙前额佩挂野猪獠牙,姑娘多佩带野猪门牙。从此,青年男女就可参加族中的一切社交活动了。
道宽二儿子出生后的第七天,大龙的媳妇金枝也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哥们、爷们坐在一起,给孩子起名叫玉树。
道宽的儿子满月了,他和父亲商量着,给二儿子起名建业。
兴州的人们啊,真的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前前后后用了二十多年,余家、黄家和陈家,先后在兴州建起了三处大院。
余庄头是吃皇粮的,还有内务府的大力支持,当然是建了最大的一个四合院。最南面是庄头府,有办公房六间,庄丁用房四间,厨房、库房各两间,一共十四间;东院是行宫,八间房宽,其中有大厅五间,套间房两个,居室五间,前后房五间,有厢房十间,计二十六间;西院是临街地段,六间房宽,院内由北至南有厢房、围房九间,花室三间,还有库房、酒肆,计二十一间。北院是余道宽一家的住处,六间房宽,有大厅三间,居室五间,前后房五间。有厢房六间,计十九间。总计八十间,花园一处,占地十五亩。后来,还在西院开设了客栈、商铺,特意开办了学堂,一个蒙馆、一个经馆,还有维持治安的保家队。田地达到了四千八百多亩,每年收租六百多石、店铺收入三千多两银子。
黄家的大院,九间瓦正房,有三间一明的客厅,两头各为一间居室,有瓦厢房十间,门面房六间,共有二十五间,房后有一亩地的花园。黄家成立了瓦工社、木工社、石匠社和铁匠炉,黄大龙成了大掌柜。田地一百多亩,每年收入也到了千两以上。
陈家建的一处院子,规模比余府和黄家小了一些,也有十间房子。他们开了一间山货铺、一间钱庄。田地八十亩,年收入五百多两。
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栽了很多树,院子里栽上了大芍药、刺梅果(玫瑰)等花花草草。
余道宽有了三个儿子建庄、建业、建功,个个聪明伶俐。家业兴旺,其乐融融。
年事已高的父母也相继寿终正寝。道宽哥几个在黄家爷几个的帮助下,先后把老人的遗体送回了东北老家,按照满族的丧葬习俗,得到了风光、体面的安葬。
黄大龙的媳妇金枝,先后生了两个儿子玉树、玉德。后来又接连生了两个漂亮的女儿,大的叫牡丹,小的叫二菊。
人丁兴旺,家和业兴。古镇兴州复兴起来了。
名门望族的兴起,带动兴州的户数和人口连年增加,形成了一个有一百多户、五百多人的大集镇。
“余家的粮,黄家的房,陈家银子窖里藏,家家户户芍药香,古北口外好地方。”
这是当时兴州的真实写照。
到这个时候,从古北口到喀拉河屯的滦河、潮河和伊逊河两岸,又先后来了二十三个皇粮庄头,他们雇佣农民,或租给农民土地、山场,为朝廷或是王府生产供应粮食、蔬菜、马匹、牛羊、山野货等物品。
这里,成了京都的粮饷、山货补给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