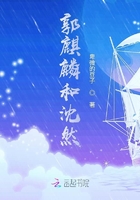林非
去年的盛夏季节,在一个阴郁和闷热的早晨,长桌上的电话机突然响起了急促的铃声,是韩国一位年轻朋友打来的,告诉我许世旭教授病逝的消息。已经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接到他充满欢声笑语的电话了,我正准备在一两天之内,像往常那样往他家里打去电话,兴冲冲地交谈一番,却怎么会传来这样的噩耗?太使我惊讶和悲伤了!
像他这样总是挺立着结实的身躯,睁开炯炯发亮的眼睛,风趣而又恳切地跟大家说话,热忱地挚爱与关怀着所有的朋友们,洋溢着如此侠义心肠的人,应该长久地活在世界上,却为何匆匆地离开我们?我几乎要大声呼喊起来,询问这人世的命运,怎么会如此的难以预料?!于是整天都回忆着与他相识之后多少难以忘却的往事。
立即想起了二十年前,还没有跟这位比我年轻三岁的韩国朋友晤面时,就收读过他的信件,接听了他打来的多次电话。说得一口多么流畅的汉语,从他响亮与豪爽的嗓音中间,就能够感觉到一颗多么灼热的心。我在当时对于韩国的很多情况,还都十分陌生,也并没有留意过这位鼎鼎大名的汉学家。他却如此盛情地邀请我前往首尔,去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国际散文研讨会”。比起我的闭塞和孤陋寡闻来,他了解和掌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情况,是相当详尽与丰富的。
他在多次的电话中,仔细和我磋商,如何凭他寄来的机票,先从北京飞抵香港,再搭乘转往首尔的航班。因为在当时,中韩两国还未曾建交,并无从北京直达那儿的飞机。这位在当时还是十分陌生的外国学者,竟如此不辞辛苦地筹划我整个的行程,替我办理前往韩国的一切手续。如果在广阔的世界中间,多少并不相识的人们,都涌动着这样温馨与亲切的友谊,能够如此和蔼与耐心地对待,那将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情景。
许世旭还邀请了散文理论家傅德岷教授,和我一起赴会。当我们从北京抵达香港之后,碰上了一队又一队拥挤的旅客,纷纷前往韩国去游览,因此无法签上当天飞向首尔的航班,要等到明天早晨再办理登机手续,而且也不允许走出机场的大厅,去外边的旅馆投宿。那就只得焦急地坐在这儿,背靠着硬梆梆的塑料椅子,准备度过一个困倦的不眠之夜。
高耸的玻璃窗外边,一阵阵红红绿绿的光芒,从路边巨大的霓虹灯里照射出来,像是在燃烧着一团团滚烫的火焰。几个匆忙赶路的行人,正擦着脸上的汗水,向前面一幢幢灯火通明的高楼走去。在黑黝黝的天空中,像有一串串摇曳的星光,不住地闪烁和晃荡,原来是多少架起飞或抵达的飞机,正在忙碌地升降着。
听到广播里的声音,知道在密封的窗户外面,是摄氏三十四度的高温天气。大厅里却冷飕飕的,空调机里吹出的凉风,让我们两人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傅德岷从凳子上拿起一张色彩鲜艳的香港报纸,不是为了要观看上面登载的苏联刚发生解体的消息,而是快速地围住我的胸膛,想用来替代御寒的棉被。我双手握住这张薄薄的报纸,赶紧盖在他的脖子底下,然后就站立起来,走到公用电话机前,打了个电话告诉许世旭,我们已经到达香港的机场,明天才能够办理出发的手续。他听到我的声音,长长地喘了口气,说是刚才没有接到我们,真把他吓坏了。我放下电话,带着傅德岷去寻找进餐的地方,草草地吃完之后,就在空旷的大厅里踱起了脚步,张望着远处的大门旁边,偶尔走进来几个金黄色头发的旅客。
经过整夜的煎熬,终于在第二天乘上了前往首尔的飞机,很快抵达之后,就见到许世旭的夫人,正带领一位我们都认识的韩国友人,等候在机场的门口。这位有着一半华夏血统的韩国朋友,缓缓地说起昨天傍晚时分的情景:许世旭的手里,握住写上名字的纸牌,站在候机大厅的走廊中间,张望着从前面匆匆走过的多少旅客,和气地询问着是否有来自香港的那架客机,等到人们全都走空的时候,还没有瞅见我们的影子,他的心里顿时变得慌张起来,分明已经往我家中打过电话,肖凤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他,说是已经将我和傅德岷送进前往机场的汽车里,那么是否在香港发生了什么意外?却又无法跟我通话,回到家里,忧心忡忡地坐着,不想说话,也不像我们这样,从容地完成了晚餐的程序。
他在默默无语中,突然接到了我的电话,才放下心来。夜已经很深了,却还不想躺下睡觉,担心我们明天能否顺利到达,赶紧给香港的一位朋友打去电话,委托他帮助我们,能够签上飞往首尔的航班,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张口大笑了一阵,接着就打起哈欠来,还朦朦胧胧地想象着我们的困境,很紧张地猜测着我们疲倦的模样,整夜都合不拢眼睛,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悠长的夜晚。
我们在香港的不眠之夜,显示出旅行的艰辛与劳顿,他于首尔的不眠之夜,却纠结着友情的牵挂和惦念。尽管在当时,我还没有跟他见过面,更不曾知晓他运用汉语撰写的那些诗歌和散文,他却已经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像这样真诚、纯洁与高尚的情怀,将会永远记住在我的心间。如果不是牢牢地记住这一点,不是也如此对待许许多多的人们,而是冷漠和琐碎地打发自己一辈子的生活,真的又有什么意义呢?
正因为被许世旭这种十分仁义的胸怀所打动,就与他结下了诚挚的友谊。恰巧是在这之后不久,中韩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于是他非常容易地实现了许多年前的愿望,连续来到中国大陆参观访问。他说起了多么遥远的童年,就在自己父亲的教诲下,认识了不少的汉字,后来去台湾留学的时候,学习的又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从那儿毕业以后,回到首尔的几所大学里,开始讲授有关这一方面的学问。他翻译过中国的不少文学作品,也撰写过不少有关中国文学的理论著作,这些典籍,对于韩国广大的人士深入地熟悉和理解中国文学与社会状态的演变,以及不断向前拓展的情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且不涉及那些比较大型的项目,只说他翻译朱自清的《背影》这篇散文,在被选入韩国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之后,就使得成千上万的年轻学子们,滋生出一种关注中国的情愫。像这样形成的影响和力量,真是无法用数字能计算得清楚的。
记得在十余年前,另外一位韩国友人邀请我前往首尔,去参加一个国际性的鲁迅研讨会时,曾经从釜山南端的大海之滨,走到了三八线北边的雪岳山顶巅。当我跟许多萍水相逢的韩国朋友,提起许世旭的名字时,人们都非常熟悉地称赞他在建立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和深厚友谊方面的诸多建树。每逢这样的时刻,总会使我想起唐代诗人高适在《别董大》里写下的那一句诗,“天下谁人不识君”。他所作出的这些贡献,确实会永远留在许多人们的心里。
正因为毕生都关注着华夏的文明,所以他最喜爱和向往的一桩事情,是在辽阔与美丽的中国土地上行走。这二十年之间,他大概来过有十余次之多,多么雄壮或俊秀的风景,使他感到无比的神奇,深深地迷恋和陶醉着,又很惋惜地感叹生命的短促,肯定是无法走完和看尽这些多姿多彩的景致。
他在那一回畅游了庐山之后,又辗转寻找到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坟墓。途经北京回国之前,他与我聚会畅谈的时候,形容着多少挺拔与倾斜的峰峦旁边,一朵朵的白云,映照着朝霞的红光,纷纷飞向冲过悬崖的瀑布,凝视着溪涧里潺潺的水流。他又诉说自己徘徊在苍翠的松树底下,默默地吟咏《神释》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两句很玄妙的诗,接着还兴奋地一面绕过青翠的田野,一面就轻轻地背诵那首《饮酒》。他兴高采烈地跟我诉说时,还大声念起了“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并且举着杯盏,抿住嘴唇,将浓浓的酒水灌了进去。
在酒兴正浓的时候,他忽然说起了侵占和蹂躏自己家园的日本军队,喝得醉醺醺的,挥起尖尖的刺刀,凶狠地戳向过路的行人。他怀着满腔的仇恨,回忆起当时的多少苦难。当我也诉说起自己的童年,被侵占故乡的鬼子兵欺凌时,话语就变得跟他同样的激烈。他后来又经历过多次的战争,感叹着在惨重和残酷的伤亡中间,最遭殃的总是无辜的平民百姓。
他抬起头颅,激昂慷慨地抒发着内心的愿望,说是必须要将这些苦难的历史,告诉今天的年轻朋友们,让大家深深地知道,保卫祖国的独立,打造和平的日子,是多么的珍贵与幸福。他又举起酒杯,希望多少贫穷的人们,都能够过上富裕和美好的生活。正因为遭受过世间的不少磨难,他才会竭力地主张要尽量做到欢乐地度过每一天。喝一口美味无穷的酒水,正是他此种十分舒心的享受,而且当嘴里含着这样香醇的气味时,会更升腾出邈远与神秘的思索来。
又有一回,他前往新疆游览的时候,先在北京停留过两天,于是我们又有了一次晤面欢聚的机会。他诉说着将要踯躅于茫茫的沙漠中间,观看那一望无际的尘土,回想人类的祖先,怎么能够如此智慧地开辟出新颖的世界来,却又无法避免贪婪的争夺,野蛮的抢掠,直至爆发毁灭多少生命的战争。独自站立在灿烂的阳光底下,冥想上两天的光阴,然后再回归到熙熙攘攘的人海中间,比较一下在不同环境里的思索,究竟会有何等的差异。过了几天,他真的漫步在没有人烟的沙漠里,给我打来了电话,兴奋地诉说着自己面临的景致。他正笼罩于阴霾的天空底下,一阵阵吼叫的狂风,刮起了脚下细碎的泥粒,满世界都是灰蒙蒙的,于是他念起了高适在《别董大》里写下的“千里黄云白日曛”这句诗来。我在电话里大声地叫嚷,嘱咐他千万要注意旅途的安全,既然已经是薄暮的天色,得要在住宿的地方好好地休憩。
至于他观赏得最多的景点,是我从未去过的青海湖。听说那望不见边沿的湖水,在阳光的照射底下,碧蓝碧蓝的,闪耀着晶莹透亮的光芒。每当中国各地的很多诗人,在这里开会讨论的时候,他都会被邀请前去,发表精彩的讲演。他这几次与诗人集会的行程,提醒我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于是和北京的十余位散文家商定,召开一次讨论他散文创作的会议。
参加那一回讨论的,除了中国的作家和记者之外,韩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因为在跟许世旭通话的时候,知悉了这个消息,也兴冲冲地赶来,聆听大家发表的意见。
由于参加会议的多位作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查阅了他不少有关的著作,因此都提出了很好的看法。有一位文友这样评论他的散文集《移动的故乡》,认为在他的笔下,蕴涵着一种充满了文采和情韵的语言,因此就很能够震动读者的心灵。像那一篇《再也移不动的故乡》,写他的母亲于弥留之际,显出多么痛苦的模样,使得自己在内心的哀伤中,竟觉得似乎天地也不再旋转了,又像那一篇《一寸与二寸之间》,因为澎湃着悼念母亲的情怀,竟觉得自己所栖身的土地,也似乎随着亲人的亡故,正一天天变得冷却下来。读着读着,不由得使人也热泪盈眶起来。
还有一位文友认为,在许世旭的笔下,只要是他所触及到的人间世态,抑或是种种的自然风光,都描摹得栩栩如生,这样就能够让我们津津有味地浏览下去。他所作出的这些艺术上的成就,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参照的。分外让人觉得惊讶的是,一位外国的作家,怎么竟会运用中国的汉字,写出如此美好的篇章,闪烁出一种深沉的文化传统?这不能不启示着中国的同行,怎样更努力地继承悠久传统中最为珍贵的因子,从而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崭新局面来。
又有一位文友认为,中国的汉字是如此的优美和丰盈,凝聚着无穷无尽的表达能力,却由于并非从拼音的轨迹所构成,因此想要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它,实在是太艰难了。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似乎还从未听说过,有哪一位作家能够像许世旭这样,构筑如此洋洋洒洒的汉字,来从事自己的散文创作,实在可以说是世界文学领域中的一桩奇迹。
文友们的发言,都充满了严谨的说理、深切的思索和动情的话语。通过这些情况的说明和分析,真可以让人们从历史与地域的角度,更宽泛与深邃地考察他取得的成绩的意义。大家静静地坐着,默默地听着,尽情地享受着哲理与诗意的情趣。
我瞅见许世旭微微地张开眼睛,入神地倾听着大家的每一句话语。他肯定会在仔细地考虑,如何去描摹出更多动人心灵的作品来。不仅是他在琢磨这个严肃而又艰巨的课题,包括所有的文友和我自己,肯定也都揣摩着如何去融化这些能够启迪自己的话语,因此真是一个开得十分成功的会议。诚挚与深入的探讨,真是取得成功的保证。
回忆自己和许世旭多年以来深深的友情时,最感到惋惜的是再也不能见到他了,再也不能听到电话里他响亮与热忱的声音了。我从好多册厚厚的照相簿里,找出了几张与他合影的照片,可以瞧见他多么爽朗的笑容,同时还从高耸的书柜里,拿出他用汉语撰写的《许世旭散文选》,和他编选与翻译成韩文的《中国现代散文选》,放置在自己读书与写字的案头。从这些喜笑颜开的身影中,款款深情的文字里,回忆他多么爽朗、豪放、仁慈、悲悯和寥廓的情怀。
选自《上海文学》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