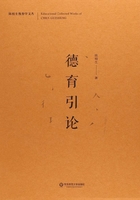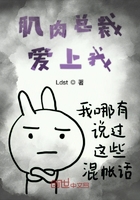梨澈似乎愣了一愣,只是即便如此,嘴角温温柔柔的笑意却片刻都不曾消弭。静静的垂下眸,他伸手夹了块糖醋甜藕放进了我面前的碗碟,神色悠然的道:“画扇,很好。”
我不禁轻轻的呼了一口气,他既肯这样说,应该算是欢喜画扇的吧?想到那条时时记挂在我心头的红线即将牵引成功,我心竟是说不出的愉悦熨帖,不自觉的便轻笑出声:“你既然……。”
“公主,也很好。”
他打断我,第一次以一种不甚礼貌的方式,玄而低头为我淡淡的续了一杯茶,重复的道:“公主,你也很好。”
我怔诧,抬头望他,却见他也正望着自己,依然是淡淡的浅笑,却仿若始终隔着层迷雾般让人琢磨不透。这情景太过诡谲和不寻常,我讪讪的放下了手中的筷子:“梨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
“公主三月之后便要嫁进酹月府了吗?”
又一次被打断,饶是我再愚笨,此刻大概也明白了几分他的意思,不禁心有些默默然。不仅为画扇的一厢情愿,更是为我前途未卜的将来:“是,你知道的,母皇的命令一向是不许人违抗的,我别无选择。”
他低头沉吟了瞬方道:“可是我听说那酹月王爷从16岁开始就病卧床榻,这些年里每日里便是靠着药罐子将养身子才勉强苟延活命,先帝曾挑选五名女子嫁进酹月府,最后却全部离奇惨死,无一幸免——。”
他顿了一顿,方含笑望我:“公主如何看?”
我轻压了一口茶,半天却只是默默:“你心中既已有了答案,又何须问我?”
察觉到了我的隐约不安,他凝起笑意,莹润的瞳内闪过一丝淡淡光华,安定而温暖:“公主无需忧心,不管这酹月王爷是真病亦或是假病,对于我们都没甚影响,甚至有极其大的助益。”
“哦?”我略微诧异的望他:“此话怎讲?”
他淡淡一笑,唇角眉梢间是不曾改变的波澜不惊:“如果他是真病,那公主便可以轻而易举的将他作为傀儡取而代之,借助其至高无上的王族身份和人脉来谋划自己的事业;如若他是假病……。”
“我便可以笑看鹬蚌相争,坐收渔翁之利?”
梨澈摇头:“并没有那么简单。”察觉到了我不解的目光,他续续道:“如果那酹月王爷真的是在装病,我倒不认为一个小小的虞水心能使得他如此的大费周章。”
“你的意思是——”,我的心猛然一颤,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闪现在眼前:“莫非他要的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小小的天虞,他想要的竟是——。”
“整个天下!”
梨澈断然道:“如若他想要的仅仅只是一个天虞,他犯不着从四年前便开始装病,不问世事。毕竟先帝并无子嗣,一旦仙归,他便是第一顺位人,到时虞水心即便是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但他却在最为光辉的时刻退隐了,就连一年前虞水心登位,改东临国为天虞,他都不曾有任何反应,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他要躲避隐藏起自己的锋芒,不让真正的敌人有所察觉。”
梨澈浅浅一笑,琥珀色的眸光带着俯瞰一切的华贵与优雅,赞赏的扬眉:“没错,虞水心虽狡诈凶残,但聪明有余却始终带着几分妇人的浅短见识,不能知人善用且太过专横武断。对于反对自己政治理念的臣子,从来便是以杀戮来解决问题,这样子残暴的排除异己,虽一时可以震慑住朝堂众臣,但日子久了,人心必然大乱。”
他抿了一口茶续道:“这样子的虞水心,根本就无需酹月王爷费多少气力。而观望如今天下局势,天虞表面看来是太平无比,实则南有兵力强盛的南越国压境,西有经济阜盛的西络国虎视眈眈,天虞经济上不如西络,兵力上不及南越,始终处在中间这样一个不尴不尬的位置,其实是极危险的。”
“你的意思是说,酹月王爷隐蔽锋芒,韬光养晦防着的其实是南越和西络两国?”
“是”,梨澈起身,对着皎皎月色背手而立道:“你看,最近南越国不是有些耐不住了吗,时时在边关滋事,若不是被逼到绝处,虞水心又怎么会下决心派北漠带兵出征呢?北漠的确是一个天生的将才,可惜却太过年轻自负,缺少实战经验,这一仗注定是要败的。只是我们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到,天虞朝廷能用的人才实在是不多了。”
我被他这样一点拨,一时间竟将过去许多不曾明白的事情想的通通透透,脑中不觉闪过一个怪异的念头:“莫非这酹月王爷暗中也训练着一队精锐之师,只等着虞水心与南越王打的不可开交,越见疲乏之时,他再从后来个突然袭击,打的双方措手不及,从而坐收渔翁之利?”
梨澈笑着点点头:“公主猜的一点儿都没有错。从古至今战场之上讲究的便是一个速度,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时间拖得越久战士们的斗志便只会越低迷,而酹月王爷便是看准了这难能可贵的低迷期,在双方都精疲力竭之时,出其不意的来一一招釜底抽薪之计,自然便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听他这样说完,我心下里竟沁染上几许薄薄的凉意:“如若这整件事的发展真如此刻你我所预测的一般,那我便只能感叹那酹月王爷的心思竟能深沉至此?以前我一直想不明白,如果那酹月王爷果真是在装病,却为何还能在虞水心登帝改朝换代之时,他都能按兵不动,隐忍至此?此刻方才明白,他哪里是在隐忍,他分明是早早就将所有人的动作和想法算计的分毫不差,然后编织好天罗地网,只等着那两方活活往里跳。一年前东临改朝换代,最开心的便该是西络和南越,在他们心目中,东临女子当政,局势岌岌可危,这便是那酹月王爷用心给他们编织的错觉和网。于是一向崇尚武力的南越便耐不住性子了,必然会向天虞开战,等两方打的不可开交筋疲力竭之时,他再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仅可以扭转虞水心当前权倾朝野的局势,更能狠挫南越的军事力量。而西边的西络国虽经济强盛,但其军事一向薄弱不堪,几百年来若不是仰仗于南越的庇护又怎么能绵延存在至今?南越的军事受挫,自身都自顾不暇自然也就没有气力管西络,那么天虞要攻下西络也便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了……。”
一口气将这整件事的脉络理清之后,我竟又是一阵隐忍不住的喟叹与感慨:“还真是一箭三雕之计,此人的心思简直深沉不可揣度……。”
梨澈弯腰拾起一朵落地的残花,若有所思的捻了捻,沉吟了许久方道:“其实公主也无需太过忧心,以上种种也不过是我们的猜测罢了,是否真是其事还得经过之后的试探方才能有定论。亦或许这酹月王爷的的确确便是个不问世事的病痨子,一切的一切不过只是我们杞人忧天罢了。”
我凝眸索眉:“如何试探?”
他笑了一笑,玄而握起桌上泡茗的杯盏,浅浅抿了一口方道:“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会将毕生所学的切脉之术细细教予公主,三月之后公主只需近得他身,便能轻松知晓其到底是在装病亦或是真病?”
我念了念,不禁点头:“这倒是个不错的方法。”
话虽说的安宁妥帖,但我却是颇不平静的,想起那不可预知的惨淡未来,我心竟是说不出的茫然无措。我深吸气正欲起身舒缓一番,却发现不知何时撑在桌沿边的手被一双大掌暖暖倾覆住,五指如玉,修长疏朗,温温灼烫间似在传递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锁情,你在害怕,对吗?”
第一次,这个矜淡男子没有再叫我公主,而是柔柔的唤了一声锁情。我怔了一怔,抬头便望到了他淡淡如清水般的眸子,不自主的便开始反驳:“我没有……。”
他低低笑起来,很轻很轻,却如暖暖的柔羽般,轻划过我茫然无定的心脏,带着出乎意料的力量。玄而抬头,目光坚毅恒远,一字一顿仿佛在说着一个亘古都不会变更的誓言:“锁情,我永不会让你寂寞,即便是阴曹地府,我也愿陪你笑着走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