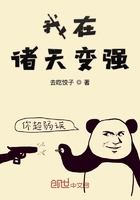许多年过去了。坐在午后的安静的光景里。那时,日光有些老了,斜斜地穿过树梢,飘落得满地都是。茶早已淡了,凉了。人生,正如一杯绿茶,喝着喝着,不经意间,岁月已经老去,人意已经老去,嫣然如花的人面已经老去,心上落满了漂泊的离愁别绪。无论离乡去国千里万里,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离开过家乡,少而壮,壮而老,人生一路漂泊而来,漂泊的意绪总会时时在心底涌起。
拂去漂泊的意绪,在心的最深处,总有一个小小的天地,明亮、温暖、纯粹。那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照亮了漫漫人生之路,温暖了游子寂寞的情怀。人生萌发于童年。童年的经历,父母的言传身教,家族的人文环境,总是深深浅浅地刻进记忆的深处,总是化作一种力,时时推着你,规约你,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成为宿世的果和今生的因。
直到很久以后,童年的美好还深深地刻在李叔同的心里,化作他的《忆儿时》一歌:
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读来颇为感伤,但心底里又情不自禁地弥漫着温馨的因子。
这是李叔同在老宅生活的情景。其实,李叔同三岁时便离开老宅了。那年,李筱楼买下了离老宅不远的粮店后街60号大宅子,供全家人居住。大宅子建于道光年间,分成前后两个大院,由四个小院落合成“田”字格局。“田”字中间位置,有一座十分考究的洋书房,名曰“意园”。名此“意园”,李筱楼心意里渴望随心顺意,情感里想望田园之闲之雅之自在之从心所欲;但身处熙熙来攘攘往的漩涡中心,又如何能够清净脱身?意园,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意念,一点点志闲的意思吧。
那么小就离开老宅子了,回去的时光一定不会很多;但在李叔同的记忆里,那低矮而温馨的茅屋,屋前的老梅树,老宅子外高枝上的啼鸟,金钟河里的粒粒游鱼,无不清晰如昨。不难想像,老宅辰光留在李叔同的记忆里是何等的深刻,又是怎样的温馨。
孩提时代的李叔同,有老父亲宠着,有母亲护着,有一群下人围着,锦衣玉食,无忧无虑,十分快乐。不过,李叔同最快乐的还是家里举行的放生活动。李筱楼生日,李文熙生日,李叔同生日,李家都要放生。每到这一天,李家人一清早便赶到菜市场,凡是活鱼虾、活鸟儿,一律统统买回来放生。商贩们早早便得到消息,纷纷或挑或捧或背,携着活鱼虾、活鸟儿赶到粮店后街李家贺喜。一时,李家门前车水马龙,喜气洋洋,热闹非常。
看着那些鱼儿摇着尾巴向金钟河的深处游去,看着那些鸟儿扑楞着翅膀向高高的云天飞去,李叔同的眼里灵光闪闪。那一刻,一缕慧光掠过,一阵和风拂过,一粒叫做慈悲的种子随风落进了李叔同的心田。风雨际会,种子便会发芽,扎下慧根,生长出慈悲的灵苗。慈悲,正是佛家的根本所在,“因佛心者,大慈悲是,今能放生,即具慈悲之心,能植成佛之因也。”
放生,寄托着祈求延寿、健康、免难等美好的愿望,更显现出对生命的尊重、悲悯和关怀。在佛的眼里,人,飞禽走兽,鱼虾微虫,都是平等的众生,都有权利拥有一缕阳光、一滴水和一个小小空间。置诸当今世界,贪心炽热,物欲横流,极尽豪奢,放生所表现的大悲悯情怀,也许不止是一种清凉剂。
放生的善业,化作妙妙祥光,照亮了李叔同人生最初的岁月。那么,李筱楼大行善事,兴办备济社、馍馍厂、存育所、义塾,救助穷苦,关怀孤寡,则化作慈风悲雨,滋润了李叔同心底的那一枚幼小的灵苗。
母亲王凤玲善良。是纯良的天性使然,也是她人生际遇的结果。穷苦人上门来求助,母亲王凤玲不但不感到厌烦,反而总是帮着他们说话。母亲的纯良和慈善,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化作缕缕蕙风,吹起了李叔同心里的那片慈悲清波。
李叔同喜欢“意园”,喜欢那屋前的花草和屋子里的摆设,更喜欢默默地看父亲读书、写字。李叔同安安静静地待在身边,李筱楼的心似乎觉得更加的充实和安宁了。也许,李筱楼还隐隐的有一层深意,期望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把读书的心气传到李叔同的身上。
李叔同早慧,听父亲讲说得多了,尽管似懂非懂,却已经记下了许多警句联语。多年以后,已经是弘一法师的李叔同,在与自己的学生刘质说起这段往事时,还能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两副对联:
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
今日方知心是佛,前身安见我非僧?
知足者可静,无求者能定;静寂安定,禅意自生,佛性自具。佛性照彻,心地通明透亮,无牵无挂无碍。仰望佛,走近佛,其实我就是佛;过去,现在,未来,无往而不往,能说此前那一世不是佛前虔诚的一衲么?
这些联语,像清凉的泉水,流进了李叔同的心里。涤荡着,浸润着,滋养着,李叔同的精神得到了佛性最初的净化。这大约是李筱楼始料未及的。
离李宅不远,有无量庵和地藏庵两座寺庙。李叔同常常随家里去那里,心里感到有些神秘,更存着一份没来由的向往。听和尚诵经的次数多了,李叔同竟然能够一字不差地背诵《大悲咒》和《往生咒》。乳母刘妈妈听来,总有怪怪的感觉,觉得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没有好处。于是,刘妈妈便把自己会背诵的《名贤集》里的格言诗教给李叔同。李叔同记性好,不久就会背诵刘妈妈教给自己的格言诗了。
刘妈妈原想让李叔同幼小的心灵明媚一些,欢快一些,实在一些;但她没有想到,她所诵的格言,像“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像“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传达着人性丑恶、人世艰难的信息,依然充满苦空、无奈的意味。从本质上说,这些格言,同样是滋育李叔同心底里那棵佛性灵苗的营养。
李叔同五岁那年,李筱楼撒手人寰。李筱楼人生之最后,实在是李叔同一堂重要的佛教课。
李筱楼虔诚皈佛,对于生死早已有了不可言传的妙悟。与其说是痢疾不治,不如说李筱楼已经明了自己往生的日子到了。他平静地安排着自己的身后事,退医停药,屏退家人,转请高僧学法上人一行前来颂经。
屋子里极其安静,唯有学法上人轻轻唱颂《金刚经》的声音。那声音舒缓安详,空寂悠远,像一片明净的光轻轻地飘掠,又像一缕和煦的风微微地吹拂。经声里,李筱楼那颗疲惫的痛苦的破损的负累重重的心,终于轻了淡了明了净了,被和煦的风托着,在明净的光里,飞,飞,一直地飞,好轻松!好安宁!
李筱楼安详而逝。李叔同走进老父亲的卧室。老父亲睡在那里,微闭双眼,脸上是祥和、安宁、满足的神情。这神情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李叔同的心里,以至多年后他还记忆犹新:“舍报之时,安详迁化,如入正定,盖亦季世所希有矣!”
李筱楼的丧仪其实就是一场佛事活动。灵柩在家里停放了七天,请来大批和尚,昼夜诵经。安葬前的最后一晚,还请来道士与和尚一起对放“焰口”。
那时候,李叔同太小,老父亲的故去,或许让他心里有一丝丝牵挂的疼痛和没来由的失落,但终究感觉不到亲人死别的撕裂之痛。对晚清重臣李鸿章亲自为李筱楼祭仪“点主”的哀荣可能早已记不起来,但李叔同对丧仪的佛事活动却一直记忆犹新。时常和邻里儿童们玩类似的游戏。他们把被单当袈裟披在身上。李叔同装扮成大和尚,口中不断念念有词。侄儿李圣章和邻里的几个孩子则装成小和尚,听从李叔同的调度。
这是李叔同戏剧人生的最初尝试么?是李叔同皈佛生涯最早的吉羽祥光么?一盏祥妙的灯,悬挂在幽深的历史空际,穿过茫茫的时空,照彻纷繁的红尘,照彻一个又一个从他的光里穿过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