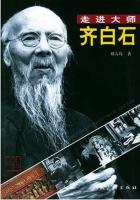还是第一次在惠安净峰寺的时候,弘一法师写过一联自况:
誓作地藏真子,愿为南山孤臣。
地藏王菩萨大愿行世,“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南山律教,数百年衰落,续脉已难,而要加以弘传发扬就更加的艰难了。弘一法师道心已坚,哪怕是孤独一人,哪怕是抛却形寿,也要把南山律学的种子一颗一颗地播下。
1937年5月14日,弘一法师带着传贯、仁开、圆拙和特意迎请他的梦参等四位法师,乘船从泉州蹈海,道经沪上,继续易船北上,20日抵达青岛。
弘一法师在湛山寺的行迹,倓虚法师在自己所著的《影尘回忆录》里记述甚详;而僧隆安法师当年还是一个少年火头僧,有幸亲受弘一法师的法雨慈光,点点滴滴,化作了《弘一法师在湛山》一文,是一旁静静地观察,又是一颗心被渐渐地点亮。
一到湛山,似乎还没有洗去长途奔波的劳倦,弘一法师便开始了又一回的弘律讲学。
佛祖释迦涅槃前告诫自己寂灭之后,佛教当以戒为师。佛教里的戒、定、慧三学,佛典里的经、律、论三藏,其中的戒和律,都是讲的佛徒行为规范,什么样的行为必须禁止,什么样的行为必须奉行。可以想见,戒律在整个佛教体系里处于怎样重要的地位。说戒论律,最根本的,是要内心的真正受持,是要自律。每个人都能够从心开始,谨严自律,心与心便会像灯与灯一样相互照亮,相互温暖。
自律之重之要,弘一法师便以“自律”开讲,接着讲授“三规五戒”和“律学大意”,然后开讲《随机羯磨》,最终讲授《四分律》。前后半年时间,循序渐进,由浅及深,弘一法师引导着大家,一路走进了南山律学的圣殿,领略了南山律学的种种精微。
弘一法师出家即开始研究戒律,前后近三十年,讲授律学也近十年;但在湛山讲律的第一堂课,竟然整整预备了七个小时,足见其认真程度。《随机羯磨》讲过十几课后,因为气力微弱,便由弟子仁开法师代讲,遇到难题由仁开法师随时向弘一法师请教。弘一法师还专门编写了《随机羯磨随讲别录》和《四分律含注戒本别录》,驭繁就简,供教学使用。弘一法师离开青岛之后,湛山寺从此坚持循环演讲《随机羯磨》和《四分律》,学者们对律条制熟悉得如数家珍,湛山寺和长春的般若寺、哈尔滨的极乐寺等寺宇还一体律仪化。
湛山弘律一经传开,相识的,不相识的,远至西安、沈阳、山西、营口的学僧,一时纷纷前来湛山寺就弘一法师学律。苏州的妙莲法师,与弘一法师在此结缘,终于成为弘一法师的侍侣,直至弘一法师人间最后的托付人。
倓虚法师和少年火头僧,都对弘一法师首讲《律己》记忆犹新,尤其是讲课结束前,弘一法师规劝大家严于律己,口里不停地说着“慎重,慎重!慎重又慎重!慎重又慎重”,竟至几十遍才罢。
弘一法师北上青岛弘扬南山律教的成功,固然得力于美妙的开示讲授,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行持极严的身范,所谓感化的力量正在于此。古语说:听其言,观其行。佛教最看重的,正是信众的行为。禅宗所说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明心见性,直指人心”,换一个角度来说即是,不依赖于文字学问,完全可以见性成佛,怎么见性成佛?当然在于以实际的“行”来悟了。净土宗甚至强调,只要一心念一句“阿弥陀佛”,便可以见性成佛,这一念当然也是重在净心净行了。
未行湛山,弘一法师就已经向寺主倓虚上人约定:不为人师,不开欢迎会,不登报吹嘘。这纯粹是律己的约定,人还没有到来,那种不骛名闻利养的品格已经让人心生崇敬。
云落湛山,弘一法师那简破的行李,一下子便打动了每一个在场的人。倓虚法师在《影尘回忆录》里,专门记录了弘一法师的行李:
别人都带好些东西,条包,箱子,网篮,在客堂门口摆了一大堆。弘老只带一破麻袋包,上面用麻绳扎着口,里面一件破海青,破裤褂,两双鞋,一双是半旧不堪的软帮黄鞋,一双是补了又补的草鞋。一把破雨伞,上面缠好些铁条,看样子已用很多的年了。另外一个小四方竹提盒,里面有些破报纸,还有几本关于律学的书。听说有少许盘费钱,学生给存着。
弘一法师从大病里脱出时间不长,身体虚弱。倓虚长老想为弘一法师改善一下伙食,考虑到弘一法师持戒极严,不敢备什么好饭菜,只是吩咐送四个菜到弘一法师的寮房里。没想到,弘一法师一点都没有动。第二次预备次一点的,弘一法师仍然未动。第三次送去两个菜,弘一法师还是不吃。最后盛去一碗大众菜,弘一法师在问清之后,才满心喜悦地吃起来。
讲律的时候,弘一法师不坐课堂正位子,而是在讲堂一边另外设了一张桌子。倓虚长老说弘一法师是自谦,觉得自己不堪为人作讲师。我想,弘一法师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来之前已经约定“不为人师”,现在另设讲桌于一边,应该是为了不违背前约。我们只能景仰弘一法师行事的认真,只能拜服弘一法师言行的不二。
弘一法师的待人接物,也让倓虚长老感叹钦服不已。
无论出于是真心,还是出于装点门面的需要,权势者多喜欢附庸风雅。世俗眼里的大才子,一代高僧,弘一法师当然是附庸风雅者争趋的对象了;但却常常打破弘一法师安宁清净的心,让他总是处于无奈和扰攘之中。时有东北海军代总司令、青岛市长沈鸿烈,想见弘一法师一面,弘一法师以已经午睡相拒。翌日,沈在湛山寺请客,想请弘一法师坐主席,但弘一法师只让人带了宋人一偈赠与沈鸿烈:
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杖又思维。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宴中甚不宜。
沈鸿烈自然闷闷不乐,宴毕怏怏而去,但从此却对弘一法师的人品更加敬服。而那些年轻人,甚至是平常的学生,谁去谁见,你给弘一法师磕一个头,弘一法师照样磕一个头还给你。山东大学学生张希周等人,两次拜见弘一法师。时值“七七”卢沟桥事变,话题自然离不开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弘一法师似乎经过深思熟虑,告诫学子们:
佛门忌杀,但为抗日救国,应当不惜死!抵抗日寇为救同胞,是大仁大勇行为;杀日寇是灭魔,与佛法不违背。救国不忘念佛,念佛不忘救国!青年是国之希望,民众精华,抗日,读书,都重要,上了战场抗战第一;身在学府,书要读好,因抗日是长期之事,要沉着,急躁坏事,沉着又积极才好。
近50年之后,张希周已为古稀老人,忆及当年,依然十分激动。而今,又是30年过去,虽不是亲聆,但弘一法师那清醒、热烈而深挚的话语,依然如热风吹过我的胸臆。今天的人们,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理解或许比当初要深广得多,但弘一法师的大仁大勇,弘一法师的冷静和沉稳,无论如何都依然是我们前行的一剂良药。
当时青岛似乎已经能闻到硝烟的气味,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弘一法师事先有约,不肯中途畏战而去。在给弟子蔡丏因的信中,弘一法师坚称:
朽人前已决定中秋节乃他往。今若因难离去,将受极大之讥嫌。故虽青岛有大战争,仍不愿退避也。
时逢出家头尾二十年纪念日,正是“七七”日寇挑起侵华战争刚刚一个星期,弘一法师特意书写“殉教”二字,并附跋语:
曩在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岁次丁丑,旧七月十三日,出家首尾二十载。沙门演音,年五十八。
为民,为国,为教,为仁,为义,弘一法师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写来平常安静,不着一个字的豪情壮语,读来却字字如铁。林则徐有诗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实与弘一法师的这则跋语异曲同工。
倓虚长老和火头僧的记述里,都有弘一法师喜欢一个人独自去海边看海的细节。倓虚长老的《影尘回忆录》记得更细:
在院子里两下走对头的时候,他很快的躲开,避免和人见面谈话。每天要出山门,经后山,到前海沿,站在水边的礁石上了望,碧绿的海水,激起雪白的浪花,倒很有意思。这种地方,轻易没人去,情景显得很孤寂。好静的人,会艺术的人,大概都喜欢找这种地方闲待着。
倓虚长老是一位得道高僧,但在他的眼里,弘一法师似乎仍然是一个艺术家,这一点颇值得注意,但倓虚长老似乎还没有说尽。弘一法师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海,除了海边孤寂的情景可以让人心清凉之外,是否在雪白的浪花里寄托了渺茫的怀想?因为,浪花的尽处,有一个难以忘怀的宅院;因为,浪花的远处,遥遥的岛国,有一缕难尽的牵挂。
也许我是在臆测测,甚至是在曲解;但是,我的理解丝毫不会损伤弘一法师的光辉。自律极严的弘一法师,常常处于自警自责之中;弘一法师至情至性,自然会对大海那边的亲人怀有深深浅浅的歉意,只是这歉意常常让佛声梵香冲淡;唯有存着这份歉意,才是真佛子,真律师。心底的隐痛,总是难以为外人道,于是,只有面朝大海,逐无边浪花。
秋风时起,雁羽南归。弘一法师此行弘律已经完成,便向倓虚长老辞行,并且再次相约:不许预备盘川钱,不许备斋饯行,不许派人去送,不许规定或询问何时再来,不许走后彼此再通信。
前三条,依然还是自律;后两条,也许是弘一法师不想自己离开后人们过于怀念他,以至影响静修,所以才会有如此不近人情的约定。道是无情却有情,那无情和冰冷的背后,怎么能掩藏得住才子的如水柔情?
倓虚长老当然期望弘一法师能在湛山寺多住些日子,已经为弘一法师准备好了过冬的棉衣。现在弘一法师如约又要羽翔南国,倓虚长老是个解人,心里纵有千般留念,也不再挽留。
临行,弘一法师不停地写字,以书法结缘。湛山寺的每一位僧人,都得到了一幅“以戒为师”的条幅。寺外的人们,也都纷纷前来求字,弘一法师不忍拒绝,最后竟然写到双臂麻木,手足疼痛,仍然笔不停挥。
行前几日,弘一法师为大众作最后的开示,火头僧记之颇为生动感人:
他老说:“这次我去了,恐怕再也不能来了。现在我给诸位说句最恳切最能了生死的话——”说到这里,他老反沉默不言了,这时大众都很注意要听他老下边的话,他老又沉默了半天,忽然大声说,“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如果人心有千万光年之长,即使那份别情离绪藏在心的最远处,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份不可遏止的深情。
分别在即,弘一法师你声对倓虚长老说:“老法师!我这次走后,今生不能再来,将来同登西方极乐世界再见吧!”
果有极乐西方,但那已是另一个世界,另一重境界。斯时,斯世,斯人,斯情,真真切切,何以却?何以绝?倓虚长老的修为,仍然不免怅然若失:
走后我到他寮房去看,屋子里东西安置得很次序,里外都打扫特别干净!桌上一个铜香炉,烧三枝名贵长香,空气很静穆的,我在那徘徊良久,向往着古今的大德,嗅着余留的馨香。
9月中旬,弘一法师一行船行上海。此际,上海已经陷入一片战火之中。弘一法师穿过硝烟,飘飘而来。是应约而来,应今生不可能再有的约,应心底里只可意会的约,因为这个城市在弘一法师的心里刻下了太多的印记,因为这个城市还有此生最重的朋友,硝烟如何能够迷得住?枪炮如何能够挡得住?
终于和老友夏丏尊相对而坐。窗外,日寇的飞机正在狂轰滥炸,屋宇震动,窗上玻璃乱飞。夏丏尊有些惊悚,但弘一法师丝毫不为所动,口诵佛号不止。当此国难之际,两个知友都已老迈,前路茫茫,也许今生从此不会再有相见的机会。还需要说什么?在轻轻执手之间,在相视一笑之中,心意已经洞明。
炮火不断,但夏丏尊还是请弘一法师摄影留念。仿佛预感到今生不会再相逢,那么,且用一张照片作药,治疗那无边的牵挂和怀念吧。
凡所有相,皆是虚枉。此时的安慰,只能如此!弘一法师只能为老友再诵《金刚经》偈语: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战火纷飞之中,生命飘蓬,连草芥也许都比不上,执手相别,还能作何观之?唯有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