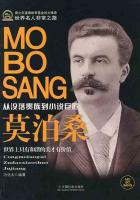四君须听从不佞之意见,不可违背。不佞并无他意,但愿君按部就班用功,无太过不及。注重卫生,俾可学成有获,不致半途中止也。君之心高气浮是第一障碍物(自杀之事不可再想),必痛除。
1918年,李叔同已经决意出家,但仍不忘刘质平的学费问题,在给刘质平的信中说:
余虽修道念切,然决不忍致君事于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君以后可以按心求学,勿再过虑。至要至要!
这些信件的语言也许有些平淡,甚至是琐碎,但字里行间满溢着的浓浓的慈父之爱,已经是任何华美的辞藻都不能比拟的了。还需要华词丽句来虚饰么?正如李叔同此时的清简、淡远、平实、纯净和安宁,透发着至为深沉的真,至为温厚的善,至为广大的美。李叔同的慈爱,如极纯极净的清泉流过,净化、滋养和慰藉了刘质平的灵魂,陪伴着刘质平走过了漫漫的人生长路。“名虽师生,情深父子”。在未来岁月里,刘质平一直像对待慈父一般地侍奉着李叔同,演绎了许多让人泣下的故事。
如果说传道授业解惑是老师的职事,那么,发现人才,爱之惜之护之,便是为师者难能可贵的品质了。李叔同发现弟子丰子恺有着不一般的艺术悟性和气质,慰勉有加,且悉心培养。当丰子恺与学校训育主任闹矛盾而几至被开除时,李叔同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主动陪丰子恺登门道歉,终于求得训育主任的谅解,保护了一棵艺术灵苗。
此后,李叔同时常约丰子恺等学生去自己的宿舍谈话,用《人谱》上的嘉言懿行来教育弟子遵循“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的准则,因为一个人无论技术何等精湛,倘没有“器识”,人品不高,也不会有大的成就,更难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丰子恺正是在李叔同人格力量的感化之下,改变了人生取向,矢志献身艺术事业,终成一代艺术大家。
处无为之世,行不言之教。李叔同那不绝如缕的慈爱,如无声的好雨,不经意地便滋润了弟子李鸿梁的心田。老师不仅推荐李鸿梁到南京高师为自己代课,而且把南京那边的一切都悉心地安排过了,甚至细到连吃饭须两双筷子、两只调羹都要交待一番。行前一早,李叔同便来到李鸿梁住的旅馆,请学生共进早餐,送学生上火车。直到火车开动了,李叔同还站在那里目送着火车。
不由想起朱自清的《背影》。当朱自清父亲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再也找不着的时候,坐在火车上的儿子一时感从中来,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当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李鸿梁看见清瘦的老师孤独地站在那里,翘首而望,我不知道李鸿梁的心里会涌起什么样的感觉,是融融的慈父般的仁爱么?是酸酸的对于慈父的那一种牵挂么?我想,李鸿梁心底里那至柔至软的部分一定会被掀起来了,他能不潸然泪下么?
化一缕蔼蔼之光,哪怕只是一豆之微之弱,也足以照过漫漫长路,点亮和温暖一颗又一颗灵魂。从心开始,向心贴近,心便热了融了化了,热做人生里的一片赤诚,融做人生里的人一道风景,化做人生里的一阵和风。此时,李叔同已经深具悲悯情怀、勇猛精神和精进力量。所以,当舍监夏丏尊诉说学生宿舍财物被盗而又苦无解决办法时,李叔同十分认真地对好友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室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夏丏尊当然未肯如言,但是李叔同自己却实行了一回。国画大师潘天寿在浙一师读书期间丢了一件毛衣,李叔同在课堂上宣布,如果窃衣者不将毛衣归还,自己身为老师惭愧无地,将誓死绝食以殉教育。事后,这件毛衣果然悄悄地回到了潘天寿的手里。
人品既好,才情又高,李叔同便把浙一师的图画和音乐课程教得风生水起,魅力无穷,注定成为风气的引领者。李叔同抛开当时图画课依照《铅笔画帖》和《水彩画帖》临摹的方法,力倡面对实物或风景写生,并且制定了一套完整周详的教学计划。七年的教学生涯,李叔同将西洋画法和作曲法引入教学。1913年李叔同主导创办的校刊《白阳》,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艺术教育校刊。《白阳》杂志首发的由李叔同填词作曲的三部合唱曲《春游》,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部合唱曲;而同时刊载的李叔同的文章《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近代欧洲文学史。李叔同于1914年安排的人体模特写生课,成为中国人体模特教学之先河。
一棵植物在地里生长的时候,总要千方百计地营造出绿色的氛围。艺术家大约与植物无异,当他在某一处生活下来之后,总要千方百计地营造出艺术的氛围。从本质上说,艺术和绿色具有一样的色彩,都趣向生命的自由和美好。李叔同本来和吴昌硕等人就时相往来,一来到杭州,便自然地融入了西泠印社。在浙江第一师范,李叔同支持学生成立了“乐石社”和“漫画会”,更被师生们推为“乐石社”的社长。“乐石社”得到吴昌硕等名家的支持,连名士柳亚子都成为其社员。“漫画会”在李叔同的指导下,编印过一本《木版画集》,收进了李叔同的木刻作品,李叔同便成为中国第一个倡导且创作现代版画的人。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职的时候,李叔同还倡导创立了“宁社”。
时在1915年的秋天,李叔同应了同学江谦的聘请,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图画、音乐教师。多年之后,江谦忆及李叔同在南京高师的活动,写下《寿弘一大师六十寿甲诗》及“跋语”:
鸡鸣山下读书堂,廿载金陵梦未忘。宁社恣尝蔬笋味,当年已接佛陀光。
乙卯年,谦承办南京高等师范时,聘师任教座,师于假日倡宁社,借佛寺陈列古书字画金石,蔬食讲演,实导儒归佛方便也。
时间相隔得太久,且一味地为了表达李叔同的佛慧,文字里便没有了人世艰辛的细节,也滤尽了心为形役的苦况。其实,李叔同当时正艰苦地仆仆于途,半个月在南京,半个月在杭州,且还要不断地奔往上海,每次又只能选择坐夜车。谁能想到,这样一个疲于奔命的人,曾是一个富家阔少,又是一个留洋才子,更是一个艺术大家!也许,蜷伏在空气浑浊的夜行车里,于似醒似睡的倦怠里,已经人到中年的李叔同会生起无限的沧桑之感。时空无垠,人世茫茫,韶光不再,过尽千帆皆不是,心似飘蓬无所依。嘈杂里的寂寞,浑浊里的孤独,李叔同那一颗敏感的心不知不觉间便有了另外一种况味,一种别样的向往。
世上所有的真才子,也许都过于理想化,也许才情都太超迈,便不能融于世俗,又难以为世俗所容。李叔同曾评价自己:“长而碌碌无所就。性奇僻,不工媚人,人多恶之。”前一句有自谦和自伤的意思,后一句倒是颇为中肯,洵属自知之明。在浙一师的七年,总的来说,李叔同的心境比较平和,但依然难以排解与生俱来的寂寞和孤独,依然时时生起不快的情绪,竟有四次想离开杭州。也许是勾留西湖的那一汪柔波,也许是难舍杭州那一种宁静和缓慢,也许是不忍弃别那一班相濡日久的学生和朋友,或者竟而至于是冥冥里的那一声声梵音的召唤,李叔同终于没有离开杭州。
艺术教育家,教育艺术家。做一个艺术教育家不难,难的是做一个教育艺术家,所谓“求经师易,求人师难”。李叔同不但授学生以艺,而且把授艺本身当作一种至高境界的艺术,用无上的才情,用极高的智慧,用全部的身心,创造出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点亮一个又一个心灵,圆满一个淑美的梦,完善一个大悲悯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