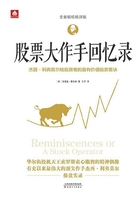“淑妃娘娘早上安抚夫人躺到床上去睡觉后,回瑶光殿用了午膳,然后就出宫了。”
“出宫?”昭尹皱了下眉头。
“嗯。她去为江晚衣践行了。”
“哦?”
秋叶飘零,染了点点霜,城郊孤亭,无语话凄凉。
姜沉鱼一身文士打扮,身后跟着书童打扮的怀瑾,来此为江晚衣送行。
半年前,江晚衣离开此地,百官云集沿途欢送,风光一时无二;
半年后,他被贬出京,两袖清风,连个仆从都没有,只有一个药箱,依旧沉甸甸地背在消瘦的肩头。
这等境地,看在姜沉鱼眼中,也只有一个“世态炎凉”的结论了。
她从食盒里取出茶壶,再将茶倒进浅口竹叶杯中,双手捧了呈到江晚衣面前:“沉鱼以茶代酒,恭送师兄,此去天涯,山遥水远,望君珍重。”
江晚衣也用双手接过,一向温文的眼角,竟有微微的湿红:“多谢。”说罢,一口气喝下,正要将茶杯递回,姜沉鱼摆手道:“此杯就当是临行之礼,送给师兄。他日若遇到需要钱财的地方,将杯子送到最大的当铺里当了,也能解一时之急。”
江晚衣听她这么说,知道这必定是很值钱的杯子,一时间百感交集,最后低叹道:“山雨欲来风满楼,沉鱼,你要小心。”
姜沉鱼淡淡一笑:“那要看是什么风,什么雨……”
“你……”江晚衣踌躇再三,终于还是忍不住道,“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姜沉鱼的眼中依稀有了泪光,她抬起头,泪眼朦胧地望着他,用梦呓般的声音低声道:“如果我收了手,那么,公子的枉死算什么?颐非的冤屈算什么?曦禾的发疯算什么?师走的残疾算什么?而师兄你的被贬……又算什么?”
江晚衣心痛地喊道:“沉鱼!”
姜沉鱼深吸口气,面色恢复了平静,仿佛刚才一瞬间的失态不过是看见的人眼花而致,然后,唇角弯弯,盈盈一笑:“无论如何,恭喜师兄脱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还归你原本就想要的生活……你放心,曦禾我会好好照顾的。”
江晚衣久久地望着她,眼中明明灭灭,最后一一沉淀成了别离:“如此……保重。”
几只乌鸦飞过长亭,风声呜咽,芳草衰黄,这一年的秋天,来得比往年要早。
江晚衣离去的身影,被夕阳长长地拖在地上,愈显凄凉。
“小姐,天色也不早了,咱们回宫吧。”怀瑾将一件披风披到姜沉鱼身上。
而姜沉鱼凝望着长路尽头几乎已经看不见了的江晚衣的背影,幽幽道:“怀瑾,我要是能跟师兄一起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该多好啊……”
“小姐……”怀瑾没办法回答。
姜沉鱼摇了摇头,打个哈哈道:“不过师兄可不要我。算了,我还是乖乖回宫吧,别忘了,我可马上就要当璧国的皇后了。皇后呢……”
皇后……
想当年,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几曾想,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世事讽刺,莫过于斯。
是夜,当昭尹抵达宝华宫时,看见的就是这么一幅画面——
各色宫灯明媚又柔和地照耀着五色斑斓的琉璃宫,晶石铺就的地板上,铺着纯手工编织的长毛地毯。曦禾坐在地毯上,穿着一件新衣,因为刚刚沐浴过的缘故,她的头发都还是湿的,像浸了水的白纱。而姜沉鱼,就坐在她身后,用一块干毛巾帮她擦头。
光影交错,姜沉鱼的手,细致温柔。
两位绝世的美人,就那样构筑成了一幅极为赏心悦目的画面,久久留在了在场的每个人心中。
罗横正要喊驾,昭尹抬手做了个禁止的手势,似乎也不忍心让人打破眼前这温馨祥宁的气氛。
姜沉鱼帮曦禾擦干头发后,用根带子帮她把头发扎好。这才起身,正要走,曦禾却反身一把抱住她,着急地喊道:“娘……不走……不走!”
“好好好,我不走,不走。”姜沉鱼温柔地对她笑了笑,“不过呢,我也是要做事情的呀,曦禾你先自己玩一会儿好不好?”
曦禾眨了眨水晶般剔透的大眼睛:“娘要去卖面吗?”
姜沉鱼想了想,点头:“嗯……去卖面。”
曦禾眼睛一眯,满意地笑了:“好。带点回来哦,晚上吃面!”
“好。晚上吃面。”总算哄好了,姜沉鱼又将清洗过的姬婴的袍子递给曦禾玩。在曦禾理所当然地伸手接衣袍的时候,她眼底闪过一丝踌躇,似乎是有点不舍得,但最终还是松了手,接着便看见曦禾抬起头甜甜地对她笑,笑得天真又无邪。
姜沉鱼想,她终归是没办法对这个人心硬。
曦禾身上,仿佛寄托了她的一部分情感,那部分情感在她自己身上被压制了、磨灭了、不复存在了,但却在曦禾身上得到了延伸。
多想跟她一样,无牵无挂,肆意妄为地一疯了之,那样就不用清醒地面对姬婴已经死去的事实;不用面对心中一向敬为天人的父亲的丑陋一面;不用面对片刻都不会平息的风云际幻的宫廷争斗;不用面对人来人去,缘散缘尽……
姜沉鱼在心中暗暗叹息着,站了起来。把毛巾等物交递给一旁的宫人后,走至殿门处参拜昭尹:“给皇上请安。”
昭尹“扑哧”一声笑了。笑得姜沉鱼莫名其妙,只好茫然地抬头看他。
昭尹将一只手伸到唇边轻咳了一下,虽敛了笑,但眼波依旧似笑非笑,于是姜沉鱼便更茫然了,忍不住问道:“皇上?”
“把你的手伸出来。”
姜沉鱼闻言一呆,第一个反应却是将手缩到了身后,然后又想起这个举动不对,只好僵硬地将手收回,颤颤地伸到昭尹面前。
修长洁白、保养得当的十指上,有几道新添的伤口,是刚才替曦禾洗澡时弄破的,因为曦禾不肯让别的人碰,所以全过程都只能由她独自完成。不想昭尹眼睛那么尖,一眼就看出她受了伤。
而昭尹的笑,自然是笑她一介千金,笨手笨脚。因此,姜沉鱼双颊微红,惭愧道:“自小父母宠溺,倒是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好了……惹皇上见笑了。”
昭尹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悠悠地嘱咐了一句:“别忘了上药。”说罢,转过了身子,抬头看着夜空。昭尹成日里笑眯眯的,偶尔发火,要不阴笑要不暴怒,总之,表情一向很生动,鲜少有太平静的时候。因此,一旦如此刻这般不笑,就显得心事重重,有种难言的抑郁。
见他心情看上去不是很好的模样,姜沉鱼忍不住问道:“发生什么事了吗?皇上。”
昭尹轻轻地叹了口气:“你看此地风和日丽,怎能想像千里之外的江都百年大旱,颗粒无收。”
此事姜沉鱼倒也有所听闻。
江都是璧国出了名的鱼米之乡,一个都的收成就占了全国粮仓的五成,因此可以说,江都富,天下足。今年本也好好的,却不知为何,自入夏后就没再下雨,烈日暴晒,河道枯竭,竟将庄稼都给活活晒死了。再赶上老城主任满、新城主交接的当口,等大旱的消息奏报到朝廷时,已经晚了。
“皇上想好前往江都处理此事的人选了吗?”
昭尹斜睨了她一眼,挑眉笑了:“怎么?你又要毛遂自荐么?”
姜沉鱼回头看了看曦禾,摇头道:“臣妾倒是想去,却怕是不能了。”
“哦?真看不出,你竟然会把曦禾看得比国事重要。”昭尹说这句话时的口吻很难说清是嘲讽还是感慨。
姜沉鱼盯着他的眼睛,沉声道:“臣妾只是觉得,江都之事,有人可以比臣妾做得更好,臣妾不是必需的,但是曦禾夫人……却只有臣妾了……”
昭尹整个人一震,久久,忽然伸出右手,慢慢地贴在了她的眼皮上。力道轻柔,没有惩罚的意思,仿佛只是不想再被那样一双眼睛所注视。
姜沉鱼连忙后退一步,低下头,再不与帝王对视。
昭尹似乎也觉得自己这样的举动有点失仪,便笑了笑,收回手道:“朕给你个立功的机会如何?”
“嗯?”这位帝王的心思,她是越来越无法捉摸了。
“这个抗旱赈灾的人选,就由你代朕挑选吧。”昭尹说着还眨了眨眼睛。
姜沉鱼忍不住问:“谁都可以么?”
“嗯。”昭尹摆明了一副“朕不信你敢说个不好的人选出来”的样子。
姜沉鱼几乎想也没想,就说出了名字:“薛采。”
昭尹又露出一副“果然是他”的表情,轻轻地叹了口气,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姜沉鱼连忙跟上前追问道:“不行么?”
昭尹还是不表态,于是姜沉鱼又问:“真的……不行吗?”
昭尹继续前行,姜沉鱼咬唇道:“皇上?”
回应她的,是如细沙一样滑入耳中、不轻不重、不紧不慢,有着责备的色彩却丝毫没有责备的语气的一句——
“你真烦。”
姜沉鱼停下了脚步,注视着那个渐行渐远没再回头的背影,这一次,是彻彻底底地呆住了。
前往江都处理旱灾的人选在第二天早朝时就宣布了,果不其然地选了薛采。
面对璧王的这一决定,朝臣自然是大为意外,震惊之后,便开始百般阻挠,高呼不可。
给出的理由不外是:赈灾不是儿戏,不是殿前娱君那等场面上的小事,怎能派个毫无经验的黄口小子去?更别说薛采不但已经不是贵族公子,还是个低三下四的奴隶,怎能担任此等重任?
当朝上吵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之时,龙座上的年轻帝王悠悠然地说了一句话,顿时把所有人都给镇住了。
昭尹说的是——
“既然如此,就谴羽林军骑都尉姜孝成一同前往,随程主持大局吧。”
羽林军骑都尉姜孝成是谁?
右相姜仲的儿子,姜贵人和姜淑妃的哥哥。不止如此,众所皆知,他还是个——大草包。因此,皇上居然说让他跟着薛采一起去,不是乱上添乱么?
群臣无不被震得风中凌乱,便连姜仲自己也万万没想到,皇上竟然会把这个山芋丢给自己。刚想反对,但昭尹已经起身道:“此事就此决定,退朝。”
一干宫人连忙摆开阵仗伺候主子退朝,于是昭尹就在满堂臣子或不敢置信或痛心疾首或莫名其妙的痴呆目光中优雅退场。
而等他回到御书房时,姜沉鱼已在百言堂中等候,看见昭尹,虽然矜持,但眼底的笑意遮掩不住,自眉梢唇角处尽数流了出来。
昭尹似笑非笑地睨着她:“你满意了?”
姜沉鱼盈盈下拜:“皇上英明。”
“哦,你倒是说说看,英明在哪儿?”昭尹施施然地往锦榻上一靠,像猫一样地微微眯起了眼睛。
姜沉鱼恭声道:“臣妾浅薄,妄度圣意,若有失言,请皇上恕罪。”
“朕赐你无罪。”
“臣妾以为,皇上让孝成跟薛采同去,理由有三。第一,现在的薛采确实不能服人,派他前往江都,名不正言不顺,但若让我哥同去,就大不一样。虽然我哥……”姜沉鱼说到此处,有点儿想笑,但又生生忍住,“不是干实事的料,但起码资格、身家都摆在那儿。而且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如此重要的事务,也是一个可以扬名立万的好时机,我爹怎么都会暗中帮他把路铺得顺顺当当,做起事来,自然也就事半功倍。”
“嗯。”昭尹点点头,示意她继续往下说。
“第二,旱灾,与雪灾不同,非一夜之难。地方官员早该有所警觉,却迟迟不肯上报,粉饰太平,而今终于拖得无可收场了就随便找个借口将原城主调离,找个新人去收拾烂摊子。若收拾好了,自然是皆大欢喜,收拾不好了也没关系,皇上追究起来,反正有替罪羊在……”姜沉鱼冷笑,“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他们仗着天高皇帝远,事事欺上,皇上就索性将计就计,派薛采和我哥去,一个年幼,一个草包,看在他们眼中,想来也不会太过重视。孰料这才是皇上真正的用意——赈灾固然重要,清污更是势在必行。等他们纷纷被定罪抄家之时,就知道自己错得究竟有多么离谱了。”
面对她如此恭维,昭尹也只是淡淡一笑,依旧不肯表态:“第三呢?”
“第三……”姜沉鱼深吸口气,表情忽然变得凝重了起来,“继薛氏垮台,姬婴离世,如今,满朝文武,可以这么说——大多碌碌,无出挑者。”
昭尹原本慵懒如猫的表情也霎时变得很严肃。姜沉鱼此话说得极重,若是换了别的时候,或是被第三人听去泄露了,都是一场大祸。可她,就那么柔柔弱弱地站在他面前,一脸平静地把这句话说出了口……
他的心,一下子就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变得又是酸涩又是疼痛起来。
“是时候该重新选拔人才了,皇上选中薛采,就是要昭告天下——高官重任,有才者居之。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无论你曾有多么不光彩的背景,都没有关系。”
姜沉鱼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不料昭尹听了却是一笑:“是么?”
和这位帝王相处久了,也就逐渐掌握到了他的一些性格特征。比如他此刻眼皮也不抬,只是左唇轻轻一扬——这种笑容,就说明他并不认同。
于是姜沉鱼便停了下来,问道:“皇上,臣妾说错了么?”
昭尹的目光掠过她的肩膀看向后方,用一种很难描述的表情道:“薛采……是不可能重回官籍的。”
停一停,补充道:“可重用,但不可赏。”
虽然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姜沉鱼已赫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一股寒意自脚底油然升起,一瞬间,手脚冰凉。
是对美玉蒙尘的痛惜。
是对帝王无情的悲伤。
亦是对世事残酷的醒悟。
亲自亡于昭尹之手的薛氏,是不可能在昭尹之手重新站起的。那是一个帝王的尊严。也是一个朝代的规则。
纵观历史,为什么很多冤案都在当时无法申诉,要等改朝换代后才能翻案昭雪?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规则在。
所以,薛采无论多么出色,无论为国立下多少功劳,都不可能加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