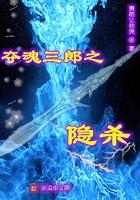脚上的两只拖鞋都不见了,丛好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它们找齐。两只拖鞋相隔着十几米远的距离,让人诧异是怎样的外力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她是缓慢的。缓慢地走出公园,缓慢地汇入柳市繁华的街道。她的下身湿淋淋的,沾满了尿液,口腔里弥留着烤鱿鱼的味道,眼镜也被狗舔花了,市声鼎沸的夜,在她眼里成为了一团模糊的色块。
丛好在这样的夜里,看清楚了柳市浮华背面的凄凉,那种衰败,是与兰城毫无二致的。她迷路了,一直缓慢地走着,直到身边的人渐渐稀少,街道变得空旷。
丛好的身体里被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撕扯着,她多么想纵声哭泣,同时又感到是多么的厌倦和消极,厌倦消极到麻木的地步,连流泪似乎都是显得多余的。
远远过来一个人,像一片纸那么单薄,近些后,就被风刮过来。是小丁,他哭着说:
“你怎么了,我找了你好久!”
丛好望着他,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她说:
“我——被强奸了。”
小丁像鬼一样发出一声凄利的惨叫,转身狂奔而去,只一瞬间,就消失在黑暗里。
丛好回到向宇汽车修理厂时,天边已经泛起了灰白的晨光。她在柳市转了一夜,累了就席地坐在路边休息一会儿。
老丛蹲在厂门口的路阶上等女儿。看到丛好的影子出现在街角,他就跑了过来。丛好的脸色苍白着,似乎并不是面无表情,而是浮着一丝若有有无的笑意。她的裙子很脏,左脚的脚踝上还有一些血迹。女儿的状态令老丛不敢发问,只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
丛好一声不出地回了宿舍。老丛想询问些什么,但是被她用那道布帘挡住了。
小丁在那天夜里消失在了黑暗里。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向宇汽车修理厂。
没有人关心小丁的去向。在柳市,一个打工青年的出现和消失,根本不会成为一个问题。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情,当然也成为了一个不足挂齿的秘密。
老丛把小丁的那间宿舍争取了过来。他有充分的理由——女儿这么大了,谁都可以理解他的难处。丛好就搬进了那间小宿舍。小丁消失了,但那些书却留下来,现在由丛好陪着它们睡。
睡在那些书的旁边,丛好常常感到困惑,无端地产生出疑问:真的有小丁这个人吗?这个人和由他形成的记忆,都是那么令人怀疑。丛好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家乡,也是一个丛好根本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就像兰城之于他一样,那里对于丛好也是可以当做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他的纯洁,其实是一件怯懦的外套吧?他是假的,这样的男人就像一把空气,随时可以吹散在风里。
丛好想,是梦吧,一个逼真的梦,把这个扣着电焊面罩的人栩栩如生地送给她,只是为了让她在梦中经历一个绝望、沸腾的夜。
但是这个结论也不是非常可靠,丛好经常会被手腕上那根玻璃珠子串成的手链吓一跳。它是一个物质的存在,晶莹剔透,打磨出的棱面略显粗糙,有的部位对准了什么割下去,甚至可以当做刀子使用。看到它,丛好就有着从梦里给现实带回证据的荒谬感。
丛好的神经由此变得非常衰弱,经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睡着时又经常做梦。
我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拉了一条尼龙绳,用来挂一些女孩子不宜公开晾晒在外面的小衣服,夜里灯黑下来后,月光洒进来,这条绳子的阴影就将小屋横切成两半。我常常瞪着眼睛,目光在绳子的两侧摇摆,渐渐就制造出这样的幻觉,仿佛那是一道空间的伤口,或者是一条梦、醒之间的界线,自己的目光从这一半跃到另一半,就会立刻跌入到活生生的梦境中。即使这个时候我依然睁大着眼睛,也会不能自拔地身临梦魇中的一切。
在梦里,一条大狼狗舔着我的身体,那温热的舌头,陡然将我卷离了地面,让我在悬空的状态中变得焦灼和潮湿。
我在不能入睡的夜晚,一边抟弄着那根手链,一边读完了身边的那些书。
然后我开始写作,把自己那些惊悸而亢奋的梦记录下来。那些书成为了我最初的文体范本。
就像小丁所说的那样,“人是可以自己提高自己的”。
女儿从身边搬开,老丛和大脸盘刘姨的关系就进展得非常顺利,披荆斩棘,一路凯歌到1993年的国庆节,他们结婚了。
老丛兑现了他的诺言,在举行仪式的前一天晚上,把结婚证拿给丛好看。丛好翻了翻那本证书,没有格外的意见,只是觉得,照片上的这个刘姨,脸盘实在是大啊。又看到了父亲的名字:丛楠生。——居然有着几分斯文和清雅。这个名字几乎被丛好遗忘了,如今又重新和父亲对上了号,让父亲仿佛被重新命名和确认了一样,再生一般,具备了他所应当具备的那些尊严。
这个时候的丛好,整个人的内心都趋向安静了。少女被一场沸腾的梦涤荡着,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一般,性格呈现出一种虚无的姿态,似乎也不觉得这个“丛楠生”有多么面目可憎了。
丛好打量着父亲,发现父亲胖了些,面色也很红润,完全不像一个兰城人了,心里面居然有些替父亲高兴。
丛好说:“这个刘姨对你好吗?”
老丛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半天才哼哼着说:“好,还好。”
丛好教导父亲:“那你也要对人家好,要像个男人的样子。”
老丛受宠若惊地愣住,不由得便“要像个男人的样子”地挺起了胸。
仪式挺简单的,就在厂子附近的一家饭馆里举行。父亲请了工友们,在一种粗糙的热闹中宣告了新生活的开始。丛好坐在饭桌上,却想到了自己家里那盘端在餐桌上的鸡。
刘姨又给丛好准备了礼物,一件白色的连衣裙,这一次,丛好收下了,并且对刘姨说了谢谢。
来柳市对于老丛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在这里运气变得好起来,有了新的女人,而且这女人还给了他一个家。刘姨自己有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两人结婚后,老丛就搬了过去。他态度端正地征求过丛好的意见,问她是不是也跟着搬到新家去住。丛好拒绝了,她要留在那间小宿舍里。
老丛还不死心,说:“把你一个人留在厂里我交代不过去。”
丛好问:“你要跟谁交代呢?”
老丛说:“跟我自己啊,我是你爸,在这世上,咱们俩是相依为命的人。”
“相依为命”这样的词让丛好难过,更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她已经习惯了那间小宿舍,在里面读书,在里面做梦。工友们对她这个向宇汽车修理厂里唯一的女性也很好,比如每天专门会把浴室留出一个小时给她使用。而且,不为人知的是,她已经在那间把角的小宿舍里结出了自己的果实。
丛好把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寄给了一家文学刊物。刊物也是小丁留下来的,丛好不过是循着地址将自己的作品寄了出去。她住在这间小宿舍里,似乎是继续小丁走了一半的路,前面的歧路,小丁已经替她跋涉过了,而她后面要走的,已经是坦途。
没有一点悬念,寄出的作品很快就发表了出来。丛好丝毫不感到意外,非常自信。她的写作是被梦托举着的,也像是躺在一块敦厚的飞毯之上,有种梦幻般的性质。而梦,是没有边界的,在梦里,没有所谓的奇迹,一切都是必然的。
起初丛好只是把稿件寄出去,连地址都不留,只隔些日子去报刊亭看看新出版的刊物,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上面,就买一本回来。走在路上,翻到里面要求她速与编辑部联系的启事,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这样的方式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发表了近十万字的小说,渐渐地没了新鲜感,丛好才开始在寄出的稿件上落下向宇汽车修理厂的地址。
收到第一张稿费单的时候,丛好不由得想起了小丁。她去邮局把钱领了出来,只有一百二十块钱,拿着这笔钱,丛好一个人勇敢地出了门,也是先在门口的河粉店吃了份牛肉河粉,然后就只身在夜晚的柳市徜徉了许久。她什么也没有买,一百二十块钱回来的时候还是一百二十块钱。躺在床上,丛好灵机一动,用那张电焊面罩罩在了自己的脸上,夜晚一下子变得格外安全,让她睡了一个无梦的好觉。
向宇汽车修理厂的老板潘向宇,在一天中午敲响了丛好的房门。
柳市作家协会的一位主席是潘向宇的朋友,他向潘向宇打听一个叫丛好的人,说这个人写出的东西“蛮有意思”,但一直隐藏着身份,最近终于有了下落,居然地址在潘向宇的厂子里,他让潘向宇落实一下。潘向宇以为对方是在和他开玩笑,听完就丢在脑后。但对方隔三差五打电话催问他,他才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神奇。潘向宇找来具体负责厂子的经理询问,果真是有这么一个叫丛好的人,还是个女孩子,是自己手下一个职工的家属。这个结果令潘向宇顿感好奇,他决定亲自来见一见这个女孩子。
丛好还在睡觉,她的白天与黑夜是颠倒过来的。丛好以为是父亲,迷迷糊糊爬起来去开门。门外却站着一个挺拔的男人,红色T恤统在裤腰里,小腹微凸着,手背在身后,扬着刮得青青的下巴。
丛好愣一下,急忙缩回门里,因为她只穿着简单的睡衣。穿好衣服重新打开门,潘向宇依然保持着刚才的那副姿势,纹丝不动,甚至让人感觉他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
丛好是认识潘向宇的,她见过这个男人,知道他是这个厂子的老板。潘向宇被让进屋,一眼看见满床的书,就什么都信了。那条横在半空中的绳子让他有些不知所以,又看到一条醒目的白色短裤,扔在一张电焊面罩上,不由得就转身去打量它的主人了。丛好意识到他看见了什么,很自然地弯腰把那条短裤收拾起来,团一下,塞在枕头下面,整个动作不慌不忙。
丛好说:“对不起,我这里没有坐的地方。”
潘向宇在自己的厂子里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她说“我这里”,完全就是一种主人的口吻,这就使他这个实际上的老板显得像一个客人了。潘向宇看着这个单薄的女孩子,心里起了微妙的感觉。
“既然这样,我请你吃午餐吧。”潘向宇提议说,“我们边吃边谈。”
丛好点一下头表示同意。潘向宇看着她不慌不忙地把暖瓶里的水倒出来,就着一只搪瓷脸盆洗脸刷牙,头发都不用梳,只向后拢起,用一块手帕扎住。离开兰城后,丛好的头发就一直留着了,如今已经长过了肩头,并且有些自然的蜷曲。
潘向宇没有见过这么从容的女孩子,从容到一种冷漠的地步,更没有见过不化一点妆就出门的姑娘,以至于丛好将脸盆里的水开门泼在屋外后,做出“开始吧”的表情时,他都有些回不过神来。
潘向宇开车带着丛好去了一家中式快餐店,简单地吃了顿午餐。吃的过程中,他询问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关于丛好写作的事,却是只字未提。
“丛好?”他问道。
丛好点点头,并不奇怪这个人何以知道自己的名字。
“丛师傅是你父亲吧?”
潘向宇的这些问题都不像是问题,他是在陈述,不过是用了疑问的句式。
丛好再次点了点头。
问了丛好的年龄后,潘向宇同样问道:“你怎么不上学?”
丛好的回答令潘向宇刮目相看,她沉静地说:
“人是可以自己提高自己的。”
潘向宇摸着自己的下巴,点头表示认可。
吃完后,潘向宇就送丛好回了修理厂,将她放在厂门前,一直目送着她走了进去。厂门外挂着牌子,“向宇汽车修理厂”这几个字,让潘向宇落实了自己在这个空间里的那种主权感。
潘向宇是典型的柳市人,可以代表这座城市的主流趋势:乐观,有头脑,有野心,蒸蒸日上。大学毕业后他就开始经商,从开汽车修理厂,卖走私车,到经营加油站和物流业,三十岁就已经拥有了可观的财富。
丛好进入到潘向宇的视野里,令他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潘向宇憬然发现,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一种女孩子,完全在他的经验之外,像一株神奇的植物,生长在一块他从来未曾涉足过的神秘之地。而对于那些人迹罕至的风光,潘向宇这类人有着天然的征服欲,探险啦,登山啦,这些行为,就是他们释放这种欲望的一个途径。
现在,潘向宇的这只探索之手就伸向了丛好。
丛好那间进门就是床的宿舍,是潘向宇见到过的最为古怪的一个空间。床上堆积如山的书,横空的绳子,以及那条醒目的白色短裤与一张电焊面罩的奇异搭配,都令潘向宇有种震撼的感觉。潘向宇发现自己被一种新鲜的刺激调动起来了,说不清是这个女孩子让他蠢蠢欲动,还是这间小宿舍所展现出的那种诡谲让他亢奋不已。
平时潘向宇基本上是不去修理厂的,那只是他产业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现在他开始关注那里,坐在公司的办公室里打电话过去,命令修理厂的经理给丛好换一间大些的宿舍,“再配一个书柜”。但反馈回来的消息又一次令他感到了着迷:丛好拒绝搬出去。潘向宇决定了,一定要把这个女孩子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