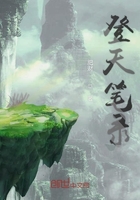自从水泥厂和化工厂的筹建工作开始以后,运输中转站的事儿更多了,水泥厂的设备堆积到钢厂盘圆钢筋的另一侧,没等运完,化工厂的蒸馏塔又从省城运来排队,等到夜间从狼洞隧道通过。
一些小件便随着索道天车运到四水索道运输站,忙活了一个夏天总算把积压在中转站的工厂设备都运到河套地带,毛先武感到松了口气,就在夜间巡逻时冲黄花花说道:“厂里让我找个助手,我已写了个材料,让你当中转站的秘书,以后你可得负起责任,帮我多想想中转站的事,别出差错。”他看黄花花很高兴地笑了,就又寻思起来黄棋这一招果然很灵,就想趁热打铁来打探一下尤建美的消息,又说道:“上次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到省城看化工设备的机会,可是你也没告诉我是在哪个夜总会见到的尤建美,害得我利用晚上睡觉的时间打听了好几个夜总会也没见到尤建美。”
黄花花心直口快地问道:“钢厂改成公园的夜总会你去了吗?”
毛先武疑惑地说:“钢厂改成公园我知道,没听说那里边还有夜总会。”
“我就是在那个公园里的夜总会见到了尤建美,那个公园可漂亮了,还修了好几条小河,两边都是树丛草坪。”
毛先武听到这里心中不禁萌生出个新的念头:如果自己能有辆汽车一天就能跑个来回,到省城就不用去等长途车了。次日中午连饭也没吃就跑到小镇去买了一辆上海产的黑色小轿车,回到中转站后,贾风等四人都以欣赏和羡慕的口吻来祝贺师傅,唯独黄花花撅着嘴埋怨道:“师傅!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就去买车了!你就是开到省城北郊公园也不见得能找到尤建美。其实,我也只跟建美见过一次面,等我第二次再到钢厂公园那个俱乐部改成的夜总会,就没见到她,都怪我,要是不惊动她就好了。”
毛先武发现黄花花现出十分后悔的神色,便笑着宽慰道:“这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改革开放以后,生活都提高了,私家车很多,买辆车去看看钢厂改成的北郊公园也很值得,特别是那个钢厂俱乐部也很有纪念意义。钢厂搬迁的动员大会实际上就是在那里召开的。”
黄花花听到毛先武讲起了在俱乐部演出十八罗汉斗孙悟空的故事,很感兴趣,听得很入神,当她听到省京剧团领导不让毛先武演A角,似乎很气愤,不禁激发起一种打抱不平的情绪,插言道:“师傅来到钢厂中转站工作是对的,干吗让你给他们打小旗,唯一可惜的是把老婆丢了,成了光棍啦!”
蒋月也跟着打抱不平,结结巴巴地说:“等找到尤……尤建美,我……我好好教……教训教……训她。”
毛先武心平气和地说:“建美出走,也不能怪她,我也有很大责任,哪个人没有自己的理想和爱好,爱唱歌,没有过错,爱在大庭广众唱歌,也是可以理解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愿意去显示自己,去表现自己,这种需要,同吃饭结婚生儿育女的需要一样,都是人的生活需要,直到她出走以后,我才想明白。”
黄花花看到毛先武语重心长的陈述,似乎十分悔恨自己,就很有感触地说道:“等找到尤建美以后,跟她好好解释解释,其实她也很伤心。”
宋山嬉皮笑脸地取笑了一阵说道:“噢!师傅买车是为了找师娘啊!”
贾风一本正经地说:“才不是呢,师傅是为了让我们大伙学学开车,让你们多掌握一点本事。”
毛先武笑道:“还是我的大徒弟会说话,对呀,会开汽车就是方便么!”
小个子吕雪说:“找到尤建美就不用背了,用汽车拉回来。”
蒋月拉开车门坐到驾驶位上,打着火开了一圈,下车后说:“这车还行!”
贾风、宋山和吕雪都跟着排号上车去试开,争先恐后的样子很热烈。
毛先武心中暗自窃喜,十万块一辆汽车又换来了个信息,即便开车去省城的钢厂公园也未必能找到尤建美,还是不能轻举妄动,只能等得到准确信息后再付诸行动。毛先武在观察几个徒弟争抢学习开车过程中,心里又萌生出一个新的主意,重点是要培养黄花花的开车技术。如果她能每周回省城一趟,去打探尤建美的信息,那比自己亲自出马方便多了,于是便在晚上巡夜时,鼓励黄花花学开汽车。当黄花花考取了驾照后,又唆使她在周末开着车回省城探望其母亲,黄花花也心照不宣,每次由省城回来都向毛先武报告说她到北郊公园夜总会的情况,唯独没有告诉他关于尤建美的消息。毛先武并不去追问,他知道如果黄花花见到了尤建美肯定会告诉他的,既然车子借给了她,就不会亏待自己的,果然在秋后的一个周末,黄花花开车回来就向他神秘地说:“师傅,这个礼拜天我见到了尤建美,她又回到了北郊公园的夜总会唱歌了,我没敢惊动她,你自己去看看她吧!”
毛先武喜出望外,笑盈盈地说:“太感谢你了,花花,真是上天不负有心人,我去见她一面,你把中转站的事管好,千万别丢了钢材。”
毛先武开着车来到了省城钢厂旧地址北郊公园,原先的钢厂俱乐部已经挂上了公园夜总会的霓虹灯,来往游人络绎不断,为了不惊动尤建美,他按黄花花的做法找了个偏僻的角落坐下,想静静地欣赏前妻浑圆低沉的女中音伴唱。可是歌舞厅里总有些爆豆似的掌声和尖锐的叫嚣声,使他感到不舒服,不过他并不像过去那么反感了,也许这同妻子的出逃和协议离婚有关。那种自家宝贝给别人共产了的自私观念好像有点烟消云散了,继而出现的却是一种失落感和冷漠感。周围欢腾的人群什么时候走的,他全然不觉,直到清场的服务员请他让路扫地,毛先武才从回忆的梦乡中醒来,不禁下意识地问道:“尤建美呢?她什么时候走的?”他从服务员摇头晃脑的莫名所云中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尤建美已经改名叫吴泊女了,于是便又改口道:“噢,我说的是吴泊女,她什么时候还唱呢?”
服务员漫不经心地说:“明天晚上还唱!”
毛先武找了家宾馆睡下,一连看了三个晚上,才又开车回到小镇中转站,黄花花见面就问:“师傅你同她接上头了吗?”
毛先武摇摇头叹息道:“你的做法对,不惊动她,就可以老同她见面。”
时间飞一样地过去,每当毛先武想念起前妻的时候就开车去一次省城北郊公园夜总会,欣赏一次这位缩脖端腔前妻的音容笑貌。在一次夜巡中,黄花花好奇地问道:“师傅,你是不是觉得世上女子唯独尤建美才最美?”
毛先武摇摇头叹息道:“我还从来没去比较过,哪个女子最美。”
黄花花沉默了一阵,自言自语道:“我觉得你对她的感情不完全是丈夫对妻子的感情,也有点好像是儿子对母亲。”
毛先武在内心深处对这句话发生了共鸣,也自言自语地叹息道:“好像是啊!在我双目失明以后,母亲不在家,父亲成天上班,我连大门都不敢出,甚至连每天吃的药在哪里都找不到,那时候建美闯进了我的生活,我真觉得她像母亲一样温暖可亲,就像黑暗中忽然透进视野中的一线光亮,使我对生活又恢复了希望和信心,就不再想自杀了……”
黄花花仿佛受到了心灵的启迪,喟叹道:“真是患难夫妻恩爱深,我真后悔,我没有经受过这种折磨,也没有能力去承受爱情的考验。”
毛先武在沉寂中好像听到黄花花的语气中夹杂着惋惜和哭泣的声音,不禁从悲凉的追忆中又回到了现实,下意识地抚慰道:“花花,你真像个小孩,直率,天真,很容易感情冲动,你一点也没有错,我很感激你对人的诚实坦率,你替我又找到了建美,我很感谢你,我会感谢你一辈子,你相信我说的话不是客套,而是真心话,你相信吗?花花。”
黄花花微微点头,啼笑皆非地说:“师傅很执著,我信,如果帅哥都能像师傅这么执著就好了,可惜我没长前后眼,总吃后悔药。”
毛先武想避开黄花花的后悔思路,摆脱开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希望能获得更多前妻的信息,就挑开话题,兴致勃勃地问道:“我听建美唱的歌,好像全是德德玛唱过的,是不是?”
“才不呢!我去听时,她唱过不少新歌,都不是模仿德德玛。”
黄花花的情绪扭转地很快,说罢就亮开嗓子轻声唱道:
“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来来回回只是一场空……”
黄花花唱够了,就十分纳闷地说道:“师傅,我总想不明白你为什么总跑那么远去看她呢?图的是什么呢?”黄花花好奇地问。
毛先武茫茫然地自言自语道:“我总觉得想念她,看了以后就放心了。”
冬天落了一场雪,毛先武又在周末开着自己的上海黑轿车到省城北郊公园夜总会欣赏前妻的歌,不料她竟没有出场,一问主持人,说:“吴泊女住院了,伤势很重。”毛先武便来到了医院,白衣护士说:“是美容美体中心送来的病人,是颈部拉伤,现在还没脱离危险。”
原来是尤建美自从成为女中音第一名之后,总想到省城乐团去工作,谈判了几次都因她脖子太短未被录用,她也明白,夜总会里灯光暗淡,缩脖端腔的生理缺陷可以用服装遮饰,而正式乐团的演出场合总是灯光明亮,其短脖子的缺陷必暴露无遗。于是便想到去美容美体中心探讨一下,可否做些拉伸,老板一问她年龄才刚到二十五岁,便蛮有把握地说可以拉伸出一定的距离,而尤建美去试验医疗几次后,觉得很有效果,就一再催促老板不断加大拉伸力度,并掏出大把钞票进行鼓励,美体老板见钱眼开,就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你多给钱,我当然可以多给你吃点进口的好药,来促进你软骨生长,不过万一出点事,我可负不起责任。”尤建美一听便顺口说道:“我自己负责,不会让你赔偿,只要脖子不断就行。”尤建美对于脖子的结构和功能缺乏生理知识,又加上追求美体心切,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自己的脖子拉伸出来,即便赶不上白云小姐那么长,也会赶上嫂嫂的长脖子了,那该多好,自己就可以从缩脖端腔的体貌特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没有生理缺陷的歌手,名副其实的德德玛第二,到那时前夫毛先武就再也不敢说我是德德玛第二百五了。尤建美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她也并不满足夜总会里的掌声,她要在省歌舞团或乐团中当主角,去赢得那些正经八百的音乐爱好者的掌声和欢呼声。到那时谁还敢再说我总和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在一起,等到钢厂北边的化工厂旧址改建成体育馆和歌剧院以后,自己就去毛遂自荐,就凭全省女中音第一名这个头衔再加上摘掉了缩脖端腔的帽子,他们凭什么会不录用我呢?没有理由。尤建美越想自己的未来越美妙,尽管美体老板一再问她的脖子在拉伸过程中有没有酸痛感,尤建美咬紧牙关地硬挺着说:“不痛,不痛!”老板又嘱咐道:“要是很痛,那就是拉伸到了生理极限,千万要说呀,好给你减压。”尤建美在过分紧张中忽然咳嗽了几声,这意外的震动使她顿感天昏地暗,疼痛难忍不禁喊道:“哎哟……”在拉伸极限中绷断了颈部筋骨。
毛先武见到前妻尤建美时,她已是双目紧闭,呼吸微弱,不能说话,医院把他当成患者家属令其交款后进行护理,毛先武抽空赶紧给尤创新打电话报告这一不幸消息。尤创新回电说:“我正处理一件生意,让我后爹去看看再定。”毛先武知道她后爹是野狼沟村医院院长兼中医。当他赶来看望时,尤建美已能睁眼,只是说话吐字不清还咳嗽。尤老五对毛先武说:“这种病情极少见,咱们还是采取保守疗法,送回家去等建公回来,再做定夺。”二人将尤建美用汽车带回野狼沟医院,尤创新看了以后,对毛先武说:“你的任务完成了,我代表他哥向你表示感谢,你自由了,不能让你背这个包袱,我来护理。”
毛先武怎肯撒手不管,焦急地说道:“我要亲自护理,只有我在建美身边我才安心,我不能离开她。”
经过一个月的专心护理,尤建美已完全恢复了神态,只是不能活动四肢,说话的声音也十分微弱。对毛先武的问寒问暖使她总是泪流满面,悄声向毛先武说道:“我求你件事,能帮我个忙吗?”
毛先武忙不迭地问道:“你说吧,什么事,我一定能办!”
“你给我弄瓶安眠药,别让我遭罪了!”她绝望地流下热泪。
“你想干什么?建美你还能好,还能再唱歌!千万别想不开。”
“我这样拖累你们,于心不忍,我不能再唱了,快让我闭上眼睛吧!”
毛先武快活地向她安慰道:“过些天,春暖花开,我带你去看咱们西山河套工业旅游区,我给你定制一把带电脑控制的轮椅。我推你到处走走,让你散散心,你就会完全康复的。你不能大声唱,可以小声唱么,就唱给我一个人听,另外给你安个麦克,我早就希望你只给我一个人唱,现在好了,我就是你的观众。”
轮到嫂嫂尤创新来接班护理时,看到毛先武正在指挥几个工人在安装防盗网,她指着不锈钢防盗窗笑道:“人家楼下都不安防盗窗,你也不怕人家笑话!”
当毛先武把妻子尤建美想服安眠药自寻短见一事说了之后,尤创新便冲小姑尤建美一本正经地批评道:“先武找你可煞费苦心,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先武也会跟你一块走,那就等于你亲手杀了他……”说得尤建美又热泪盈眶。
尤创新发现堆积在沙发上的衣服大都有许多开了线的裂缝,她知道这是尤建美坠窗逃走时,把衣被当绳子用给拽开的,就去拉开抽屉寻找针线和剪刀,想给缝缝。可是找遍了整个房间都没找到,等到毛先武回来接班一问,毛先武才把柜门用钥匙打开,一看里边不光有针线和剪刀,连菜刀和刮胡刀都锁了起来,不禁叹息道:“你也真够心细了,母亲对婴儿也没你这么周到。”
当毛先武向嫂嫂尤创新打听她哥哥尤建公什么时候回来时,尤创新又笑道:“他说要等我生孩子的时候才回来伺候月子。”
毛先武向躺在双人床上的妻子尤建美一努嘴,悄声埋怨道:“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尤建美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我和我哥都希望你们俩能替我们完成这个特殊任务,我拜托了。”她反反复复地念叨着。
她从被里探出两只手在空中摇晃着,毛先武以为妻子在要什么东西,就立即走到面前,妻子用左手抓住丈夫的一只手,又继续摇着右手喊道:“嫂嫂!”当尤创新赶过来问时,尤建美又用右手抓住嫂嫂尤创新的手,然后将他们俩人的手合并在一起按住,继续反复念叨着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