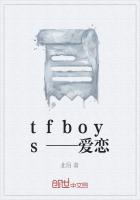除了摄影,大眼刘还让夭夭体会了另一种快乐。他很难有片刻的安静,游泳,登山,攀崖,在乡间的小道上奔跑。他的身体天生就是运动的,在天地之间运动。他们是疯狂的,草地上,树林中,山谷的溪流边,都成了他们做爱的温床。刚开始这种无遮无拦的野合让夭夭很紧张,不过很快她就坦然接受了。树成了他们的观众,草也成了他们的观众。天上有飞鸟,鼻间有花香。夭夭有了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她躺在树林中,她的身体好像铺陈了整个树林,而大眼刘不过是其中一棵树。她匍匐在草地上,她的身体就是整个草地,他是其中的一根草。她睡在春天里,她的身体就是春天,春暖花开。她在冬眠,冬天就是她的身体,银装素裹。有一次,在夏天,他们在流水中游动着,戏耍着。大眼刘的身体像手掌一样托住了她的身体,他们在水中飞啊飞啊,不知飞向了何方。她的身体成了水,成了鱼。如果不是大眼刘清醒,也许那一次她就会沉睡河底,永远上不了岸。
这些疯狂的日子,大眼刘替夭夭拍摄了许多写真照片。他总能找到那么多场景,夭夭在开满野花的草地上奔跑,睡在满地红叶之上,一棵沧桑的古树,一堵风侵雨蚀的老墙,爬墙虎有力的茎就像无数的手指。夭夭脱去衣衫,她的身体泛着某种光芒。明亮的,柔和的,带着玫瑰红,或镀上了古铜色。她的身体不只是身体,而是身体的雕塑,活的雕塑。她能够变幻一万种颜色,一万种形状,一万种表情。也许她的身体原本就是这样的,真实,可又无可捉摸。有一天,大眼刘拉着夭夭参加了一次大型的野外人体拍摄活动,几个女孩子在众多的镜头下追逐着,嬉戏着。她们是他们请来的人体模特。模特,写真,人体艺术。夭夭想他们真能找到语言,身体就是身体,不需要这么多花花哨哨的语言,也不需要这么多虚伪的装饰。无论是欲望,还是他们说的人体艺术,他们都在贪恋她们的身体。这些词语只不过是他们的借口,夭夭取笑过大眼刘。
他们的疯狂最终酿出了苦果。夭夭怀孕了,她的身体在变形。原本平坦的小腹慢慢隆了起来,像揣了一个小小的包裹。这个包裹是个魔,是会生长的癌,她怎么也包裹不了它,就像谢沁儿无法包裹她的身体一样。她在舞台上笨拙了,她的身体像灌了铅。她扭动不了她的腰肢,更不敢裸露她的身体。她害怕它会吞噬她的身体。她必须将它除掉,将它从她的体内驱逐出去。她不敢上谢沁儿所在的医院,大眼刘陪同她去了一趟省城。她躺在手术台上,那种锥心的痛险些将她的身体掏空了。她以为自己会那样死去。夭夭的身体残缺了,她的一部分扔进了医院的垃圾桶。这是对她的惩罚,对她放纵的惩罚。可夭夭又想,如果早知道保护自己的身体,她就不会有这个遭罪的过程。如果谢沁儿和陈雪知道如何保护她们的身体,那夭夭和酒酒就有可能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了。夭夭的出世也许就是对谢沁儿的惩罚。
8
谢沁儿同尹师傅的关系是个谜团,让夭夭很费解。她的父亲是不是尹师傅,还是她的父亲另有其人,谢沁儿为什么对她隐瞒这些,这一连串的问题纠缠着夭夭。谢沁儿是夭夭的亲生母亲,可制造夭夭身体的另一半——父亲,现在何方。就算尹师傅不是她的父亲,至少他是谢沁儿的熟人,或许熟知谢沁儿刻意隐藏的这些秘密,有可能他会帮她解开这个谜团。
夭夭怀着这种希望去接近尹师傅。从外表看锅炉房是个庞然大物,可内部空间差不多让锅炉全占去了。夭夭进去时尹师傅正在往炉膛里添煤,根本没发觉有人进来了。火光从炉膛里泼出来,染得他一身红亮。他的背有些驼,已经显露了身体的老态。锅炉房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煤气,夭夭咳嗽了一声,尹师傅才抬起头,煤铲都未放下就僵在了原地。夭夭的到来让他很是意外。夭夭只好向他笑了笑,说,我渴了。尹师傅慌忙丢下煤铲,穿过过道,钻进了锅炉房右侧的屋子。进去老半天,才捧出一只小桶似的茶缸,茶缸里结了老厚一层茶垢。他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塞满了黑泥。这只手老了,他的年纪看上去比谢沁儿大一些。夭夭接过茶缸却不喝水。尹师傅憨憨地瞅着夭夭,两只手掌不住地摩挲着,表情有些发窘。夭夭同他的谈话也不顺畅。你是我妈的朋友吗?夭夭问。是,哦,不是,是不是。尹师傅的回答结结巴巴,后来可能感觉连他自己都不明白在说什么,便开始摇晃脑袋。夭夭不得不重复了一遍问话,尹师傅又多摇了几次脑袋。你认识我妈妈?夭夭又问。不认识。尹师傅又摇了几下脑袋,可接着又点头承认,哦,认识,认识。也许他想他同谢沁儿在一所医院上班,不认识她有些不合常情。你是谢沁儿的女儿?他反问过夭夭一次。夭夭点点头,之后的谈话再也没有什么结果,也没法往深处谈。尹师傅不知是不善于同女人交流,还是故意装憨,表达的意思总是含糊不清,夭夭听得云里雾里。也许谢沁儿同他早串通好了,让他在嘴边加了一把锁,夭夭离开时想。
不管谢沁儿和尹师傅如何掩饰,夭夭断定他们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她想到了另一个人陈雪,也许她有可能知道。有段时间,夭夭同酒酒特别走得近,她们本来就是少时的伙伴,这内在的原因深究起来恐怕是谢沁儿和陈雪的关系起着微妙的作用。谢沁儿和陈雪的关系看起来冷淡,但陈雪是进出北门街那座老院子唯一一个自由的人。正是因为这种自由,才透露出她同谢沁儿的关系非同一般。夭夭接近酒酒,目的在于接近陈雪。酒酒并不知道夭夭玩的心眼,从小到大,夭夭都是一个让她信赖的朋友。酒酒不同于夭夭,酒酒天生就是安静的,甚至有些不合群。夭夭同一帮孩子疯玩,踢毽子,荡秋千,老鹰捉小鸡,酒酒就在旁边坐着,一动不动盯着她们看。她的眼神小时候就很迷离,完全不像一个小孩子。夭夭生在二月,酒酒生在同年四月,夭夭是姐姐。夭夭平常疯着,对酒酒却是照顾有加,酒酒在谢沁儿面前也替夭夭守口如瓶。夭夭对酒酒的照顾也只限于外表,酒酒会自己照顾自己,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什么活都会干。陈雪偶染病痛时,也是酒酒端茶送水。长大后,谢沁儿的拘束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背地里夭夭依旧疯狂。她画眼描眉,抹口红,涂胭脂,画指甲。谢沁儿恨不得将她的手指甲脚趾甲全剁了。她的恨终究解决不了问题,夭夭的身体该红的地方依旧红着,甚至她还想过文身,因为害怕针刺的痛苦才放弃了。酒酒同夭夭刚好翻了个,谢沁儿的教育没在夭夭身上产生影响,却熏陶了酒酒。酒酒依然文文静静,在一家影楼做收银员,每天端端正正立在柜台前。夭夭也揣摸不透酒酒内心有什么想法。酒酒有过一些小动作,比如她利用上班的便利,偷偷拿过几本影集同夭夭一块观看。都是客户没来得及拿走的婚纱照,画面上的装束几近相同,洁白的婚纱,被摄影的对象一律捧着花,机械地面对镜头,机械地笑着。她们的身体是笨拙的,僵硬的,夭夭很不喜欢这样的照片。酒酒却是无比羡慕,眼睛里都有了光芒。酒酒还给过夭夭多次的意外。有一次她拿过一本影集,里面全是大眼刘的照片,像是他的写真集。嬉笑的,扮着鬼脸的,沉思的,都是夸张的表情。他的眼睛为什么那么大,酒酒用手摩挲着大眼刘的照片喃喃说。她的话让夭夭咯噔了一下。还有一次,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夭夭偷看到酒酒身体的一个细部,在她的肚皮上,接近小腹的位置,有一块细小的文身,是一只鸟在振翅欲飞。那一刻,夭夭都有些震惊了。就是这个细小的发现,夭夭彻底改变了对酒酒的看法,她读不懂她,但她对酒酒没有说破。
酒酒进入北门街时四岁或者五岁,这个时间夭夭没有确切的记忆。后来她才慢慢了解到酒酒为什么会来到北门街,完全是因为陈雪婚姻的失败。酒酒进入北门街一次,陈雪的婚姻就失败一次。前前后后加起来,酒酒进入北门街五次,陈雪也就经历了五次失败的婚姻。第一次,陈雪嫁给了某个村子的一个木匠,木匠姓张,酒酒跟着姓张。陈雪忍受不了村子里单调的生活,苦熬了几年,最终一走了之,又无处可去,才进入了北门街同谢沁儿为伴。第二次陈雪嫁给了一个酒鬼,酒鬼姓胡,根本不在意酒酒姓什么,只要他有酒喝。陈雪的日子跟着过得酒醉糊涂,颠三倒四。陈雪的第三任老公是个茶厂下岗的职工,锄了半辈子茶蔸,下了岗锄不了茶蔸,就拿陈雪当茶蔸天天锄,锄锄都是折干断茎。陈雪回到北门街时养了大半年,才将身体上的淤紫消除。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婚姻,陈雪依然不肯安静,像是对结婚离婚上了瘾。后来的婚姻时间越来越短暂,第四次过了半年,第五次仅维持了一个多月。酒酒跟着改了三四次姓,在北门街搬进搬出三四次,后来干脆单独租了房,同陈雪分开过起了日子。陈雪可能也厌烦了,不再搬进北门街。北门街院子的西厢房始终空着,哪一天如果陈雪搬回去住了,也不是什么怪事。
夭夭原以为酒酒会知道陈雪很多事情,了解了陈雪说不定谢沁儿的历史也就弄清楚了。夭夭始终坚信自己的判断,谢沁儿和陈雪她们有着必然的联系,甚至有可能有过一段相同的历史。夭夭接近酒酒也是徒劳的,对于酒酒出生之前的生活,陈雪没有吐露过半个字,她们不约而同对夭夭和酒酒隐瞒了那段历史。酒酒也羞于谈论陈雪。夭夭也问过酒酒,想不想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酒酒的回答很简单,知道与不知道又有什么区别,无非让她再改一次姓,不姓陈就是姓马姓周或者姓梁姓赵。她甚至说了句让夭夭吃惊的话,她见了男人眼睛就放光,恨不得将他们吞到肚子里去。酒酒说的是陈雪。酒酒似乎将陈雪从她的生活中剔除了。而陈雪也好像忘记了有这么个女儿,她的热情全部投入了结婚离婚的游戏。夭夭想她必须去找陈雪,直接追问她。
夭夭找到陈雪时陈雪正同一个半老的男人谈论什么,嘀嘀咕咕的,两颗脑袋凑在一块儿掰也掰不开。这是两具正在衰老的身体,男人的头发白了一半,女人的身体变了形,已经不见了腰身。夭夭在他们旁边站了老半天,男人才注意到她,他示意陈雪,陈雪才回过头。陈雪的眼睛很迷惑,不知夭夭为何会找她。她将男人打发走了,男人走了几步远回头看看她们,走几步又回头看看她们。陈雪朝男人挥了挥手,男人这才不再回头了。夭夭的问题很直接,尹师傅是她父亲不。面对夭夭逼视的双眼,陈雪丝毫没有怯意,而是一脸的警觉。你问这个干什么,你该去问你妈。陈雪同样直视夭夭。那一瞬间,夭夭明白了她突破不了这个女人,可又不甘心。那么酒酒的爸爸呢?他是谁?夭夭反戈一击。夭夭想错了,这个问题并没有起到反击的效果。她原来就此追问过陈雪。陈雪的脸只是灰暗了一下,很快就将夭夭的问话堵死了。这个就更不该你来问了。陈雪的声音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
9
大眼刘对夭夭说,马赛是苏小卒的父亲,亲生父亲。夭夭狐疑地盯着大眼刘,不怎么相信他的话。他只好补充说,苏小卒随他母亲姓苏。大眼刘说这话的时机不对,夭夭认识苏小卒没多久,正同他火热。她以为大眼刘的话隐藏了某种阴谋,他不可能吃醋,他对于她的身体是不留恋的,他留恋的也许只有相机里虚无的影像。可夭夭听见这话时身体莫明其妙颤抖了一下,有种冷在她体内游动。她的身体似乎在向她暗示什么。
认识苏小卒之前夭夭做过一个梦,她梦见自己赤身裸体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巷子里奔跑,转过一个弯,又转过一个弯,已经记不清转过多少弯了,巷子依然曲曲折折。后来她发现巷子两旁的墙壁不是砖砌的,也不是水泥的,而是人墙,一具具赤裸的身体,死死盯着她,向她呵着冷气。巷子起风了,是阴风,越吹身体越阴冷。夭夭只有拼命奔跑,一步也不敢停歇。她必须尽快找到出口,从巷子里逃出去。巷子里的光线越来越暗淡,黑暗越来越黏稠,她好像身陷泥沼中,每迈一步都非常吃力。她大口大口吸着气,努力挪动自己的身体。她有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是在奔跑,而是向黑暗中跌落,下跌速度越来越快,耳边都能听见飕飕的风声了。她不知道自己会坠落何方,她的眼前虚无一片。她觉得好像是在自己的小肠内奔跑。拐弯,拐弯,没有尽头。转过一个拐角,突然无路可去,巷子让什么堵死了,那东西像只企鹅又像只熊猫。快进来吧。那东西的肚子裂开一道缝隙,有个声音冲她喊叫。她什么也没想就一头撞了进去。她的身体碰撞在一种坚硬的物体上,哎呀一声,她痛醒了。摸摸枕边,大眼刘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只有她的身体孤独地占据了整张床。
夭夭反思过这梦,她好像在恐惧什么,又像是会遇见什么。大眼刘的身体是不可靠的,他有他的自由,随时可以离开。其实任何一个人的身体对别的身体都是不可靠的,不值得信赖,它们有各自的自私、任性,又有各自的完整,和不可分割。喜欢一个人的身体,可谁也不可能带走一个人的身体。夭夭胡思乱想着,想不出什么结果。夭夭一个人在舞台上跳着舞,唱着歌。她是孤独的,她的身体是孤独的。这样的时候很容易让她怀想刀鱼。那逝去的日子多么美好,多么温馨。她欢歌劲舞时刀鱼就在同一个舞台表演软体柔术。这种场景现在只有大眼刘的照片中才有。该死,又是大眼刘,照片。她身体的一部分似乎被那个虚幻的世界软禁了。她想到刀鱼,可立刻又想到了大眼刘,由一个身体过渡到另一个身体,她在他们之间摇摆,徘徊。夭夭无比感伤。
有一天,夭夭的目光在舞台之下漫无目的地游弋。她突然遇上了一双眼睛,那双眼睛放着光,光芒全照耀在她的身体上。那种光芒是稚嫩的,纯真的,夭夭身体的某个部位让他照亮了。可是她瞧不见他的身体,他躲藏在一只巨大的企鹅中,在舞台下来来回回。他在给商家散发宣传单。一群孩子跟着他走来走去,他们摸摸他藏在翅膀下的手,又瞧瞧他的眼睛。他们对企鹅体内的那个身体充满了好奇。有孩子模仿他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得滑稽可笑。他们的父母让他们逗乐了,在呵呵笑着,可分不清谁是谁的父母。夭夭想到了那个梦,梦里那个堵在巷子中间的动物,原来就是企鹅。她要遇见的就是这个藏在企鹅体内的人。
我认识你,你叫夭夭。苏小卒从企鹅的肚子里钻出来,向她傻傻地笑着。我叫苏小卒,你的忠实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