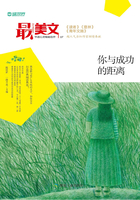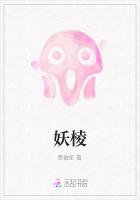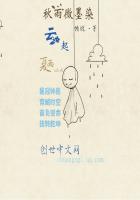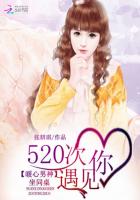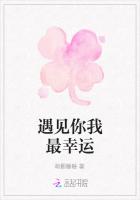风是长翅膀的,它被天性推怂着,恣意奔放地行走在天地间。它有时是激情的,有时是温婉的,有时是目中无人的,有时是漫无目的的。它没有方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情绪。
徐志摩如风。
当初徐志摩在美国的克拉克大学学银行和社会学,而后又进入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他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日后会成为一名诗人。他说,二十四岁以前,我对诗的兴趣远不如我对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趣……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那时的徐志摩还醉心于哲学和政治。
徐志摩的情趣很广泛很多时候如风,开始他对尼采着迷,他说,我仿佛跟着查拉图斯脱拉登上了哲理的山峰,高空的清气在我的肺里,杂色的人生横亘在我的脚下。他在尼采的哲学世界里悟到了,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向上的精神。后来,他的喜好又转移到英国哲学家罗素。他认为罗素的思想言论,仿佛是夏天海上的黄昏,紫黑云中不时有金蛇似的电火在冷酷地料峭地猛闪,骇人的电闪,在你头上眼前隐现。正是因为崇拜罗素,恣意纵情的徐志摩放下唾手可得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头衔,跑到伦敦的剑桥来找罗素,只为“想跟这位20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那时,他生命中还没有诗,只是想当一个大政治家。可惜的是,当时的罗素因为战时主张和平和他的私生活事件,已被剑桥大学给除名,随即他去周游世界到中国去了。徐志摩的愿望落空了。他只得失望地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政治经济博士。
失意的徐志摩在伦敦时感寂寞,他是个生性爱热闹又乐于交往的人。很快,他就和留英的中国留学生和来英国考察的中国学者打得火热。这当中有陈西滢和章士钊。通过他们,他结识英国作家狄更生,并在他的帮助下进入了剑桥做了特别生。
徐志摩是风,当他置身于英国知识名流之间,并大量阅读西方名家的作品,又对文学陡然增加了浓厚兴趣。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像一粒随风飘来的种子,在本性浪漫且充满灵性的徐志摩心里落了根。正如他后来所说,数十年前,我吹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是照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潜化了我的气质。
在康桥,徐志摩过得很惬意,每天忙着散步、划船、吸烟、骑自行车跟朋友聊天,或独自带本闲书到郊外,躺在青气葳蕤的草地上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在康桥那个自由浪漫的王国里,形成了他的艺术人生观以及浪漫气质。他建立了自己的理想。
徐志摩说,在康桥,任选一个方向前行,都能让你获得半天的逍遥和性灵的补剂。道边有清荫与美草,可供你随时休憩。如果你爱花,这里多是锦绣的草原。如果你爱鸟,这里多是巧啭的鸣禽。如果你爱人情,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
在徐志摩眼里,康河是世界上最秀丽的一条河。是康桥奇异的月色,让诗潜入了他的气质,进入了他的灵魂。他如此迷恋和赞美康河,是因为在美丽的康桥,徐志摩曾有一次最美丽的邂逅。
人生有许多的偶然,偶然到一个地方,偶然遇见一个人,而那人好像早在你梦中出现过许多次,让你一点也不觉得陌生,你为她改变了性情,你为她改变了命运,这就叫缘分。
在伦敦,徐志摩结识了一位来英国考察的中国客人,这个人叫林长民。他是民国的一位著名人物。早年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一生基本都交给了政治,最高司职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这一年他官场失意带着女儿漂洋过海来到伦敦讲学。林长民是梁启超的政坛好友,私交也极好,而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学生,早就倾慕其人了。
在伦敦阴霾潮湿的天空下,林长民和徐志摩相识了。他们俩一个是才华横溢、英俊潇洒的年轻诗人,一个是谈吐豪爽、幽默倜傥,进而思政事有成、退而求文章的书生逸士。俩人又都巧是浙江人,真是他乡遇知己。在伦敦阴冷的天气里,俩人坐在壁炉前谈政治、谈文艺、谈人生,有许多的观念竟然惊人地相似。他俩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竟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有了林长民这个朋友,让徐志摩觉得雾雨蒙蒙的伦敦竟透出融融的暖色。于是,徐志摩成了林长民在伦敦寓所的常客。后来,他之所以去林家那么勤,不仅仅只是为了林长民。
当徐志摩第一次去林长民家时,是一位少女为他开的门,她穿着一件浅色的中式上衣和一条深色的长裙,乌黑的头发梳成两条辫子自然地搭在肩上,她的脸庞像粒白皙润泽的莲子米,清澈的眸子泛着粼光,精致秀丽的五官,像朵含苞欲放的白莲。她是林长民的女儿,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林徽音(后改为因)。徽音取自《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徐志摩第一次看见林徽因,仿佛觉得她是从云端处走来的,纤尘不染。她那恬静典雅的笑容能让再浮躁的心都安静下来。徐志摩是见过大世面的男人,从人间天堂的杭州到北京,从自由的美国到浪漫英法,也可谓是阅人无数。但这个女孩子给他的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有她在,屋里就犹如有清雅隽永的兰草,散发着馨人肺腑的幽香,让他的经络里有着从未有过的舒畅。每次他与林长民谈话时,林徽因总是双手托着腮,静静地坐在他们身旁倾听着,她俏丽的身姿,散发着纯净的气息。有时在他们的谈话间,她也偶尔插嘴说二句,竟然都是精辟之理。原来眼前这个小女孩,不仅娇美如花,而且还秀外慧中。
渐渐的,徐志摩发现她读书很多,她活泼跳跃的思维、明澈清新的识见、对文艺作品的理解和悟性都远超出了她的年龄段,是个可以与他们对话的朋友。此时,林徽因正在英国圣玛丽学院上学。她的英语很好,发音很准,是地道的牛津音,吐音说话婉转清脆。让人听起来充满了音乐的韵律。徐志摩被她深深地吸引着,感到林徽因的可爱不仅只在她的外貌。
作为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是非常幸运的。他的父亲最早接受西方文明,对女儿也是非常开明的。林长民在北洋政府任职时,举家从上海迁到北京,并把女儿林徽因送进了英国教会办的贵族学校。让女儿的谈吐都充满了高雅的气质。以后父亲又带着她远渡重洋,游览欧洲列国。她是领略过大江大河壮丽、小桥流水委婉的聪明女孩。她的见识,她的经历并非是一般人家的女孩子所能比拟的。
徐志摩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林长民,林长民骄傲地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
徐志摩与林徽因这样一个美丽惊心又绝顶聪明的女孩相遇,他的心,像被一丝明丽的阳光射入,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此时的徐志摩受西方教育数年,骨子里已经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崇尚爱、自由、美。他感情的闸门瞬间被打开,爱的浪花奔涌而出:
今晚天上有半轮的下弦月,
我想携她的手,
往明月多处走——
一样是清光,我说,圆满或残缺。
园里有一树开剩的玉兰花;
她有的是爱花癖,
我爱看她的怜惜——
一样是芬芳,她说,满花与残花。
浓阴里有一只过时的夜莺;
她受不了秋凉
不如从前浏亮——
快死了,她说,但我不悔我的痴情!
但这夜莺,这一树花,这半轮月——
我独自沉吟,
对着我的身影——
她在哪里,啊,为什么伤悲,凋谢,残缺?
徐志摩还是常常去林长民的家,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更多的是为了林徽因。他在林徽因身上发现了许多梦寐以求的东西。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内心封存了许久的爱,像岩浆一样汹涌澎湃地喷薄而出,别的东西全顾不得了。
十六岁的林徽因正是少女情窦初开的年纪,她的青春如花,她的貌美如花。二十四岁的徐志摩也正是诗人最好的年龄,他俊逸的面容,一双含着诗意的眼睛,注视着谁都能让春花羞涩让飞鸟惊心。他如玉树临风的气质和迷人的微笑让许多女子为之着迷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