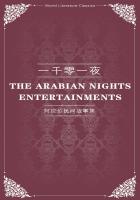徐志摩虽然身在北京,但只要一有机会就赶回上海。从他到北京不到半年,就先后来回奔波了八次。小别胜新婚,生性浪漫的徐志摩多么希望陆小曼看见他回来能立刻扑上来给他一个香吻。然后两人相依偎着,卿卿我我地诉说相思之苦的情话。可是,每当徐志摩风尘仆仆地赶回家时,总是看到这样的情景,陆小曼与翁端午横卧烟榻,看见徐志摩回来并不起身,只是颔首示意她看见了,然后继续跟翁端午一起吞云吐雾着。每当徐志摩看到这情景,心里一阵阵说不出的酸楚,从北京赶回时的那一腔热血,犹如被一盆凉水从头浇到底,心里凉透了。徐志摩忍不住说,我的好太太,说起咱们久别见面,也该有相当表示,你老是那坐着躺着不起身,我枉然每回想张开胳膊来抱你亲你,一进家门,总是扫兴。我这次回来,咱们来个洋腔,抱抱亲亲如何?这本是人情,你别老是说那是湘眉一种人才做得去。就算给我一点满足,我先给你商量成不成?我到家时刻,你可以知道,我即不想你到站接我,至少我亦人情的希望,在你容颜表情上看得出对我一种相当的热意。更好是屋子里没有别人,彼此不致感受拘束。况且你又何尝是没有表情的人?你不记得我们的“翡冷翠的一夜”在松树七号墙角里亲别的时候?我就不懂何以做了夫妻,形迹反而得往疏里去!那是一个错误。我有相当情感的精力,你不全盘承受,难道叫我用凉水自浇身?
自从跟陆小曼结婚后,徐志摩被父亲断了经济来源,再加上要供陆小曼在上海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让那个从前花钱不问出处的徐志摩为钱愁得快白了头。
在北京,徐志摩每月除了给自己留下很少的零用钱,其余的全都给陆小曼带回去。可是,陆小曼的开销太大,不管他如何努力赚钱总赶不上她膨胀的奢侈消费。
钱,钱,钱!成了诗人徐志摩的噩梦。睁眼是孔方兄闭眼也是孔方兄,他成了锱铢必较的算账先生,后来他在给陆小曼的信里已经少了过去许多的浓情蜜意,大多数是为钱而焦虑着。
正如果有余钱,也决不自存。我靠薪水度日,当然梦想不到积钱,唯一希冀即是少债……
徐志摩在北京一边极力节俭着,一边拼命地赚着钱。常常是钱刚一到手还没暖热,就赶紧带回上海供陆小曼花销。可是不管他再怎么努力赚钱,拼命节省,也难负担得起上海家里的巨大开销。负债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徐志摩在北京也时常窘迫的捉襟见肘身无分文,连胡家的仆妇都瞧不起他说,这个寄食的客人一脸寒酸,别人这样为他跑前跑后的,最后连个赏钱都从指缝里蹦不出。徐志摩一生爱朋友喜欢热闹,最后因为兜里没钱连朋友家都很少去了。
有次陆小曼写信要他回上海,他悲哀地回信说:
至于我回去问题,我哪天都可以走,我也极想回去看看你,但问题在这笔旅费怎样报销,谁替我会钞。我是穷得寸步难移;再要开窟窿,简直不了。
你是知道的,手头无钱,要走可得负债。如其再来一次偷鸡蚀米,简直不了。
陆小曼接到徐志摩的信,心里一阵酸楚,她不是不爱徐志摩,而是控制不了自己奢侈的生活。接到信后,陆小曼马上从家中找了二件值钱的首饰让家人当了,赶紧给徐志摩寄去,这才让他得以回到上海。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徐志摩热衷搭乘免费飞机的原因之一。
北京,一个让徐志摩准备起飞奋进的地方,最后竟因为钱,被拖得苦不堪言。徐志摩无奈地对陆小曼说,我既然决定在北大做教授,上海现时的排场我实在担负不起。夏间一定得想法布置。你也得原谅我。
这两个历经波澜走到一起来的爱人,又因为生活弄得焦头烂额,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孽缘吧。
人失意的时候厄运往往会接踵而来,1931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在徐志摩来北京不久,他最挚爱的母亲在硖石病故了。
古老的硖石有自己的生活宝典,婚事必须是父母做主,八台大轿抬进来的媳妇方能认可。凡是小官自己胡闹带回来的都不作数。对于陆小曼,硖石人用冷酷的眼光看着她,在他们看来,这个所谓的儿媳妇根本不算数的,只有张幼仪才是徐家正宗的儿媳妇。
也许陆小曼与徐家根本无缘,关于她和徐志摩的“荒唐婚姻”在硖石成为笑话。后来,陆小曼在硖石当着公婆的面,与徐志摩调情,让保守的二老再也看不下去而逃到前儿媳妇张幼仪那里。后来关于陆小曼吸鸦片以及与翁端午的风流韵事,徐家二老不可能不知道。在他们眼里,陆小曼是大逆不道的女人,他们压根就没有把她当成徐家人。
徐志摩母亲病重期间,徐申如把徐志摩和张幼仪都叫回了硖石,唯独不让陆小曼来。徐志摩跟父亲提了几次,父亲就是不吐口。徐母去世了,整个徐家都在悲哀之中。当陆小曼得知婆婆病故,要到硖石祭奠。徐志摩知道父母素来不喜欢她,就跟父亲商量说,小曼也要回来。谁知徐申如看了一眼儿子,厉声说,用不着,你要叫她来我走!在徐家人的心里儿媳妇只有一个,那就是张幼仪。
从徐母发丧,守灵,送殡,徐申如始终没有让陆小曼跨进徐家半步,家里是张幼仪戴重孝,主丧事。徐志摩憋着一肚子火,忿忿地想,父亲做的太过分了,不管陆小曼再怎么样不如意,但毕竟是他娶回来的儿媳妇,父亲这样待她,自己脸上也无光。守灵时,几句话不搭,他竟忍不住跟父亲顶撞起来。
徐申如看着一向温顺的儿子,竟在办丧事时跟自己横眉瞪眼地顶撞起来,一下子愣了。为了培养这个儿子,自己多年呕心沥血,除了不曾上天揽月外什么事没有做过?过去,虽然他做了许多荒唐事,让他们二老恨他不得。可是,他每次见到父母总是笑眯眯的告饶,或买些东西讨好二老。让他们原本一肚子的气也恨不起来了。徐申如没想到,夫人尸骨未寒,儿子竟敢这样对待自己。夫人仙逝,他正悲痛欲绝,又见儿子这样顶撞自己,忍不住扑在夫人的棺木前恸声大哭。任亲友们怎么劝也劝不住。
徐志摩木然地坐在灵棚里,看着悲伤的父亲心乱如麻。一边是自己至亲的父母,一边是自己的妻子。父母给了自己血肉,而老婆是自己人生的伴侣。他站在歧路口,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走。他知道还有一场雷霆之怒正等着他呢。人呀,活着真不易呀!
消息传到上海,陆小曼气得浑身发抖,真是奇耻大辱,婆婆病故办丧事竟然不让她这个正牌的儿媳妇参加,反而把已经离婚的张幼仪叫去。这让金尊玉贵心高气傲的陆小曼很受打击,她把所有的怨气都出在徐志摩身上。她立刻写信大骂徐志摩,说他们徐家父子俩串通一气欺负她。
可怜的徐志摩犹如一个钻进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他忙不迭地给陆小曼写信解释,对这件事他是站在她那一边的,跟父亲闹得很凶,只是因为在母亲的热孝中,不便立刻有太过激的行为。并跟陆小曼表示说,我家欺你,即是欺我……我虽懦顺,决不能就此罢休。但我却要你和我靠在一边,我们要争气,也得两人同心合力的来。
家庭关系、夫妻经济、经济窘迫如三条绳索紧紧地勒住了徐志摩的脖子,直要勒得他窒息。
徐志摩悲哀地说,你们不要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经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
徐志摩是痴子,他永远对陆小曼充满着幻想。他想,也许他离开上海可以给陆小曼有更多的时间思考,能戒掉鸦片重新振作。每当他看到林徽因,她如仙草样柔弱却充满着灵气,如梅一样傲寒而经久弥香。她的身体也羸弱,但内心却很强大。她让自己活得扬眉吐气。学建筑,她高屋建瓴,写诗文,她一身诗意千寻瀑,她率性而坦诚,既有女性的妩媚又有男人的豪情,她把一个女人活得无比精彩,让男人走近她,如嚼莲米的清香和雅致,如饮美酒般的迷恋和陶醉。徐志摩多么希望陆小曼也能像林徽因一样活得自信活得精彩。陆小曼原本也是冰雪聪明的人,她的才华完全可以与林徽因媲美。只是阿芙蓉让她迷了性,她如一只美丽缱绻的蝴蝶,最后竟化蝶为蛹。美丽的翅膀折了,只剩下慵懒的身体。
徐志摩对陆小曼可谓是用心至极,他多么盼望陆小曼能像林徽因一样有品位有理想地活着。他对陆小曼拍着哄着,希望她能走上正途。他说,小曼奋起谁不低头。但愿今后天佑你,体健日曾。先从绘画中发现自己的本真,不朽的事业端在人为。
有时,徐志摩说多了,陆小曼也动一动笔临摹些画,徐志摩都如获至宝地赶紧拿到北京给朋友们看或是装裱。绘画,凌叔华当然是行家,她看了陆小曼的作品后皱着眉头,毫不客气地说,原卷太差,一个画家必须要多看多临摹好作品,才能出好作品。徐志摩把画拿给胡适看,胡适在画的背面题了首诗,说画山要看山,画马要看马,闭门造云岚,终算不得画。小曼聪明人,莫走这条路。其他的朋友看了,都说,唉,小曼够聪明的,只是可惜留在上海糟蹋了这种才华。
徐志摩沮丧地卷起画来,给陆小曼写信说,再说你学画,你实在应该到北京来才是正理。一个故宫就够你常年揣摩了,眼界不高,腕下是不会有神的。可是,陆小曼对到北京的事根本不为所动。这年的九月是陆小曼的生日,借着她的生日,徐志摩写了封语重心长的信:
今天是九月十九日,你二十八年前出世的日子,我不在家中,不能与你对饮一杯蜜酒,为你庆祝安康。这几日秋风凄冷,秋月光明,更使游子思念家庭。又因为归思已动,更觉百无聊赖,独自惆怅。遥想闺中,当亦同此情景。今天洵美等来否?也许他们不知道,还是每天似的,只有端午一人陪着你吞吐烟霞。
眉爱,你知我是怎样的想念你!你信上什么“恐怕成病”的话,说得闪烁,使我不安。终究你这一月来身体有否见佳?如果我在家你不得休养,我出外你仍不得休养,那不是难了吗?前天和奚若谈起生活,为之相对生愁。但他与我同意,现在只有再试试,你从我来北平住一时,看是如何。你的身体当然宜北不宜南!
爱,你何以如此固执,忍心和我分离两地?上半年来去频频,又遭大故,倒还不觉得如何。这次可不同,如果我现在不回,到年假尚有两个多月。虽然光阴易逝,但我们恩爱夫妻,是否有此分离之必要?眉,你到哪天才肯听从我的主张?我一人在此,处处觉得不合式;你又不肯来,我又为责任所羁,这真是难死人也!
……
在徐志摩到北京短短的十个月里,几乎每封信都催着陆小曼到北京来,可惜陆小曼一点不为所动。当初徐志摩去北京时,她强烈地反对,后来反倒觉得离开徐志摩的唠叨,让她的生活更惬意更无拘无束地畅快了。所以每当看见徐志摩回来,她总是淡淡的。当然,谁也不会想到,二个月后,再也没人会催促着她到北京去了。她的一生真的再也没离开过上海了。
因为陆小曼坚守上海,徐志摩心系两地,他在《猛虎集》中写道,今年六个月内,上海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之间摇动活了我久蛰的性灵。
是谁唤醒了徐志摩久蛰的性灵?还是林徽因。
你去,我也走,我们就此分手;
你上哪一条大路,你放心走,
你看那街灯一直亮到天边,
你只消跟从这光明的直线!
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
放轻些脚步,别教灰土扬起,
我要认清你的远去的身影,
直到距离使我认你不分明。
再不然,我就叫响你的名字,
不断的提醒你,有我在这里,
为消解荒街与深晚的荒凉,
目送你归去……
不,我自有主张,
你不必为我忧虑;你走大路,
我进这条小巷,你看那株树,
高抵着天,我走到那边转弯,
再过去是一片荒野的凌乱;
有深潭,有浅洼,半亮着止水,
在夜芒中像是纷披的眼泪;
有石块,有钩刺胫踝的蔓草,
在期待过路人疏神时绊倒,
但你不必焦心,我有的是胆,
凶险的途程不能使我心寒。
等你走远了,我就大步的向前,
这荒野有的是夜露的清鲜;
也不愁愁云深裹,但须风动,
云海里便波涌星斗的流汞;
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
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
这首诗是徐志摩独自到香山看望林徽因,傍晚时林徽因送他下山在路口分手时的心情。这天月浑天暗,别离时总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徐志摩目送着林徽因归去的背影,内心有种说不出的凄凉。他愿林徽因顺着有街灯的光明直线的大路前行,而他还得继续在荒野、黑暗、荆棘、乱石的小路上跋涉。但他心里揣着那颗不夜的明珠,永远照在他的心底。这也是他写给林徽因的最后一首诗,也算是应和她那首《那一晚》的深情。
人生如烟,浮生若梦,有些爱不得不各安天涯。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再别康桥》
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
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次地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