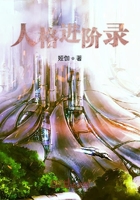眼下哪里还顾得上休息,我将篝火踢灭,牵出马儿,骑马而去。
第二日夜里,抵达安都城下,此刻离薄江上,也不过一日路程,想着此刻大军应是在薄江十里外扎营了。
我打算好好休息一夜,再行上路,横竖已经如此近了。在安都城寻了客栈住下,楼上西南厢房。
进了客栈便听都在议论薄江一战,恐也是人心惶惶,也不乏有看热闹的人在。
我径直上了楼,想早些休憩。
西南角的厢房有窗,明亮,放好行礼我便睡下。
半夜又有不适,忽然醒来。
大抵是这几日赶路,有未曾好好休息,有些伤风,也有些脾胃不适。
我下了床,轻推了门打算出去,恰在此时看到一鬼鬼祟祟的身影,我忙又躲了回去,开了门缝,小心觑着。
是个娇小的身影,面容也有几分清楚。
若素!
我吓了一跳,险些出声,慌忙捂了自个的嘴。
见她弓着身子,小心翼翼的上了楼,正往我这个方向过来,但不知她究竟是寻谁而来。她不是应该枉死了吗?是如何活下来的,又如何会出现在西景?
心中有众多疑团,此刻更是按捺不住。
她前脚刚刚经过我房门,我便破门而出,她发觉有动静,正想屈身躲闪,可我身上的功夫也不是莫须有的,又岂能任她逃逸。
一手将她肩头扣下,她抄手打上来,我又伸手将她压至门框上,使她不能动弹。
“别出声,你回头看看我是谁!”我低低道。
她果然不挣扎,缓缓的回头瞧我,一时露出惊愕的神色,久久不能回神。
我原以为她除了惊愕,当还有欣喜,可并不如我所愿。若素愕然,张着嘴瞪着眼久久未说一句话。
松了手,将她放开。
她缓缓站稳了身子,神色也正常了些,只是双眼左右躲闪,双手也垂摆的极不自然。
我估摸这里头有猫腻,她必有不能叫我知晓的事儿,可我这儿还有太多疑团想问她。
“若素,你怎到了西景?你是如何从南桀逃出来的,又为何出现在这里。”我只先这样问,是实在不知从何说起,挑了首要的先问她。
刚瞧着她她瘦了些,但面容比两年前姣好,此刻垂着头倒看不清她的神色。
“奴婢…”她臲卼摆手,声音也有些微颤。
她这个样子,倒不似我认识的若素。我认识的那个若素聪慧果敢,哪里有过这样的样子?
“你慌什么?答便是了。你安好,我心中也宽慰很多。”
巴不得她赶紧把前后因果都说与我听,直直的望着她不移开眼,哪里料到身后有人。待我发觉时,已被一掌打晕。
后颈上酸痛,这一觉睡的更是不安稳。
竟是被外头的喧闹声给吵醒了。
我撑着后颈,缓缓去起身,环视四周,此刻竟是在军帐里头。我低头看了自个的衣裳,也被换了,换成了素净的白色,腰间系着一根青色的丝带,简单大方。
过了一刻,我撩开军帐的门帘,走出去。这儿大概是大军驻扎的地方,各帐前都有士兵把守,两侧涌来的士兵正朝前方某处集结着。
我便跟着走了过去。
他们的盔甲,以及远处立着的军旗,都向我传达了一个信息。
这是西景国的军队。
我自然不必再怕些什么,心中的疑团也暂且搁置。
前头围场里聚了许多人,整装待发,我悄然走进去,四处望着也未见熟人。
倒是先前领兵的那一位发觉了我,径直走了过来。瞧他的盔甲,武器,模样应是个将军。
我微微点了点头,以作小礼。
他面容坚毅,两眼炯炯有神,几步踏至我面前,拱手作揖道:“眠王妃。”
他知道我的封号,又这样有礼。
“请问将军是?”
“末将绥远。”
绥远?那不便是绥静的父亲了?我一时有些惊讶,连忙道:“竟是绥将军,久仰,久仰。”
说罢便有些局促,这话说的实在仓促。我脸微红,垂了头。
“王妃说笑了。”他淡淡道,似不爱笑的模样,又道:“王爷在前线,末将正要前往,诸事还请王妃等王爷归来吧。”
我点了点头。
“末将告辞。”
他转身便要走。
我又急忙道:“等等,可否带我一起!”
原本这女儿家随军,就已经很不妥了,更何况我是王妃之躯。可绥远竟没有拒绝我。我称自个会骑马,他仍是寻了一位副将为我护在我一侧。
此番他只带了两百弓箭手,据说都是军营里的佼佼者,没有那些人能比的过这二百人的箭术。我猜想,两国交战隔着一条薄江,也没有什么比弓箭手更得力的了。
若是有一方先行渡江,必会在水上失利,也失了先机。
薄江,薄江。
我竟又回到薄江了。
行了半个时辰的路,远远的便感觉到那浩浩荡荡的气势,这还是我头一起瞧见千军万马,心中难免有些激动。
一时竟心跳加快,被这场景所震撼。
那一望无际的士兵,排列整齐,当真就是西景最雄厚的兵力了吗?
我随着那二百弓箭手,穿过千军万马直向薄江边上而去。我左右都是岿然不动的士兵,一个个昂头挺胸,丝毫不对即将到来的战火而有一点点惧怕之感。
走在他们之间,我竟也微微扬头。
不远处,那个骑在马上身穿银白盔甲的男人,显得有些瘦弱,可他昂头挺胸,竟丝毫不弱于他人。他卸了头盔抱在一侧,微风中发梢凌乱,缺更显得侧脸坚毅。
好久不见,他又瘦了,本就清瘦。
他面容坚毅,双眼直视这薄江一岸,一侧副将告知他弓箭手到来,他只微微点头,目光不曾离开彼岸。
其实横跨薄江,也算不得宽厚。若是渡船,最窄出,不过片刻便可渡过,只是薄江水深,水流湍急,万万不能徒步渡江,否则竟会丧命。
我遥遥向对岸望了一眼,竟也是熟悉的面孔。
赫连墨,他果然亲征了。
对岸亦是千军万马,那盔甲,那兵器也无一不叫我熟悉,南桀一国也曾强盛一时。
我微微顿了一会儿,赫连墨也发觉了我的存在,多望了我几眼,只是隔得有些远,神色看不大真切罢了。
许是西烽发觉赫连墨的目光到了他身后,他便回头瞧了一眼,正好瞧见骑马逼近的我。
我对他微微一笑。
他唇色有些苍白,笑容也有些苍白,只是他的微笑如从前一样温柔温润,淡淡道:“你来了。”
我将马儿在他右侧靠后的方向勒住,待马儿停稳妥。
经年久时,再相逢,在这浩浩汤汤的战场上。我身侧站在将陪伴我一生的男人,而敌人,恰是我无知时爱过的男子。
这样的情景,叫我永生难忘。
西烽伸出右手,向上张开,双眸凝视着我。
我便将自己的手,放入他手心。一同遥望对岸敌军,赫连墨,此一战,必有胜负。
薄江两岸驻兵,只留弓箭手防守。其实若无一方先行渡江,这一仗便开不了。便更要看哪一方忍得住,只能等。
西烽已在薄江上一日一夜未眠,只因我来了,才随我回了后方扎营之地。我早把若素之事忘得一干二净。
直到吃晚饭时,他问起我身子可还有不适,我才想起自个被打晕之事。
细细一想,打晕我的必是西烽的人,才会叫我醒来后便在薄江边上了。
可西烽和若素,素不相识。这一事又叫我不解,可我又不想问西烽,免得牵扯出南桀王宫的事儿。
纵有疑惑仍是埋在心底。
席间西烽提起越国,便问了一句:“越国身子可好些?”
我点头道:“必刚出生时好多了,也不常咳了,也会喊我娘亲了。”
他双眼一亮,微笑道:“可会喊爹爹了?”
“你又不在,他如何喊?”我失笑道。
他皱起眉,苦涩道:“走前大半月你都不曾见我,也不让我见越国,我可如何是好。”
瞧他委屈的样子,却又让我想起他的身世。一时冷了脸,淡淡道:“若不是你太多事叫我难以捉摸,我也不必这样烦心,不愿理你。”
他显然有些吃惊,忙问:“你知道什么了?”
“我…”
我正要开口,外头突然吹起号角来,似是乱作了一团。
有人匆匆闯帐进来,跪倒在地,急急道:“王爷,敌军突袭了!我军粮草被烧!”
西烽猝然起身。
所谓突袭,竟是南桀军中挑了几十人熟识水性又身体强健的,入夜时趁机潜入水中渡江而来,顺着我军防守漏洞,悄悄上岸。
皆是便衣,与薄江边上的小村庄里的百姓无差。
借着送义军粮草的百姓而来,光明正大的将火折子丢进了粮草营帐中,烧了我们的粮草。绥远当即将他们活捉了,只有七人,尽数咬舌自尽。
绥远猜测决计不会只有这几人潜入,立刻全军戒备。
西烽叫我留在营帐内不可乱走动,自个跑了出去探个仔细。
我在帐内坐立不安,来回走动,赫连墨居然这样沉不住气,可却也使我方失利。
正是焦躁难安,忽然有人闯进了帐内,立刻跪倒,道:“王妃,王爷叫您万不可离营帐一步,还请王妃稍安勿躁!”
竟又来提醒我一番,我不在意的摆了摆手,道:“知道了知道了,你退下吧。”
他久久没有离去,只跪在那儿岿然不动,我便觉得有蹊跷,走近了他。
“你怎还不去?”
他低垂着头,将手缓缓抬起,手心里赫然是一卷纸。
不动声色。
我将纸团握进手心里,低声道:“去吧,我知道了。”
他便默默起身,退了出去。
此人,必不是我军中之人。
我寻了椅子坐下,将纸团打开,上面赫然是两行字:若想知悉前因后果,请往三里外安云村与故人一聚。
右下画了一枝简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