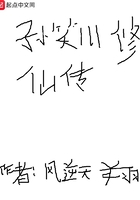狐仙姑说了以后,一家人惊恐万状。王凤同说:“咱们家,那啥,主事的都在这,咱们合计合计。”
焦桂玲说:“我说两句中不中?”
王凤同说:“那啥,中!”
王凤举说:“你娘们儿家家地,说啥?”
焦桂玲说:“呸呸!你这老爷们儿顶个屁!”
王凤同说:“那啥,让他三婶儿,说说。”
焦桂玲说:“我估摸着,狐仙姑说的对,咱们信!要是狐仙也差了呢?”
王凤同的老伴儿齐素云接着说:“吆!他三婶儿说的可对呀。要仙姑差了呢?”
焦桂玲说:“我看,咱们去算算卦。多算两个先生。要是算卦先生也说是让长虫精吃了魂,那就按着狐仙姑说的办。”
“嗯!他三婶儿说的在理儿!”齐素云补充说。
王凤同说:“那啥,大家,合计合计,看那啥,中不中?”
老二王凤刚说:“中!”
老二一搭话,在场的人都说中。于是经商议,一家去一个人。一同找算挂先生算卦。最后确定的人选是老大家王凤同、老二王凤刚、老三家焦桂玲、老四家李秀英、老五家王凤林,五个人去找算卦先生算卦。家里留下老三王凤举、老四王凤贵和老五的媳妇江风琴以及王凤同的儿子、儿媳,王凤举的儿子、儿媳。对待老头王万发的办法是,先不给吃的喝的。算卦回来再做处理。
夜间,牛郎星已经到了蛤蟆山的顶上,小北风刮的呜呜叫。黑夜有些瘆人。尽管天气不好,王凤同还是套了一辆小马车,五个人坐着车上路。他们是去红石县窑沟乡上台子村找算卦先生张宽。
人们都知道张宽不但会算卦,还看阴阳二宅。据说,那张宽算卦极准、非常的灵验,不但在红石县出了名,在偏远县也出了名。经常有人请,有人敬。王凤同等五个人找人算卦,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宽。蛤蟆沟距离上台子村五十多里路,五个人先还在车上坐着,可是西北风刮得冻耳朵,后来开始冻脚。于是几个人就下车走着、跑着。五十里路,五个人赶着车整整走了七八个小时。到达上台子村时已经上午九点多钟。
这是一个小村庄,比蛤蟆沟也好不到那去。他们经过打听,找到了张宽的家。这是一个黑油子大门,门楼非常的气势。王凤同看了后,感到这张宽才活的有滋有味。想罢,将车停在一旁,上前敲门:“那啥,张先生,在家吗?”
只听得屋门开了:“谁呀!”一个女人的声音。
“那啥,外乡的,找张先生,算卦的。”
“进来吧!”那女人说着开开了大门。
几个人进了院子,王凤同一眼看到了那个女人,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亮光光的衣服,王凤同叫不上是什么布料做的,他看了看那女人的脸。那女人的脸油光发亮。他又回过头去看了四弟妹李秀英一眼。只有四弟妹的脸能和这女人相比。那女人往屋里让着:“快上屋暖和暖和!”这女人说着看到了李秀英:“吆,这妹子真好看!”
李秀英说:“这大姐比我更好看!”
两个女人说着话,王凤同打量起这院子来,这是五间大瓦房,黑瓦、灰砖墙,玻璃窗,玻璃门,显得相当的气派。院中间一条用水泥打成的水磨石路直通的屋门处。路的两侧是用砖砌起来的花墙,每面花墙里边都围成了一个小菜园。王凤同又看了一眼,屋里窗台上摆放的花,透着玻璃就看到那花开的正艳,红色的、粉色的,白色的。来到了屋里是一条小走廊,拐过走廊连着几个门,那女人走到一个门旁,推开一个门。这是两间房子的客厅。中间生着煤火炉子。四外一圈儿沙发。沙发前都摆放着茶几。只见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在沙发上坐着,他翘着二郎腿,带着花镜,右手拿着一把紫砂壶,顺着壶嘴喝水。他一边喝水,一边翻书。猛看,具有一副绅士派头。王凤同等几个人一进来就看到这人用小茶壶喝水。他们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喝水。他们感到很新鲜。到了屋里竟然不知道怎么坐下。那汉子见王凤同等五人进来,冲他们点点头:“请坐!”
五个人坐在了沙发上。焦桂玲悄悄地与李秀英说:“这个大皮凳子还真软和!”
李秀英悄悄地扒拉她一下,焦桂玲知道自己说了外行话,冲着李秀英伸了伸舌头。
虽然焦桂玲说地是悄悄话,但是项来粗葫芦大嗓的焦桂玲小声说话全屋子也都听到了。那人冲着焦桂玲和李秀英笑笑。焦桂玲感到不好意思起来,心里骂道:“呸呸,我这张臭嘴。”想着也冲那人笑笑。
还是王凤同见过世面,他听到三弟妹管沙发叫皮凳子,心里感到这不怨三弟妹,而是怨山里穷。可蛤蟆沟也没有一家坐沙发的。所以山里的妇女不认识沙发是情有可原。为了挽回这尴尬的局面,王凤同就主动出击问那汉子:“那啥,你是张先生?”
那汉子点点头:“是,我叫张宽。你们是哪的?”
王凤同说:“那啥,偏远县,蛤蟆沟的!”
“啊哦!”张宽当即热情起来:“快,沏茶!”
那女人给五人沏茶,每人倒了一茶碗儿。五人在路上几乎冻僵,端着茶碗儿的手都有点不好使。喝了几口热茶,心里有点做主。
张宽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王凤同回答:“那啥,我们来找先生,给我爹那啥,算一卦。”
“你爹怎么了?”张宽问。
焦桂玲说:“让长虫精把魂给吃了!”
王凤同看了焦桂玲一眼。焦桂玲知道自己又多嘴。于是心里又骂了几句:“呸呸,这张臭嘴。”
张宽听到焦桂玲说老头让长虫精吃了魂,心里就感到好笑。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说:“老人的生辰八字你们知道吗?”
“那啥。知道!”王凤同说着想了想:“是,那啥壬寅 癸丑,还那啥,嗷甲戌 己巳。 ”
张宽掐算了一会儿说:“老人生于1903年正月初三巳时末。”
王凤同说:“那啥,是!”
张宽又掐算了一会儿说:“老人子月生人,犯太阴。”说罢念出了四句:“太岁之妻曰太阴,子年居戌顺推寻,犯之家长多灾病,吊替之中用意分。”
王凤同几人不知张先生说的为何意。王凤同眨了眨眼睛:“那啥,张先生,给我们那啥,细说说。”
张宽说:“这解释有两点。一是太岁星是凶神,其方凶不可犯。固有‘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之说。太阴是太岁之妻,随之亦不可侵犯。老人冒犯了太阴,故一生不得安宁。”
王风同说:“那啥,是啊。老头那啥,生我们五男二女。我妈那啥,死得早。老头就拉扯着我们七个孩子过日子。一生也那啥,没消停。”
张宽听王凤同说完,又看了看其他几位都在认真地听着。于是又说:“从老人的生辰八字上看,也不好。”
“那啥,咋那啥,不好?”王凤同忍不住地问。
张宽又念出四句:‘风云蔽月未得安,虽有智慧做事难,孤独多难无所至,老来惨死在蛇山。”
众人一听都大惊失色。
李秀英问:“先生,能给我们细说说吗,我们真不明白。”
张宽细细的看了李秀英一会儿,说“这老人甲日生于己巳时,食神旺盛,自身衰弱,甲木对巳来说正处病状,虽说暗中有中戊土为财,以巳中丙火为食神,如果不得月令,也难享福运。甲己是平头煞,如果生于春季,自身健旺而财神衰微,主骨肉兄弟不和,平生做事,往往会弄巧成拙,己巳金神如果有火制服为好。如果见不到火,必然会让甲木克尽甲己所化土气,主凶恶暴亡。这老人正好缺火,又命犯太阴。注定惨死蛇山!”
王凤刚问:“先生,我爹那啥,是让长虫吃了魂了吗?”
张宽说:“从我算的卦中应该是让长虫吃了魂魄!”
王凤林问:“先生,我爹还活着吗?”
张宽说:“老人早已不在人世。现在活着的则是长虫精。”
焦桂玲说:“呸呸!这个长虫精!”
王凤同问:“那啥先生,还能那啥,治活我爹吗?”
张宽说:“已无回天之力!”
王凤同拿出了一百元钱放在了茶几上。几个人告辞。
他们出了窑沟乡上台子村的张宽家,又去了三十里地以外的头道沟乡沟岔村找了另一个算命先生杨凤祥。那杨凤祥几乎与张宽说的一摸一样。王万发让长虫精吃了魂魄,现在附在王万发身上的是长虫精。这杨凤祥也是打卦算命,看阴阳二宅,驱神驱鬼。当王凤同让杨凤祥出手相救时,杨凤祥写了几道符。并告知:“回去以后,将这符贴到褥子底下一道,贴到炕沿帮上一道,贴在门上一道,一道烧成纸灰,用白酒当引子,给他灌下。如果三个时辰,长虫精不离开。那我杨凤祥就没办法了!请诸位再另请高明。”
王凤同问:“那啥,先生,长虫精咋样,才算离开?”
杨凤祥说:“老头死了,长虫精就离开了。”
王凤同说:“那啥,明白了!”然后又放下一百元钱。几个人告别了杨凤祥,最后赶着马车回了蛤蟆沟。到家已经是夜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