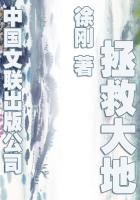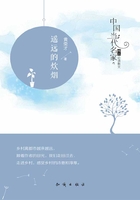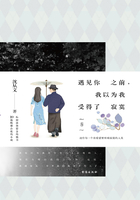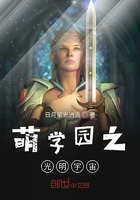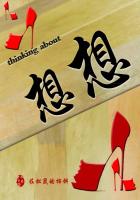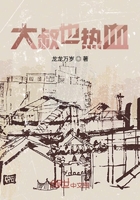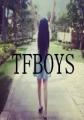经济重心的南移,引起了政治重心的变化。唐以前,虽然有些王朝曾在南方建都,但大部分王朝都建都于北方,特别是关中的长安,正因如此,西北地区成为全国的政治重心所在。西北地区在全国边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西北地区的安危,直接关系着中原王朝的存亡,因而历代中原王朝都十分重视对西北地区的经营,以保证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陆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与中原王朝对西北地区的经营关系十分密切。唐以后,中国政治重心逐渐东移,由洛阳、开封最终到北京,中国北部和东北地区成为边防的重点,西北地区在全国的战略地位也随之下降,中原王朝对西北的重视程度自然要次之,对西北地区的经营也较之唐以前大为逊色,这必然要对丝绸之路产生影响。
第四,海上丝路的兴盛,与海外贸易的收入在中原王朝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有关。唐以前,统治者把海外贸易视为获取珍奇宝玩的渠道,海外贸易的收入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并不占什么位置。到了唐代,在广州设市舶司,由中央政府派官员专门负责征税事宜,市舶收入开始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五代时期,国家分裂,但中外海上贸易仍然是东南沿海割据政权的重要财政支柱,北宋中期的宋神宗就曾指出:“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亦由笼海商得法也。”宋元以来,海外贸易成为政府一个很重要的财政收入项目,北宋初年,政府获得的舶货,“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仁宗皇韦占年间“总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到宋徽宗统治时期,市舶岁人达120万左右。南宋时,市舶收入迅速上升。仅泉州市舶司在建炎四年(1130年)就“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按南宋初“乳香九万一千五百斤,直可百二十余万缗”计算,这一年泉州市舶司所获乳香就达100万缗以上。按北宋熙宁九年收入54万余,支出23万多,收支相抵,净利占总收人数五分之三计算,建炎四年泉州一司的市舶净利钱应在60万缗左右。加上广州及两浙市舶收入,应在100万以上。南宋初年,中央财政收入不满1(100万缗,市舶收人竟占南宋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如此巨大的市舶收入,对支持南宋财政,帮助南宋渡过危机,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元代市舶收入及所收舶货在财政方面的应用情况,没有像宋代那样详细见于文献记载,但也有线索可寻。据《元史·世祖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市舶司收入黄金3400两,而大德二年(1298年)的“岁人之数”,金为19(190两,银60000两,钞360锭。至元二十六年市舶收入的黄金,就是大德二年岁收黄金总数的六分之一以上。足见市舶收入在元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很大的。正由于宋元王朝从海外贸易中获得巨大的财政收益,所以宋元两朝都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从而激活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
第五,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与宋元以来输出和输入的商品有关。从唐代开始,在中国对外贸易中,除了丝绸外,瓷器成为大宗。到了宋代,瓷器生产更为发达,产品已远销到东西方几十个地区和国家。由于瓷器成为中国输出品的大宗,从运输而言,船舶运输不仅运载量大,且比较平稳,瓷器不易损坏,由于有这些优点,商人自然就会选择海上交通,因此有人也将海上丝绸之路称为“瓷器之路”,足见海上丝路的发展与瓷器的输出关系很大。
唐宋以来,香药在中国输入商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代香药不仅包括范围很广,而且用途也很广泛,香药被用作药物、化妆、熏衣、制炬等,尽管当时香药价格昂贵,但每年都有大量进口,因而香药成为对外贸易中的重要物品。就香药产地而言,东南亚国家及印度次大陆、大食诸国,历来被认为是香药及各种名贵宝物的产地,这必然使香药输人大量由海路到达中国。
第六,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与宋元以来造船工艺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有关。宋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重大发展的时期,综合应用许多科技成果的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都有显著进步。东南沿海许多地方都有官府的造船工场,所造海船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这一时期,造船工艺的进步,突出表现在海船载重量的增加和海船良好的抗沉性能,宋神宗时,已制造出载重600吨左右的大船,反映出中国的造船工艺已处于世界前列。
中国的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海岸气象规律和天文航海技术的掌握及指南针的应用上。宋元时期,中国的航海家已较好地掌握了海上季风的活动规律,并利用它为航海服务。这一时期,有经验的航海家已掌握了利用北极星高度判断地理纬度的“牵星术”。而指南针用于航海,出现了航海罗盘,则更是宋元时期航海技术方面的一项重要突破,也是中国对世界航海事业的一项伟大贡献。此外,这一时期海员掌握的深水探测技术也更加熟练了,测深技术的广泛应用,已使航船不致“浅搁”或“倾覆”。海上航行时,还利用信鸽作为通讯工具。
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不仅使宋元时期的中国能够造出更多的可以在大海中乘风破浪航行的海船,还使得航海更加安全,航向更加准确,保证中国海船可以按计划驶向所要到达的国家,航程也大大缩短。这是海上丝路空前繁荣的一个重要的时代条件。
由以上分析可知,宋元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关系很大,作为丝绸之路咽喉要道上的敦煌,伴随着丝路的衰落,逐渐沉寂,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到了明代,经由河西走廊的陆路通道虽然仍然是连接西域与中原的主要交通干线,却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且这一时期的交通干线已不再经过敦煌,而是改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这又使在这条干线之南的敦煌失去了陆路中西交通中转站的地位,这样敦煌的进一步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当然,敦煌的兴衰不完全是由丝绸之路的兴衰决定的,因为丝路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原王朝对西域和敦煌的控制。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从元代以来,敦煌作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其战略地位已开始下降。明初,为了防止元朝残余势力的继续东进,大将冯胜在肃州以西70里处的文殊山与黑山之间的山谷地带修筑了嘉峪关,并派兵驻守。在嘉峪关至哈密间,设“关西七卫”,即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蒙古、沙州、哈密七卫,作为明王朝的西陲“屏藩”,敦煌境内设有沙州、罕东二卫,以后,嘉峪关逐步变为明朝的西部边关。明王朝设置七卫的目的,是给这些部族的酋长以一定的官爵封号,为这些部族提供一些水利、农耕设备,使它们在西部与明王朝保持正常的关系,以保证西域往来和入藏往来的使臣商队等安全通过,并使明政府可以将国防防御力量专门用以对付北部蒙古势力;明政府设关西七卫的另一目的,在于使七卫犬牙相制,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对付明王朝。关西七卫的设置,曾经对明朝的西北边防起过积极作用,但由于明王朝决策的失误,加上七卫之间相互攻杀,严重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结果七卫被吐鲁番和蒙古亦不刺各个击破,各族人民多迁入嘉峪关内,居住在肃州、甘州之地,于是,嘉峪关以西包括敦煌在内的广大地区被弃置在防线之外,敦煌的得失,对河西地区已没有多大影响了。而有明一代,敦煌长期为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区,这就改变了自汉代以来确立的以农业为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大片土地沦为牧场,从而使敦煌地区的社会经济出现了倒退。
清代,敦煌由于移民屯垦等措施的实行,经济曾再度复苏,但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