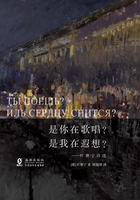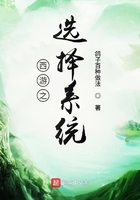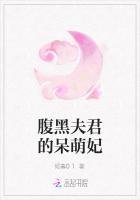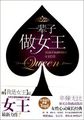我们知道,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全方位的,现存敦煌文献及敦煌石窟中,保存了大量古代科技方面的资料,真实反映了中国古代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及外国科技沿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的轨迹,对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我们摘其要者介绍如下。
1.农业科技
两汉以来,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立以及中原王朝一系列开发河西政策的实施,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传到了敦煌。汉武帝晚年,赵过发明的代田法就在河西、敦煌推广使用。曹魏嘉平年间(249年—254年),担任敦煌太守的皇甫隆,在敦煌地区进行了许多农业改革活动。
《三国志·仓慈传》注引《魏略》称:“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赵)基为太守。初,敦煌不甚晓田,常灌溉清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由于先进的耕作技术的推广,敦煌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粮食产量增加了五成。耧作为播种工具,大约发明于汉代以前,汉武帝时,赵过在过去的耧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先进的能同时播种三行的三脚耧,即耧犁。皇甫隆在敦煌推广的耧犁,就是这种三脚耧。由于它能够适应敦煌地区的农作播种需要,因而在敦煌地区长期保留下来。这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就出现在敦煌壁画中。莫高窟宋初第454窟东披《弥勒经变》反映“一种七收”的画面中,发现了一幅一个农民用一牛拉的三脚耧耕种的形象资料。用三脚耧播种时,只用一牛牵耧,一人扶耧;种子盛在耧斗中,耧斗通空心的耧脚,边行边摇,种子乃自行落下。它能同时完成开沟、下种、覆土三道工序,一次能播种三行,而且行距一致,下种均匀,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敦煌壁画三脚耧的出现,充分说明了自皇甫隆在敦煌教作三脚耧这一先进的播种工具后,一直为敦煌农村所使用。敦煌壁画三脚耧虽是宋代播种耧的形象,但它确实是汉代以来耧犁的延续。454窟壁画犁耧,是我国宋代播种耧的惟一形象资料,这不仅对我们了解敦煌及河西古代播种工具的应用情况有很大意义,而且对我国的农业考古和农业科技发展史的研究也是极其珍贵的资料。
唐代农业科技方面的一个主要成就,是曲辕犁的发明并应用。晚唐陆龟蒙在其所著《末耜经》中,记载了当时江东地区的一种耕犁,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曲辕犁。唐以前的犁多为直辕犁,犁架庞大,调节耕地深浅的设备也不完善。曲辕犁改直辕为曲辕,犁架变小,轻便灵活,能够调节深浅,用一牛即可挽拉,从而改变了二牛抬扛的牵引方法。曲辕犁的出现,是继汉代犁耕发展之后又一次新的突破,在我国古代犁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陆龟蒙是晚唐时人,他所说的曲辕犁并非到晚唐才出现,事实上,曲辕犁在唐前期就已发明并在中原内地使用,这一点已为考古发掘材料所证明。曲辕犁发明后,很快传人敦煌,莫高窟第445窟盛唐壁画《弥勒经变》中,有一幅农作图中就绘有这种曲辕犁,它将我国发明曲辕犁的时代提前到公元8世纪,是我国农业科技史的珍贵资料,这也说明唐代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已和中原内地有相近的水平。
除此外,敦煌壁画中反映的耙、耱、铲、锄等农具都与我国内地使用的相同。收获庄稼的各式镰刀、飏谷工具在壁画中也有不少表现。多数收割画面中的镰刀,和出土的唐宋铁镰刀大致相同。敦煌壁画“农作图”中出现的13幅唐宋时期的打场图全用连枷,且都是将收割的庄稼平铺在场院地上一人抡连枷或两人对打。壁画中还绘制了权、木锨、簸箕、飏篮4种扬场工具。莫高窟186、240窟和榆林窟25、38窟,画男人用四齿、五齿、六齿权扬场;莫高窟61、240窟和榆林窟20窟画男人用木锨扬场;莫高窟9、12、61、98、141、148、156、186、196、200、202、231、232、240、386等窟中则都绘有妇女站在三脚凳和四脚凳上用簸箕和飏篮扬场的画面。在粮食脱粒和扬场中还有一件重要工具——扫帚。壁画中反映的扫帚是河西乃至西北许多地区都在使用的用芨芨草扎成的扫帚,用来打扫场院和扬场时掠杂物。上述这些扬场工具至今仍在我国农村广泛地使用。
敦煌壁画中还绘制了一些粮食加工工具。唐代以来,以水为动力的加工工具在敦煌地区普遍使用。敦煌文献中大量记载了唐代敦煌寺院水磨的经营方式,出租、收费、纳税等情况。敦煌水磨的样式已很难见到,但用人力加工粮食的石磨,却能在敦煌壁画中找到形象资料。莫高窟321窟南壁《宝雨经变》中,绘有一妇女用一只手操作的手推磨,这种小石磨和1972年在唐沙州城遗址出土的唐代小石磨大体相同。手摇石磨的操作使用了“曲柄摇手”,这是我国应用机械原理的一项重要发明。61窟西壁《五台山图》中绘有两个壮汉双手抱磨杆推的大石磨,元代藏族画家画的465窟壁画中,还绘有藏族石匠正在凿制石磨的画面。61窟《五台山图》中有一幅加工谷物的《踏碓图》,榆林窟3窟西夏《观音经变》画中,则对称地绘了两幅相同的《踏碓图》,465窟绘制的《踏碓图》侧旁,还贴有用纸写的汉藏文对照的“踏碓师”墨书题记,等等。
总之,敦煌壁画中反映的农业科技远远不止这些,其他如狩猎、屠宰、放马、牧牛、驯虎、养鸭、挤牛奶、煮牛奶、制皮造鞍以及院落马厩、铡草、牲畜饲养等畜牧业生产生活方面的技术也在壁画中有反映。反映农业科技的有关敦煌壁画,不仅生动、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古代敦煌地区农业科技的发展水平,而且也成为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史研究的极其珍贵的形象资料。
2.天文历法
敦煌文献及敦煌壁画中保存的天文学资料,不仅真实记录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水平,而且也反映了古代西方国家的天文学成就沿丝绸之路向中国传播的轨迹。
天文学的基础是星象的观测。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两幅精美的古代星图,一幅是s.3326《全天星图》,现藏英国图书馆;一幅是敦博76号《紫微垣星图》,画在《唐人写地志残卷》的背后,现藏甘肃敦煌市博物馆。其中《全天星图》大约绘于705年至710年,图上绘有1359颗星,是世界上现存星数最多、也是最古老的一幅星图。
《全天星图》的成就在于,一是它囊括了当时北半球肉眼所能见到的大部分恒星。欧洲自公元前2世纪起至1609年发明望远镜之前,始终没有超过1022颗星的星图,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在当时的条件下,观测出1359颗星,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高超的天文学观测水平;一是它的画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画法。《全天星图》从12月开始画起,根据每月太阳位置的所在,把赤道带附近的星分成12段,利用类似麦卡托(1512年~1594.年)圆筒投影的方法画出来,最后再把紫微垣画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平面投影图上。在欧洲,麦卡托投影被认为是由荷兰数学家兼地理学家克雷梅尔首创的,麦卡托即克雷梅尔的拉丁语名字。他在1568年刊印了第一幅“麦卡托投影”航海图。敦煌唐代星图的出现,说明中国天文学家使用圆柱投影的时间要比麦卡托早七八百年,可见敦煌星图在画法上是相当进步的。在这以前画星图的方法一直是以北极为中心,把全天的星投影在一个平面上;另一种办法是用直角坐标投影,把全天的星绘在所谓“横图”上。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缺点。为了克服这两种画法的缺点,只得把天球一分为二:把北极附近的星画在圆图上,把赤道附近的星画在横图上。《全天星图》就是我们现在所知按照这种办法画的最早的一幅。这种办法一直应用到现在,所不同的是现在把南极附近的星再画在__一张圆图上。《全天星图》被发现后,引起了中外科技史专家的高度重视,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李约瑟教授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天文学部分就复制刊登了这件星图,并给予高度评价。
《紫微星垣图》现藏存于敦煌市博物馆,原件高31em,残长299.5cm,1944年向达先生在敦煌从事考古发拙时从民间发现。向达教授将该卷文书定名为《唐人写地志残卷》,卷子背面另写有《占云气书》一卷,残存《观云章》、《占气章》两章。在《占云气书》的前面有一幅紫微宫图,即《紫微星垣图》。星图的画法是将紫微垣诸星画在直径分别为26厘米和13厘米的两个同心圆内。在紫微垣近闾阖门处标有“紫微宫”三字,垣的东西两侧分别标注“东蕃”和“西蕃”,意即“蕃卫”,内圆(即紫微垣)画成一个封闭的圆圈,垣的前后面都设有缺口作为垣门。图中的黑点表示甘德星,红色圆圈表示石申和巫咸星。根据其中传舍、八谷和文昌等星推测,这幅星图观测地点的地理纬度为北纬35°左右,相当于西安、洛阳等地。由于《紫微星垣图》比s.3326星图稍晚,所以绘得更加细致。
现藏于巴黎的P.2512文书,也是一卷重要的天文学著作。该卷残存内容有四部分:星占的残余部分;《二十八宿次位经》和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经;《玄像诗》;日月旁气占。在《二十八宿次位经》之后有“白天皇以来至武德四年(621年)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一百岁”的记载,表明这件文献抄写于武德四年,其成书则当在唐初或唐以前。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在战国时期初步形成,当时有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家,记录了各自对星宿的观察结果,并绘成星图,流传下来。至三国末年,东吴太史令(掌管星历的官)陈卓,把甘、石、巫咸三家的成果加以总结,纳入自己的书中,但陈氏的著作和甘、石等三家的原著都失传了。P.2512文书,记录了甘、石、巫咸三家内外官星283座,464颗,和《晋书·天文志》所记陈卓录的三家星数完全吻合,星座后有11项星占文字,可能来自陈氏著作,从而使人们对三家星经及陈氏著作有了大致了解。这也是现存星书中最早的写本。上述s.3326《全天星图》中就分别用红黑不同的颜色,标出了甘、石、巫咸三家的星宿,图中十二次起讫度和《晋书·天文志》所记陈卓的十二次起迄度完全一样,显然,《全天星图》与三家星图有渊源关系。
P.2512中的《玄像诗》,则是配合三家星经而作的五言诗,共263句。全篇通过浅显易懂的诗句,将天穹上各星座的位置的次序写入诗中,人们只要记住这些诗句,再去对照满天星斗,就可以记住全天主要星官。它反映了唐初天文学普及的情况。
由于天文学的基础是星象的观测,对古人来说,无垠的穹窿是那样神秘莫测,所以在世界各文明古国里,天文学往往和占星术混在一起。在敦煌所出星占文献中,也反映了这一现象。同时,在敦煌所出星占文献中,我们也看到了西方天文学影响的痕迹。
中世纪波斯人用巴列维语写成的《班达希申》(Bundahishn,意为“原初的创造”或“创世纪”)一书,一般认为成书于9世纪。该书中所讲的波斯星占方法,是以黄道十二宫即十二星座(山羊座、人马座、天蝎座、天秤座、处女座、狮子座、巨蟹座、双子座、双鱼座、水瓶座、金牛座、白羊座),与表示命运的十二位(寿命位、财库位、兄弟位、田宅位、儿孙位、奴仆位、夫妻位、临终位、迁移位、天央位、福德位、祸害位)相配合,以推算命运。值得注意的是,敦煌所出P.4071号中有类似的星命方术。P.4071号文书课命,引述《聿斯经》、《都利聿斯经》两卷,贞元中(785年—804年)都利术士李弥乾传自西天竺。此“都利”即中亚Talas河,Talas一带有源自波斯文化的粟特人的活动,而P.4071号课命文书的撰写者康氏,当为粟特人。在P.4071星命文书中我们看到两点与中古波斯文著作《班达希申》相近之处:其一,以黄道十二宫推命;其二,课文中的“财帛宫”等,相当于上述波斯文著作中的“财库位”第十二位。P.4071文书末行为“开宝七年十二月灵州大都府白衣术士康遵课”,说明宋开宝七年(974年)之后,波斯星占术已自西印度、中亚Talas河经粟特人传到了灵州及敦煌。那么,与琐罗亚斯特教有关的波斯星占术为什么来自西印度?原来,当波斯人多数改宗******后,8世纪一部分信仰琐罗亚斯特教的波斯人来到西北印度,此种宗教在那里一直保存至今,这就是《都利聿斯经》来自西天竺的背景。P.4071号文书既有“八卦”、“分野”等中国文化,又有将黄道十二宫用于星占的波斯文化,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和波斯文化相生相成的情景。
黄道是地球上的人看太阳于一年内在恒星之间所走的视路径。黄道两侧各八度以内的部分,称为黄道带,古人为了表示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位置,把黄道带分为十二部分,叫做黄道带十二宫,每宫30度,各用一个跨着黄道的星座作为标志,叫做黄道带十二星座。黄道十二宫体系起源于古巴比伦,形成于希腊,并由希腊传人印度,后随佛教传人中国。黄道十二宫的内容也出现在敦煌壁画中。敦煌莫高窟61窟甬道两壁系后代重绘(重绘时间有人认为在西夏,有人认为在元代),其中南壁绘《炽盛光佛》一铺,在《炽盛光佛》像两旁和后面有《九曜神像》,天空中有《黄道十二宫》图形。敦煌城南60公里的五个庙石窟,第1窟东壁正中绘有一幅《炽盛光佛》,上方两侧背衬中绘出黄道十二宫及二十八宿神像。据学者们根据敦煌壁画及新疆、宁夏等地发现的有关黄道十二宫的资料,认为这一体系是沿丝绸之路传人我国的。
天文和历法,在古代也是紧密相连的。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历法写本,是研究古代历法的原始材料,现存敦煌文献中的天文历法写卷约有40余件,其形制、内涵为世人所瞩目。
在吐蕃军队占领敦煌以前,唐王朝的历法一直在敦煌地区使用。吐蕃占领敦煌以后,敦煌同中原王朝的联系被割断,难以得到中原王朝统一颁发的历日。吐蕃使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纪年,这既不符合汉人行之已久的干支纪年、纪月、纪日的习惯,也无法满足敦煌汉人日常生活的需要。于是,敦煌地区开始出现当地自编的历书。张议潮起义推翻吐蕃统治、建立归义军政权后,敦煌又回到中原王朝怀抱,但敦煌自编历书仍在民间继续使用。唐末、五代,敦煌再度脱离中原王朝控制,从现存敦煌文献来看,敦煌地区自编历日一直延续到宋初,前后达两个世纪。